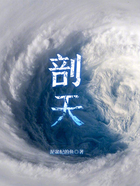
第16章 风暴潮(九)
承担两条性命的柔弱之躯远比陈相想象得要脆弱,忍受近10个月的苦楚,一不小心,竟要生出一双死亡来。陈相十分庆幸自己还有机会重新来过,这一次,他依然要利用张瑾玥对陈波挚不可摧的感情,只是换为更加柔和的方式。
“瑾玥,我有件事要告诉你。”陈相接起电话,把语调压得很沉,闷闷不乐一样。
“什么事?你说。”张瑾玥的语气里有微不可察的担忧。
“张台跟我说,我升首席那事,省里没给批准。会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老预报员调动过来,接梁老师的班。以后我都没有机会了。”
“没事。”张瑾玥语调轻快,没有惊讶,也没有惋惜,反而很高兴似的,“首席不首席的,一点都不重要,只要你好好的就行。正好少加点班,少点压力。”
“可是我工资涨不了了。而且台里新来人,就多一张嘴吃饭,我辛苦到头,挣得还没之前多。”
“日子怎么样都能过,别多想了,快把饭吃了吧。晚上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杂鱼汤,趁热吃,放凉就不鲜了。今天买的鱼不太好,都是鳓鱼和青占鱼,刺多,你……”
“瑾玥。”陈相把对方的话头截住,“我心情不好,想现在请假回家和你说说话。你在家里等着我,好吗?”
张瑾玥没有一丝犹豫,“好,我等你回来。”
挂掉电话,嘱咐好任天富,借来张勇的手表,一切都顺利得不可思议,除了最重要的一环:停在仓库旁的车。
关于那辆车的行踪,陈相打听过了,可收到的回答却十分不尽人意:那车是定期为台里送氢气的,台里每个人都见过,但没人知道它具体什么时间出现。氢气在东海岛上的炼化厂里生产,走水路送过来。海上的事,没人能说得准。
于是,晚间11点整,在能闷死人的室外,仓库旁的昏黄路灯下,立了一个东张西望的人。陈相一边甩手跺脚以防被蚊子抬走,一边不断向山头下黑黢黢的大门处看。那里没有不知何时现身的四轮车,只有一个若隐若现的黄色光点在树丛中飘来飘去。
按照经验,这个时间,赵栋梁应该猫在半山腰,做着一些神神秘秘见不得人的事,那光是他在打手电。
出于等待的不耐烦,也出于好奇,陈相走下山坡,到离光点不远的地方,放轻脚步,停在一颗年幼棕榈树旁,透过红桑丛茂密的大叶,窥探赵栋梁的行迹。只见那人一只手捧书,一只手打手电,来回渡步,一会儿把书本贴在脸上仔细看,一会儿手指从嘴角揩吐沫下来翻页,一会儿抓耳挠腮,口中念念有词。
陈相看好久都没看出什么所以然。眼前这位年轻版的赵栋梁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怪人,性格乖戾、行为诡异,比乡下的神婆更加神秘。
在一个靠科学吃饭的单位里,顶着“卖卦哥”这样一个侮辱人的外号,还真是一点都没委屈他。真不知道这样一个不靠谱的人,究竟是凭借怎样的龌龊手段,在十多年后坐上台长的位置。
正想着,远处传来发动机高速运转的嗡嗡声,渴盼已久的猎物来了。
陈相转头就跑,被两行棕榈树夹着,跑回空旷的山头,躲在仓库背面。午夜12点的环境十分寂寥,静得连划火柴的声音都显得十分刺耳。
司机没有熄火就跳下车,躲到远离车的仓库侧面,迫不及待地点燃了一根自裹的叶子烟。强烈的烟熏臭气夹杂着陈年霉味弥漫开来,漫到一角之隔的陈相面前,呛得他忍不住要咳嗽。
载着一车氢气疾驰并不是一件安全的事,所以陈相选择等,等到氢气瓶被搬空再考虑下一步。那人搬得很慢,慢条斯理一罐一罐地搬,半个小时过去,依旧没搬完,急得陈相想跺脚。期间,那人又在老地方抽了三根烟,差点把陈相熏得背过气去。
终于,那有节奏的,稳稳当当的脚步声停止了,仓库内也不再发出金属碰撞的脆响,而是被细细簌簌的布料摩擦声所取代。那人不知从哪里扯出一个探空气球胚子,细细地折叠成条,然后往自己腰上裹,十分投入。
陈相终于等来这来之不易的好时机,蹑手蹑脚走向还在嗡嗡嗡的车。半夜三更靠劣质旱烟提神送货的猛士,想必不会那么好说话。他想象不到使用什么拙劣的借口才能说服对方借车给自己,于是选择把道德的紧箍松一松。直接把车开走,跑赢风暴潮,救下两条人命,是逃离这个虚妄之地的最短路径。
但他没能如愿。对方的耳朵似乎也出奇的好使,陈相刚把一只脚迈上驾驶舱的门槛,身后就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紧接着,一双有力的大手把他一把薅了下来。
“你干什么呢?”
陈相差点摔个趔趄,身子摇晃半天才站稳,面对眼前这位身材粗壮,瞪眼发狠的人,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话。于是他选择用行动代替语言,像搁浅的小梭鱼躲避赶海者的追击,一下子重新溜进驾驶舱里,赶在对方伸手之前关门,松开手刹。
这个过程十分不顺利。期间,那位猛士半身架在车窗上,把一只胳膊伸进车内,阻拦陈相的所有动作,同时不断叫喊,“偷车贼!强盗!”
陈相终是敌不过,又被拉扯出来,结结实实被甩了一个大跟头。对方一边喋喋不休,一边把他往山下扯,他丝毫反抗不过。两人的争执似乎惊扰到了赵栋梁,半山腰飘着的黄色光点不断上移,离他们越来越近。
陈相在心中大呼不妙。也许他和这位猛士之间还有商量的余地,但一旦被赵栋梁这位正义的小鬼纠缠上,他今晚就别想走了。
情急之下,陈相喊,“你是不是偷了气球胚子?”
对方愣了一下,手上的力道弱下来。
“我看到了,你刚刚在仓库里叠气球,还想往腰上缠。那东西看起来不起眼,其实特别贵,够你坐牢的。”陈相趁势说。
这话显然很有效。他话音刚落,对方就彻底松开手,立在原地,换上一副不知所措的表情,像犯错的孩子。
“我们做个交易吧。”陈相把语气缓和下来,“你载我先去西二路二横巷,再去人民医院。作为报酬,你可以把气球拿走,我当作没看见。”
十分顺利地,陈相坐上了疾驰的卡车,赶在赵栋梁贴过来之前。
车子疾驰下山,在尘土飞扬的土渣路上熟捻地拐来拐去。陈相被晃得晕乎乎的,心情格外轻松。现在是12点50分,司机轻车熟路,要不了15分钟就能到家,接上张瑾玥后,最多1点半就能赶到医院。这次一定会顺利。
司机的心情似乎也不错,又抽了半根烟提神,把话匣子打开了。
“我叫陈德球,跑货的,专门帮东海炼化厂送氢气。头几年,我还开过大货,13米,满载,一路北上去辽宁送木材,一万里地。那个时候,开大货可神气了,方向盘一转,县长都不换。车载着货出去,载着票子回来,风一刮,飞一地,看得人晕乎。”
陈德球提起光辉往事,脸上闪着光彩。
“送氢气比送木材更赚钱吗?”陈相随口问。
陈德球摇头,“长途大货才赚钱,这几个小破瓶要多寒碜有多寒碜,还危险。可没办法,我儿生病了,要治病,他姨走得早,只能我陪着,离不开多远。我那孩子,贵虾,生得可喜欢人,还懂事,自己躺医院里打针吃药,从来不喊难受,我一回去就跟我笑。”
陈德球说着,先前的神气样逐渐从脸上消去,他歪头瞥了一眼团在两人脚下的气球胚子,冲陈相说,“老弟,帮我个忙,那气球,帮我灌点气进去,看好不好用。我叠的时候,看见上面有个破洞。”
陈相照做。他把车窗摇下来,让气球胚子兜住越来越大的风,一米见方的橡胶胚子瞬间被灌得半满,占据半个驾驶室,伸到陈德球眼前。风从球炳进,从球面上大大小小的破洞出,吹得陈德球直眯眼睛。
陈德球默默看一眼气球的残破样,没有说什么。陈相默默把胚子收起叠好,抱在怀中,眼睛直勾勾盯着路尽头被渐起的雨晕成球的灯光,二横巷要到了。
谁知这时,车子猛地转弯,偏离陈相望眼欲穿的方向,直直拐到另外一条没有灯的小路上,越开越快。
“陈师傅你走错了吧?二横巷不在这个方向上。”陈相说。
“我要先去另外一个地方,到我老兄的厂子里去借点胶水粘气球,不远,也就10里地,之后照常送你,我儿也在人民医院。”陈德球边说边把雨刷器开到最大挡位,风雨越来越大,不断有碎叶糊在车窗上。
陈相看一眼手表,1点5分了,去粘气球来回10公里,最快也要1点20才能到达二横巷附近。那个时候风雨早就大到没法正常走路了,二横巷过不了那么大的车,张瑾玥又要在如此恶劣的天气里受到惊吓。
即便能把她平安接到车上,平安挨过颠簸驶到医院,也很难说能不能赶在风暴潮之前。这样的估算还是建立在绝对顺利的前提下,期间但凡有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他们就会被淹死在路上。
于是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去。台风已经刮起来了,还会持续变强,强到能把你车掀翻。刮完风还要发大水,能把人淹死。”
陈德球没有做声,像没听到一样,聚精会神地开车。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有台风,还有风暴潮,为了粘个气球,你连命都不要了?”
陈相心急了。他并不知晓陈德球偷气球的原因,那种东西除了载着一斤多重的无线电探空仪飘摇升天,每隔10米向地面回传探测数据,供预报员分析以外,没有任何用途。
在观测场内,它是预报员吃饭的碗,在观测场外,是看都不愿意看一眼的垃圾。陈德球究竟是哪里来的执念,非要抛却骨子里的老实本分,偷拿这样一个一无所用的垃圾。拿就拿了,还一定要把它补好。
莫非是迷信了哪位神婆的鬼话,要把这能飘上3万米高空的通天之物拿回家供着?
“陈师傅,我是干天气预报的,你看见天上的跑马云了吗?这是台风,能把车子掀翻、窗子撞破、船吹跑、鱼卷到天上的台风。你要是还想平安见到你儿子,就别去补那个破气球!”
陈相把这句急到烫口的话吐出时,车子刚好行驶到南桥河边,逆着匆匆的河水往西边走。没走多远,便一个急刹停下了。
“你下车吧。”陈德球指着车门,情绪激动,“气球我要补,儿子我也要见,别说台风了,就算天上下刀子我也不怕。我车不载晦气人。”
陈相没有动弹。和陈德球不一样,此时的他十分理智,在这种沿河荒郊地下车步行,用不了多久,就能被风刮死或者被水淹死。理智之余是忐忑,他害怕眼前的壮汉一气之下把他给扔下车去,那样的话,就连一丁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
好在,陈德球只是盯了陈相一会儿,见陈相没再作声,便又启程了。
车继续西行,沿南桥河畔逆流而上,滔滔的河水看得人眼晕,车身不时被阵风撞得颠簸一下,像一艘脆弱的船。
“陈师傅,你的贵虾,得了什么病?”陈相试探着发问。一位把孩子挂在嘴边的父亲,定是爱子如命的。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打破他荒谬的执念,一定是他那等在人民医院的贵虾。
陈德球没有回答,眼睛紧盯前方,双手死握方向盘,依然保持着一副对抗风雨的专业姿态,只是肩膀慢慢垮下来,愤怒和激越的神情从脸上消失,换为让人恻隐的凄悲。
良久,他终于开了口,以格外沉郁的调子:“神经母细胞瘤,差分化型,骨髓转移,4期高危。”
这些字句从陈德球嘴里吐出来,生硬得像在背课文。专业的医学词汇,在普通人眼中显得格外苍白,但其背后必有一个痛心的故事。
“贵虾生得十分规矩,可老天爷却不待见他。驮仔十月出生,清晨天刚白的时候有动静,不到中午就落地了,连执仔婆都说生得顺。提前煲好的姜醋送出去,脐带请执仔婆剪好,渍上石灰,包到红纸里,红纸放到瓦罐里,瓦罐存在他姨的床下。老祖宗留下的习惯,这样孩儿就可以不离膝下,长命百岁。
他姨坐月子天天喝生化汤,奶水足,把他奶得可胖,胳膊腿和莲藕节一样。办满月酒,给左邻右里都送上红鸡蛋和酸姜;做百啰,请吃饭;庆周岁,讨百家衣求吉利,每年都做生日。等他三岁话说利索了,又带他拜祠堂,请先祖保佑他。
安安稳稳长到五岁,眼见就要长成小大人,忽然得了这么个病。”
陈德球的这番苦痛似乎淤着散不去很久了,一旦说出口,就像瀑流一样全倾泻出来,滔滔滚滚。
“那年初夏,我跑完一趟货,专门托人拿打了一架能窜天的木头飞机,回家看他,哄他开心。他躺在外家父的竹椅上晒太阳,老远看见我,却没迎过来。我把飞机从兜里掏出来,给机头浆上的皮筋箍紧,一撒手飞老高。
他也不看,也不喊我,一只手捂着左肚子,眼睛直勾勾不知道往哪里盯。贵虾最喜欢天上的东西,冬天天天到海边上看北方飞过来的大白鸟,都不嫌冷,夜里偶尔见到天上的飞机高兴得乱跳。
他那天是有多疼,才会呆愣成那样。
后来,我带他看病,从村里的阿祖看到城里最大的医院,越看越糟糕。花大价钱拍片抽骨髓,才知道是那么个病。整整一年,每天打针吃药,吃得面黄肌瘦,头发都掉光,也不见好,乌溜眼里明闪闪的光全都没了。
我陪他耗在医院里,把家底全部耗光。管他床的白头老大夫说,贵虾这病都是刚出生的小小孩儿才得,大孩子没见过得这个的。
我究竟是造了什么孽,让我儿受这么个罪。”
陈德球就这样说了很久,说到最末几句时,风雨已经大到让陈相听不清楚他撕心裂肺的哀怨,只能看到下弯的嘴一张一合,两束皱纹蛛网一样结在眼角上,被水沾湿。
在一个无灯的路弯,陈德球忽然减速,七拐八拐把车停到一个无灯的大仓库里,从货舱里拉出一个鼓风机,一把扯过气球胚,佝偻着背跳下车。
陈相并没有去看手表表盘上那个令人绝望的数字。他一直想搞明白的问题——那位慈父对气球胚子的执念源自何处——似乎也已经不重要了。
如果有人能对可怖的天灾熟视无睹,那一定是因为,他的人生早已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