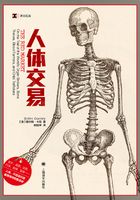
第3章 人体炼金术
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艾蜜莉[4]似乎毫无重量地悬在空中,她四肢的向上冲力即将屈服于地心引力。在她登上的最高点,物理现象会决定她的命运,不过她的身体仍是属于她自己的。不一会儿,这次撞击就会立即引发一连串的事件,艾蜜莉这个人停止存在,她身体的命运将会落在别人的肩头上。不过,此时此刻,在向上与向下之间的关键点,她是永恒不变的,或许甚至可以说是美丽的。她坠落之际,把她的头发向后吹的风,力道开始强了起来。
她撞击在混凝土上,寺院的天井传出回声,不过,当时在凌晨三点仍清醒的少数几位学生,并没有做出反应。当晚早些时候,艾蜜莉还跟大家坐在一起,她说的话不多,接着就悄悄离开了。也没人想到艾蜜莉不在场会跟天井的撞击声有关。在印度,这类嘈杂的声响很平常,所以他们没去查看,而她的尸体就静静躺在潮湿的青色月光里。这里是三千年前佛陀的悟道之地,这些学生都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能在此处冥想。为了向佛陀表达敬意,这座城市取名叫“菩提伽耶”,意思是“佛陀成道处”。过去十天以来,这些学生厉行禁语,在金色佛陀像的前方静坐冥想。严禁说话,令他们心烦意乱。最后,当他们终于可以再度使用自己的舌头时,便兴奋地熬夜聊天,像是夏令营最后一天的孩子们。
艾蜜莉死时,离她不过十英尺远的我已经熟睡了一小时,我睡在白色蚊帐里,安然梦见回到家乡妻子那里。接着,某个人推了我的肩膀,我睁开眼睛,看见一位蓄胡子的学生,是个纽约人。他惊慌失措地说:“艾蜜莉躺在地上,她没呼吸了。”我凭直觉做出反应,马上起身,穿上蓝色牛仔裤和褪色的衬衫,冲到天井。
史蒂芬妮——本课程的另一位负责人——把艾蜜莉的尸体滚到橙色的露营用睡垫上。艾蜜莉的右眼淤青,血液濡湿了她的头发。因为惊吓过度,史蒂芬妮连我出现了也没顾得上招呼,她正摸黑努力想要让艾蜜莉起死回生。她正把手放在艾蜜莉的红色亚麻衬衫上进行胸部按压急救。医疗用品袋里的东西散落在露水打湿的草地上,到处是凌乱的注射器和绷带。史蒂芬妮每按一次艾蜜莉的胸骨,艾蜜莉嘴里的血就随之溢出。史蒂芬妮见此情景,嘴唇向上噘,表情扭曲。艾蜜莉仍旧没有脉搏。
此时,寺院里的每一个人都赶了过来,聚集在现场。某位棕色长发、带有澳洲腔的女人,一见血就随即昏倒。与此同时我打了电话给人在美国的课程创办人,告知坏消息。
挂断电话后,我写着笔记,打算打电话给艾蜜莉的家人,此时三名学生把她抬进生锈的救护车。那是寺院的救护车,用来给乡民提供医疗服务,今晚却用来载送她的尸体,穿越干燥的农田和熙熙攘攘的军事营地,驶向唯一的一家医院。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二日凌晨四点二十六分,艾蜜莉抵达了伽耶医学院(Gaya medical college),到院时已经死亡。
上午十点二十六分,我有如老了一岁。她遗留在房外阳台上的日记,写满了比喻性的文字,让我怀疑她是自杀的。十天的静心冥想,加上造访半个地球外的国家所带来的文化冲击,显然并不适合她。不过,跟接下来所要面对的艰难任务相比,她的死因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她家位于八千五百英里外的新奥尔良,返家的头几段路程就是要穿越印度乡间干燥不毛的荒原。前一天晚上,圣城瓦腊纳西的铁路枢纽附近恰巧发生火车意外,通往伽耶的铁路中断,而当地机场也似乎没兴趣帮忙安排载运尸体。
红色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之际,两名警察出现了。他们穿着绿色卡其制服,髋部佩有半自动手枪,蓄着翘八字胡。他们已经在医院看过尸体了,现在是过来问话的。
“她有仇家吗?有没有人嫉妒她?”警长米斯拉问道。他超过六英尺高,高大的体型引人注目,肩章上有两颗银星。他怀疑是谋杀。
“就我所知,没有。”我回答。他那怀疑的语气让我全身僵硬。
“她的伤……”他停了一下,不确定自己的英文用词是否正确,“范围很大。”
我带他去看她坠楼的地点,那里有一堆医疗用品,还有急救用品的残余碎片,那些是我们努力救她未果后剩下的。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些东西,没有再继续提问,反倒请我去医院,他要我做一件事。
数分钟内,我坐上了警用越野车的后座,同行的还有米斯拉和三位年轻警卫。那些警卫不超过十九岁,泰然自若地握着二战时代的冲锋枪。我们在路上颠簸行进之际,一支银色枪管的老旧冲锋枪就指着我的肚子,我担心那把枪随时有可能会走火,但是我什么话也没说。
坐在副驾驶座的米斯拉转过身来,露出微笑。他似乎很高兴能帮助美国人,这件新鲜事打破了他那平淡无奇的警察工作。他问:“美国的警察是怎么工作的?跟电视上一样吗?”
我耸耸肩,我真的不知道。
我看见另一辆越野车在对向车道高速飞驰。隔着满是尘土的挡风玻璃,我看到了一位棕发的白种女性身影,是史蒂芬妮。当两辆越野车擦身而过时,我和史蒂芬妮对望一眼,她看起来很累。
数分钟后,我们抵达了人潮拥挤且道路坑坑洞洞的伽耶市区。虽然伽耶是比哈尔邦(Bihar)的大城,但是“开发”二字仍是遥远的梦境。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封建制度却仍是此地的治理原则。当今管控此城者,乃是大君时代治理此地的后裔。布满黑泥的大猪在街上漫步,在垃圾里嗅闻翻找食物,还发出呼噜声,要行人别挡它们的路。有的大猪还在肉店旁边等人喂食。我们快速驶过时,屠夫把剥了皮的羊头切成两半,把不要的碎片丢给店外的猪吃。一头猪吸起一条丢出的肠子,像在吸一根意大利面。
越野车转了三个弯之后,进入伽耶医学院区,停在一栋混凝土建筑物的前方。遮阳篷上漆了亮红色的粗体字:“CASUALTY(急诊)”。在印度医疗机构的分类里,这家医学院连个增补都称不上,这个脱离常轨之处,只能吸引印度最平庸的人才。伽耶医学院兴建于殖民时期,当时是由戴着遮阳帽、身上满是晒斑的英国官僚治理这片土地。如今,伽耶医学院却连一丁点儿帝国建筑的风格都荡然无存了,校区点缀了几栋形状矮宽的混凝土建筑物,以拮据的政府预算兴建而成。印度大部分地区都已经乘上信息技术的火箭突飞猛进,但比哈尔邦仍坐在发射台旁的大看台上。
我跳出车外,米斯拉带我进入病房。一名穿南丁格尔白色制服、戴帽子的护士向我投以麻木的眼神,她对悲剧已经习以为常。她的对面是混凝土制成的尸体放置台,上面就是艾蜜莉的尸体,艾蜜莉已在破旧的毛毯底下冷却。晚上,护士拿来几片薄纸板做隔挡,挡住好奇的眼光。瑞克——在寺院诊所担任义工的美国人——从入夜后就一直守在她的尸体旁边。
米斯拉把那块避免艾蜜莉受苍蝇侵扰的裹尸布拉开,她那饱受重创的遗体露了出来。撞击地面后几小时,她身体温度下降了十几度,降温后,她的伤口更为明显了。她眼睛下方的皮肤有深色的血渍,脖子根部鼓胀,看起来像是在坠落时弄断的。她手臂上的痕迹在史蒂芬妮施行心肺复苏术时是隐而不显的,现在却清晰得有如军队的迷彩。
米斯拉要我跟他说,我看到了哪些东西,他好把她的私人物品登记在警方档案里。警方合法羁留她的尸体,要是有东西不见了,米斯拉就要负责。她穿着亚麻衬衫和在德里观光市场买的长裙,右手腕则戴着一串木珠手链。
“什么颜色?”他问,而且再度注意自己的英文是否正确。
“衬衫是lal,红色的。裙子是neela,蓝色的。”我说。他用圆珠笔在本子上写了写。伤口跟服装上的痕迹符合。
就算他当时正想着这两种颜色是很怪异的搭配,也没能想多久。他的思绪被轮胎压到碎石子的声音打断了,有人来了。
屋外,新闻记者已经停好了两辆小型的Maruti Omni厢型车,他们像马戏团小丑那样从车内涌到停车场,一堆的人、音响器材、B级手提摄像机。记者的存在,有如这所医学院,证明了边缘化的现象。在印度的其他地方,新闻频道相互争抢报道独家新闻;不过,在这里,新闻报道有如团队活动,以今天的新闻报道为例,他们还一起搭车前来。十六个人尴尬地站在空荡荡的厢型车旁边,两位制作人根据摄像机和麦克风上的单色标志分配设备。
米斯拉走了出去,阻挡他们前进,或者是在跟老友打招呼也说不定。我站在病房里,几乎听不到他们提高嗓门的声音,但是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透过铁门偷看外头,想要看到制片人把藏在掌心的黄色卢比纸钞塞到警长米斯拉手里。但我没看见交易过程,不过我知道,只剩下几秒钟的时间准备,他们要过来采访了。
我把医院床单拉回去,盖住她的脸孔,然后走到病房的前头。相机闪光灯闪了六次之多,我一时之间什么也看不见。摄制小组把热烫的黄色灯光打在我的额头上。接着,新闻记者把一堆麦克风放在我的面前,对我发射出一连串的问题。
“她是怎么死的?”
“她是被杀的吗?”
“是自杀吗?”
然后,来了个回马枪:“你是谁?”
这些问题都很合理,但我不予回应。过去六小时以来,我的美国老板一直在尝试联系艾蜜莉的父母,我还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听到消息了。也有可能在还没联络上他们以前,美国新闻频道就已经抢先报道了。
现在,艾蜜莉这个人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尸体所代表着的问题。我们努力拯救她的生命时所存在的迫切感已经过去了,现在留下的是死亡所带来的一连串必然。她留下的肉身脆弱、易腐,而且不知怎的,许多人开始关注起她的遗体来。
“无可奉告。”我一面说着,一面眯眼望向摄像机无情刺眼的灯光。问题还在不断涌来,不过记者们的声音渐渐没那么急迫了。某位摄像师的眼睛闪烁了一下,他们想要找角度拍她的尸体。我举起手臂挡住他的镜头,但是穿着红色Polo衫的男人抓住我的手臂,准备将我推开。我拉着他,但失败了,他一放手,我的身体转了向。一瞬间,他们已经经过我的身边,把盖住她脸庞的裹尸布拉了开来。
在刺眼的灯光下,她眼睛下方的血液变成暗紫色。那道伤口穿过颅骨裂缝,进入脑袋里。在印度的电视上,死亡这个重要角色仅次于珠光宝气的宝莱坞名人。覆盖住的尸体与脚趾标签的高雅画面是用在美国报纸上的,然而在印度的新闻里,会先以无休止的个人悲剧蒙太奇手法,拍摄荒谬丑陋的情景,随后拍摄死者的脸孔,头舌下垂的骇人画面。印度的死者可不会害怕上镜头。如果我的责任就是保护艾蜜莉,那么我的任务失败了。
今晚,印度各地电视会播出最新的新闻快报:
美国学生死于菩提伽耶禅修中心。
警方怀疑是他杀或自杀。
在印度,不是每天都有美国人死亡。今天,她成为尸体后的名气会比她活着时大。在这一则新闻被下一则新闻取代以前,全国的注意力都会放在这个地点上。十亿人都有机会目睹她那张失去生气的脸庞。
我努力挤回摄像机前,但是记者们已经开始走人,他们已经得到需要的东西了。
警长米斯拉用左手平衡着一根沉重的手杖,他脸上的表情有如万花筒,同时表达出“你的五百卢比很有用吧”和“我不知道这些家伙是怎么绕过我的”。不过,这对记者而言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开始鱼贯而出,进入等在那里的厢型车。司机发动引擎,他们冲往禅修中心,去偷看事故现场。
一分钟前,病房里还像马戏团似的,现在却有如坟墓般安静。我没别的事可做,只能继续守夜。米斯拉向我微笑,耸了耸肩,然后回到外头的岗位上。我再度一个人陪在艾蜜莉的遗体旁,新的现实来到眼前,我的学生惨死在印度的偏远地区,现在我必须负责将她的遗体送回美国。她死后六小时,她遗留下的躯壳与包装不佳的厚肉块之间,所差甚微。气温有可能在正午达到华氏一百度,要阻止肉身的腐败过程,所剩时间不多。
我到医院的柜台,身穿南丁格尔制服的护士说,医院没有冷冻设备。此外,我必须等到政府规定的解剖验尸过程完毕后,才能取回她的尸体。护士建议我坐在尸体旁边等医生来。
我等了又等。
终于,有一辆小救护车停在病房外,车的品牌和型号跟记者用的那辆厢型车是同一款。这两种车唯一的差别在于救护车拆除了后座,以便放入轮床。两个男人出现了,他们穿着领尖扣在衬衫上的皱巴巴的商务衬衫,还有破旧宽松的长裤,说是要把尸体送去解剖。
他们粗手粗脚地把她放入救护车后面,发出砰的一声闷响,接着在土路上开了半英里。我跟尸体一起坐在车子后面,车子迅速穿越医学院区,最后终于停在一栋又小又破旧的政府建筑物外头,铝制屋顶上面还有几个大洞。门上的牌子以印地语写着“解剖教室”。解剖教室看来像是已经十年没人在这里上过课似的。几处高起的平台上设有几排座位,想必是为了让学生更能看清楚解剖的尸体。中间几排的一些椅子颠倒着放,整个空间都布满了灰尘和鸽粪。教室的前面是黑板,还有一张冰冷巨大的黑曜石桌。他们把艾蜜莉的尸体放在石桌上,用挂锁锁住门。
“医生很快就会来了。”他们说完就退到角落后面,抽小根的手卷烟。我注意到建筑物外有遭弃置的衣物和好几大丛的头发,显然是先前解剖留下的。
他们抽完烟后,其中一人带我去附近的一栋建筑物,这栋建筑物比解剖教室大多了。他们说,医学院院长在这里等着要见我。我到的时候,达斯医生正对着一大堆文件烦躁地扭着双手,他那一小片乌黑的遮秃假发略略戴歪了。
达斯医生身兼二职,不但要处理医学院的日常事务,还要为警方解剖尸体。有课时,他教授医学院新生有关法医分析的全部细节,这也表示要在数十具送到他的太平间来且无人认领的尸体上重现伤口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很受欢迎的一堂课,所以这里才会有四个陈列柜,里头装满致命毒药与潜在的杀人武器,比方说,剑、匕首、弯刀、螺丝刀、钉了钉子的板球拍等。陈列柜最底下的架子摆了一叠犯罪现场照片,呈现的是尸体处于不同腐烂阶段的情况。我们谈话时,他不时凝视窗户上挂着的医用骨骸。
“这件案例很特殊,”他开口道,“死在这里的外国人并不多,所以我们的处理方式必须十分谨慎,有很多人在看着。”
身为学生的艾蜜莉,只不过是穿着印度服装踏上心灵之旅、追寻圣地的少数美国年轻女性之一。现在她死了,成了一起迅速蹿升的国际事件,警方的官僚体系、大使馆的走廊、承担白花花的数万美元将遗体遣送回国的保险公司,都在关注这起案件。
而我心知肚明,一切就取决于达斯医生的死亡报告。如果他认为尸体上的伤口可能是他杀所致,官方规定尸体必须交由警察看管,直到调查完毕为止。然而,这所医学院没有设施保存尸体多日,把她留在这里的话,尸体会严重腐坏,届时航空公司将会拒绝将尸体空运回美国。
另一方面,如果他认为死因是自杀,警方就会快速结案。然而,他解释道,她的家人——现在肯定知道她死了——信奉天主教,不会接受她自杀一事,因为天主教认为自杀者的灵魂会永受地狱之火灼烧。事实上,他们可能会要求额外调查,证明另有死因。
他缓缓摇了摇头。
“你看看,真是两难,”他忧虑地说,“要是她根本没死的话,事情就容易多了。”
活生生的肉体与无生命的尸体之间,有一条细到无法察觉的界线。死亡的问题就在于,一旦跨越了那条线,所有应对人体的方法规则也随之改变。达斯医生叹了口气,望向房间另一端的助手,对方正拿着两个空的宽口玻璃罐。
“也许我们该开始了。”他把手掌放在办公桌上,费力撑起身体。随即抓着一只黑色的药袋离开办公室,进入走廊,独留我一人面对几个装满医疗教学用品的陈列柜。
我没跟他走,反而望着那个末端钉了一根生锈铁钉的板球拍,它就挂在可怖的书柜里。铁钉的尖端弯了,一圈干硬的血迹轻轻垂在木头上。一想到达斯医生用板球拍打在无人认领的尸体上,重现伤口的模样,我就不禁全身颤抖起来。接着,仿佛在我已经忘记手机的存在时,口袋里的手机开始震动了起来。
在线路的另一端,半个地球之外,穿越一个海洋的嗡嗡声和噼啪声而来的是人在纽约的负责人的声音:“斯科特吗?要请你帮一个忙。”
两天后,橙色的太阳从恒河平原表面懒洋洋地浮起,缓缓上升,跃上天空。时间还早,但我没睡,筋疲力尽,眼睛布满血丝。过去两天,我在城里搜寻可靠的冰块来源,好让艾蜜莉的尸体保持冷却。最后在寺院的帮助之下,我将数百磅冰块倒入她的棺材里。棺材是我们在木工场做的。在倒冰块的时候,我尽量避免去看她的尸体。我们又一起把尸体移动了两次:先是从验尸室移到寺院,然后再移到一间小型的太平间里,在这整件事的一开始,院方的行政人员竟然绝口未提其实医院里有小型的太平间。
美国的法医专家不相信印度的法医,所以在纽约的老板要我替艾蜜莉的尸体拍照,送回美国进行独立分析。我握着从学生那里借来的数码相机。虽然她已经在这里解剖,但是解剖结果永远无法确定。老板跟我说,要是没照相,她的家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尸体可能永远无法离开印度。
一辆警方越野车抵达我的旅馆,载我去医学院。我坐在一名警察旁边,他佩着冲锋枪,脑袋向后倾,人半梦半醒,眼睛忽开忽阖,似乎没注意到枪管又再度指着我的腹部。我不由得心想,又经历了同一个画面。半小时后,我们抵达验尸室,那个警察还在睡觉。验尸室用挂锁锁住,一名头发灰白的助手翻弄着钥匙,他的手指似乎无法控制地一直颤抖。他暗示我,只要有一百卢比,他的手就不会再抖了。
我努力绷紧神经,料到自己会心生排斥感。一想到要目睹她被解剖后的遗体,直叫我恐惧不已。尸体是一回事,目睹外科医生处理过的尸体又是另一回事。我不禁想,他们拿出的东西会不会不只是她的器官而已,会不会有更重要的东西不见了。我的胃不禁翻腾起来。
一分钟后,我进入验尸室,盯着被摆在金属轮床上的她。
医生们已经用粗陋的工具把她从上到下切割成两半,从脖根一路切到骨盆。他们锯开肋骨,检查心脏。为了查看脑部情况,还横向锯开额头和颅骨。他们剥开她脸部的皮肤,额头盖住眼睛,头皮往后拉。不出所料,他们看见颅骨内部积血。血液压迫脑部,足以致死。
不过,外科医生并未就此停止。他们切了几片肝脏、大脑、心脏、肾脏,以便排除下毒的可能。为判定她是否遭到过强暴,他们还取出了部分的阴道、子宫颈和输卵管。他们把所有的器官集中放在三个宽口的大玻璃罐里,罐子上标示着“内脏”。然后,快递员把这些玻璃罐送到三百公里外的实验室。最后,他们再把她缝合起来,缝线既宽又不雅。
调查结果就跟解剖过程一样残酷。验尸报告列出的正式死因是:“头部外伤导致休克出血,伤口看似从高处落下所致”。
我的感觉跟之前预期的不一样。有一种不同的——或许是更恼人的——情绪从我的胃部蹿起,我的脸颊发烫。
我觉得很尴尬。
她的伤口并不会让我感到不安,我对伤口所做的心理准备比我自以为的还要周全。令我痛惜不已的反而是她的裸露。
艾蜜莉在世时,是个二十一岁的美丽女人,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期。她优雅健美的身材和仪态,足以让其他女孩子羡慕不已,而她本人却浑然未觉。她做瑜伽已有多年,身体处于生理健康的高峰,肌肉健美,皮肤完美无瑕。我所知道的艾蜜莉个性坚强,是个对周遭一切处之泰然的人。
不过,在这里的她,裸着身体,已然死去。我现在所了解的艾蜜莉,比我想要了解的还要多。当她从机械装置里滑出来的时候,助手和我共同目睹了她私密的部分,那些原本是她的爱人才能享有的视角。空气中几乎可以感觉到她的内脏与某种防腐剂混合起来的味道;对她的腿、臀、乳房、胃的侵犯,似乎应该禁止才对。可是,死者没有秘密。艾蜜莉一停止了呼吸,就失去了隐私。她跨越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支配她的法律和习俗跟一周前的不同。在这个世界里,她的双亲需要自己女儿的裸体照片。在这里,一群男人对着她的内里研究、辨识、思索,而她丝毫不退缩。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人生中最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与自身肉体的关系。死亡所带来的最后耻辱就是失去对自己肉体的控制。
躺在台子上的她的身体躯壳,跟她出生且伴之成长的身体比起来,少了一些东西。伤口让她的体形受损,不过,医学院的病理学医生摘取器官所造成的破坏还要更大,她被切割,内里的一部分被送到该国另一端。这具尸体正是我们即将要诉说的故事,正是她的双亲哭泣的原因。但是,要把这剩余的她称作“艾蜜莉”,或者甚至是“艾蜜莉的尸体”,等于是在说谎。无论这要称作什么,都是残缺不全的,而且再也无法回复到完整的状态。
我们让死者经历了奇异的蜕变。此处,在这个台子上,她的皮肤是个皮囊,重要的内容都已经取出,利落的缝线缝住了她空洞的体腔。死了的她是一个物件,有待切分打包后送给要用某部分谋利的人,比方说,将她的影像贩卖给网络的记者,负责解剖的医师,想要拿回全尸的双亲。现在,我也成了链子上的一环,我是死者的搜集人和故事的讲述者。无论过去的艾蜜莉是谁,现在都已经消失了,留下的只不过是她的零件。每一个人的故事结尾都是一样的,无人能成为例外。
我检查了测光表,调好了相机,准备拍照。我对着她的身体直按快门,快速连拍。我把她身体的每一寸都拍了下来,从她的脚趾一直拍到额头深长的伤口。再过不到一小时,她就会在前往德里的飞机上,接着,再从德里飞往路易斯安那,最后她将穿着双亲特地为她买的浅蓝色纱丽,入土为安。一位助手进来,抬起她的尸体放入一辆正在等待的厢型车里。但我知道,有一部分的我将永远无法离开这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