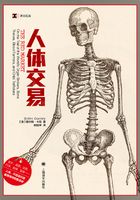
第2章 导言:人与肉
我的体重接近两百磅,棕色头发,蓝色眼睛,牙齿齐全。就我所知,我的甲状腺输送适量的激素到全身动静脉总计十二品脱的血液里。我身高六英尺二,所以有很长的股骨和胫骨,以及牢固的结缔组织。我的两个肾脏功能正常,心脏也以每分钟八十七下的速度稳定跳动着。从上述指标算来,我大约价值二十五万美元。
我的血液可分离成血浆、红细胞、血小板和凝血因子,以拯救手术台上的患者性命,或者阻止血友病患者的血液不受控制地流出;我那些连接关节的韧带,可以从骨头上刮下,移植到奥林匹克运动员受伤的膝盖里;我脑袋上的头发可制成假发,或可还原成氨基酸,作为烘焙食品的发酵剂使用;我的骨骼可作为生物课堂里最引人注目的存在;我的主要器官,如心脏、肝脏、肾脏等,可以让器官衰竭患者延长性命;我的角膜可切下,让盲人恢复视力。而即使是在我死亡后,病理学医生也可以取出我的精子,帮助妇女受孕,而妇女产下的婴儿也同样有其价值。
我是美国人,肉体可以高价卖出,但假使我是在亚洲国家出生的话,价格可就低多了。医生与掮客——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通过市场运送我的身体部位,光是提供这样的服务,就能赚上一大笔钱,而且收入囊中的金额远超过身为卖家的我。原来,无论是在器官市场里,还是在鞋子和电子产品市场里,全球供需法则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技工能够把老旧的汽车零件换成新品,替嘎吱作响的接合点上油,让引擎再度运转;同样,外科医生也可以把坏掉的器官换成新的,延长患者的生命。年复一年,技术藩篱愈来愈低,工序也愈来愈便宜。不过,人体跟机器有别,不会有一堆高品质的二手人体零件供人取用。于是,近年来有许多人尝试制造人工心脏、肾脏和血液,但是跟真品比起来,实在没什么吸引力。人体实在是太过复杂精密,目前工厂或实验室皆尚无能力复制人体。这就表示,为因应人体器官需求,目前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活人和刚去世的死者当中寻找原料来源。
我们需要大量的人体原料,来为医学院提供尸体,让那些未来的医生能够充分学习人体解剖学;领养机构把第三世界的成千上万名儿童送到第一世界,填补美国家庭里的断裂;制药公司需要活人来测试下一代的超级药物;美容产业每年要处理数百万磅的人类头发,以因应消费者对新发型永不休止的渴望。还说什么热带岛屿上穿草裙的食人族呢,再也别提了吧,当今人类对人肉的胃口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大。
但是,若决定人体可以在开放的市场上交易,就会产生奇怪的魔力。多数人直觉上知道,人类的特别之处不只是有形的存在(小至赋予质量的原子和夸克,大到维系生存的复杂生理结构),还有那种仅会伴随生命而来的存在感。在本书中,为了让读者理解我的文字,我假定人体是有灵魂的。[1]灵魂离开后,人体就会变成一堆物质。
虽然我们情愿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神圣的,不是市场上可以随意翻找的货品,但是人体器官的销售活动其实很热络,每年器官交易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全球人口将近六十亿,供应量可说是相当充沛。就全球的供应量而言,有将近六十亿个备用肾脏(要是够冷血无情的话,也可以说有一百二十亿个),还有将近六百亿升的血液,角膜的数量也足以填满一整座足球场。唯有一点会妨碍交易者赚取如此庞大的潜在利润——交易者无权开采资源。
以儿童领养市场为例,目前,若某个家庭决定要将国外的贫困儿童带回国内养育,他们对孩子的身份其实只有模糊的概念,因此在寻找心目中理想的婴儿时,只会根据可用的婴儿市场来缩小期望范围。他们会浏览国际领养机构在网上发布的候选名单,阅读报纸上对育幼院里身心匮乏的儿童所做的报道,然后费尽心力决定哪些具体的特质会让自己起了领养的念头。
当然了,那孩子将来某一刻就会成为家里的一分子,不过实际上要领养到孩子的话,就得涉及由中间人和腐败的政府官僚所操控且又往往黑幕重重的供应链,而且许多中间人和官僚看待儿童的态度,也只比看待尸体要好上一些而已。唯有等到那个家庭把孩子带回家后,那孩子才能从抽象的概念变成真正的人。
不过,我们对这一主题所抱持的道德立场并不重要,因为人体毋庸置疑就是一种商品,令人不安的商品。人体作为产品时,并不是在工厂里由穿着无菌衣的劳工组装成的新品,而是像废料市场里的二手汽车那样取得的。在你开支票取得人体组织以前,某个人必须把人体组织从一小个带有人性的东西,变成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废料的价值是以金钱计算,但人体不仅是以金钱计算,还要根据血统,根据获救与失去的生命所具有的无可言喻的价值来计算其价格。购买人体就等于是担负了人体来源的责任——在伦理道德方面要承担,在前任拥有者的生理史与基因史方面也要承担。这是一桩永远都不会结束的交易。
在法律上或是经济上,有三种市场:白市、灰市、黑市。黑市所交易的是非法的商品和服务,例如走私的枪械和毒品;而非法制造的DVD和未课税的所得则属于合法的灰色区域;白市就是每一样合法的与台面上的东西所隶属的领域,例如从街角的杂货店购买的食品杂货,每年要尽职送缴的所得税等。这三种市场有一个共通点:交易品都有现实世界的价值,可轻松换算成金钱,金钱一经易手,交易就结束了。可是,人体市场却不一样,因为顾客能重获性命与家庭关系,这都要归功于供应链。
欢迎来到人体市场。
人体市场所推出的是充满矛盾的产品,社会对人体的忌讳,与个人对活得长久幸福的渴望是抵触的。假使商品市场是用代数计算的,那么人体市场就是用微积分计算的,每一个等式都含有零和无穷大的数字。人体市场的存在,是因为供应者和买家都发生了可改变人生的大事。无论买家承不承认,总之,接受了别人的肉体,就等于是一生都亏欠了供应者。
由于有了这一层关系,加上人们在处理人体时不喜欢采用赢利主义的用语,因此所有的人体市场在交易期间都采用奇特的利他主义语汇。人们不是卖出肾脏、血液、卵子,而是“捐赠”出去的。养父母不是在扩大家庭规模,而是在领养贫困的孩童。
然而,尽管有这些连结,人体和人体部位的金钱价值依旧稳固不坠,而且赤贫地区增长迅速的人口,也是供应量接近无限的一部分原因。
在埃及、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一整个村落都在卖器官、租子宫、签字出让死后的身体权的情形并不少见,当中包含被胁迫的交易,也有双方都同意的交易。交易人体部位的中间人——通常是医院与政府机构,但有时是最丧尽天良的罪犯——会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买进,同时还向买家保证人体部位来源合乎道德。虽然采购过程有时令人厌恶,但是最终的销售往往是合法的,而且其拯救人命的微妙道德层面,也往往让这类交易获得认可。至于犯罪行为,则用“利他主义”的理想掩盖过去。
在人体市场产生交易行为,我们得要感激人体部位来源与最终结果之间的所有连结,这点和我们人生中所从事的其他交易行为并不相同,其他交易很少会像购买他人身体部位那样,立即会有红旗举起进行道德示警。至于如何才算是“合乎道德的来源”,这是人体市场中每一位潜在受益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果我们需要自己的身体方能存活,那么身体的部位怎么可以给别人呢?以活人捐赠器官为例,患者怎么可以有权获得健康者的器官呢?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才能把第三世界的孩童送到第一世界呢?人体交易无可避免有其令人厌恶的社会副作用,亦即社会阶层高的人可以取得阶层低的人的人体部位,从来不是反过来的。即使没有犯罪因素在内,但是未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会有如吸血鬼,夺取贫民区里穷困捐赠者的健康和气力,把他们的身体部位送到有钱人那里。
支持人体交易不设限的人往往会说,愿意贩卖自身组织的人可以从交易中获利,那笔钱应当能够让他们从贫困的深渊跃升至较高的社会地位。毕竟,我们难道不是都能对自己的身体遭遇做出决定吗?这当中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人体组织是社会安全网的最后一道防线,贩售人体组织可以当成是救生索,让人脱离绝望的情境。可是,现实在于,贩售人体与人体部位者很少能目睹自己的生活获得改善,而且社会学家很早就知道改善生活不过是幻想。[2]贩售身体部位无法获得长期利益,只会招来风险。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蹿升会跟人体器官的蹿升速度一样快,那就是一次卖出整个身体的时候,也就是婴儿进入国际领养市场的时候。
全球的孤儿多达数百万,表面上看来,领养可减轻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儿童无一例外会从社会边缘的不稳定处境,进入经济稳定且有关爱的家庭里。然而,领养市场如同其他市场,也面临着短缺的压力。西方国家——占国际领养案的大多数——想要肤色较浅的婴儿,造成孤儿院偏爱某些种族。在美国国内,孤儿院成了一种不幸的透镜,可观察到美国的种族政治现象。白人孤儿往往没多久就会被热切的家长领养,黑人孤儿则往往是在领养系统里长大。
在美国以外的国家,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而衡量严重程度的标准并非在于种族地位,而是儿童的健康问题。因为在印度、中国、萨摩亚、赞比亚、危地马拉、罗马尼亚、韩国等国,资源不足的孤儿院会使儿童的发育受到阻碍。在这些国家以及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养系统的经营模式跟香蕉市场很类似,这点听来实在令人不快。假使儿童或香蕉存放得太久,在市场上的价值就不太高了。儿童在机构里待的时间愈短,就愈有可能进入领养家庭,而孤儿院往往能从每一件国际领养案中,收取相当数额的领养费。当儿童通过领养来提高社会地位时,若库存量与转让契据有过大的差异,就表示领养机构需要提高周转率,或采用创新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儿童。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有合法和非法的方式。
截至一九七〇年代,全球各地都在尝试人体部位的开放贸易。大家最先争论的就是人体部位买卖是否合法,而最无争论余地的就是血液买卖的争议。一九〇一年,维也纳人、科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Karl Landsteiner)发现了四种血型的存在,终于开启了安全输血的时代。在那之前,接受输血就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赌,有时存活,有时痛苦地死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搔着脑袋,既困惑又沮丧,他们不知道血型不相容会让血液凝结,造成患者死亡。兰德斯坦纳发现血型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人对人的直接输血进行了数十万次之多,战场上的士兵纷纷得以幸存下来。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血库的贮藏量已经足以让血液成为一大战争武器,能让士兵活下来打仗。采血诊所提供现金给愿意献出一品脱血液的人,借以因应激增的需求。血液随时可用,有一个立竿见影的好处——医生能够施行比以前更大面积的手术,失血不再是手术过程的障碍。这样的发展更带领了整个医学领域往前大步迈进。
此外,这也表示采血中心成了一门大生意。截至一九五六年,美国境内诊所每年购买的血液量超过五百万品脱;十年后,贮藏量达到六百万品脱。采血点在各大城市外围的贫民窟里迅速兴起,普遍得就像是今日贫民窟里的支票兑现点和当铺。在印度,各种全国性工会与政府协商血液价格,不久之后,职业捐血人在印度次大陆各大城市的供血量遽然增加。
当时,血液的供应可救人性命,很少人会为了供应链的道德与否感到困扰。直到一九七〇年,情况才有了变化。当时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担心人体市场会造成大家无法平等地获得先进的医疗,而蒂特马斯对此议题所抱持的道德立场,则是受到自己的国家——英国——的影响。英国在二战期间发明捐血活动,数百万人无偿捐献自己的血液,为战争尽一份心力。即使是战后,英国医院所取得的血液也几乎不用买,英国人认为献血是爱国的表现,是应尽的义务。蒂特马斯在《赠与关系》(The Gift Relationship)一书中,曾比较美国的商业体系与英国的利他体系,并提出两大论点。
第一,蒂特马斯证明了购买血液会导致血液供给里的肝炎案例增加,迫使医院与血库日趋采用胁迫手段来增加人类血液的贮存量。购买血液不仅是危险的行为,也是剥削的行为。商业采血会造成国家寻求尽可能便宜的血液来源,开始要求囚犯捐血,蒂特马斯把这种情况比作蓄奴制的现代版。蒂特马斯说,其他的人体组织市场也有可能会迅速出现同样的剥削现象。
第二,蒂特马斯主张,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创造出完全以利他性的捐赠为基础的体制。他认为,血液捐赠体制不仅能拯救生命,还能为医院创造利润,此外,更可以构建一个个共同体。他写道:“作为社会一分子而替陌生人付出的人,自身(或其家庭)最终都能作为社会一分子获益。”[3]对蒂特马斯而言,人体与人体部位应该仅能作为交换的礼物,你可以直接把它想成是血液社会主义。
尽管有主张血液商业化的游说团体极力反对,但是显然大家采纳了蒂特马斯的意见。于是美国通过法律,让自愿捐赠成为常规。付钱购买任何种类的血液,会被视为胁迫行为,且要处以高额罚款。(不过,应注意一点,并非所有血液都是生来平等的,血浆就是当中的例外,血浆比较容易在人体里再生,一直以来也是美国境内许多人经常用来赚外快的方法)而这股趋势蔓延到了其他的人体组织市场。
一九八四年,艾尔·戈尔(Al Gore)呼吁禁止付钱购买任一人体部位,并进一步协助该项国家法律通过。他在美国参议院的议员席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其中引用了蒂特马斯的这句话:“人体不应该只是备用零件的集合体。”之后,参议院便表决支持《国家器官移植法案》(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 Act),明令禁止贩卖人类器官与组织。世界各国也纷纷起而效仿。今日,除了少数几个显著的例外,凡贩卖血液、购买肾脏、为领养而购买儿童或死前贩卖自己的骨骸,在各国一律属于非法行为。此外,他们还针对自愿捐赠一事,设立了复杂的制度。人们在血库捐血,签署器官捐赠卡,在死后将身体赠给科学机构,这些全是免费的。理论上,以金钱交换人体部位者,可能最终会落到坐牢的下场。法律规定得一清二楚,购买人体是错误的行为。
只可惜,在人体生意的利润公平方面,法律有其不足之处。这个由蒂特马斯所勾勒且广为其他各国采纳的体制,有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个人无法直接买卖人体,但医生、护士、救护车司机、律师、管理人员等,全都能为自己提供的服务开出市场价格。患者或许没有付钱买心脏,却肯定支付了心脏移植的费用。实际上,心脏的成本转移到了取得心脏的服务成本当中。医院与医疗机构日趋从器官移植手术中获利,有的甚至将收益分给股东。供应链里的每一个人都赚到了钱,只有实际的捐赠者一毛钱也没拿到。在明文禁止购买人体部位后,医院基本上可以免费取得人体部位。
站在顾客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器官移植生意很类似剃须刀制造商吉列公司广为人知的经营模式。吉列公司剃刀的把手费用微乎其微,购买刀片的费用却很昂贵。肾脏移植的情况也是如此。患者自然是不能购买肾脏,但一个持有证明的二手肾脏,其移植费用却将近五十万美元。
一如其他所有的经济体系的情况,免费供应原料只会引诱人找到新的方法来加以利用。在美国,发生几种绝对紧急的情况时就会需要可移植的人体部位,例如肾脏衰竭。这向来是一成不变的做法,一般也都不会有人对此产生质疑。甚至有人在候补名单上竟然等了长达五年,这再次证明了器官严重供不应求的状况。不过,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四十年来,美国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OS)一直都在扩大现有的遗体捐赠者数量,却始终赶不上患者对新器官的需求,候补名单只会变得愈来愈长。因为当有更多的器官可用之后,医生会把那些新的、先前认为是不符资格的患者加入移植名单里。随着外科医生发现捐赠者捐出的人类材料可帮助更多的患者,移植技术和病人的结局获得持续改善。
然而事实上,器官的需求量并非固定不变,只是移植名单掩盖了这个事实。名单的长度其实是受可用器官总供应量的影响的,而需求则受供应的影响。好消息是,这种方式让许多人得以延长生命。但是,扩张的潜力也是无限的,这表示我们不仅要关注器官可能所具备的有益用途,也务必要了解一点,即器官摘取体制有可能会变得规模很大,且日趋采取胁迫手段。
打个比方,就像世界各国对石油产品的需求是无限的。石油能源的创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经济、科技、社会收益,车辆的运用使得距离大幅缩短,夜晚有灯光,冬天有暖气。不过,钻探及耗尽这类产品,对人类而言可就不一定是件好事了。
蒂特马斯模式的第二个缺陷,在于他没有对医疗隐私权的基本标准做出解释。有关当局或许能够在它们的记录中追查到一个捐赠者,但捐赠者的资料都是封存起来,不受公众监督的。捐血者的奉献救了手术患者一命,但医院以外的人根本不可能找出捐血者的身份。血液被抹去了捐血者的身份,标记了条码,倒入密封的塑料袋里。我们买的是血液单位,不是人体的一部分。主流的医疗逻辑认为若让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有了关联,有可能会损及整个体制,甚至也许会在第一时间阻止人们捐赠自身的组织。
如此一来,接受血液者不会觉得自己欠了某位捐赠者的人情,而是会笼统地感激血液捐赠体制,尤其是感谢动手术的医生。接受活体肾脏移植的患者,无论是活体捐赠或遗体捐赠,很少会知道是谁放弃了自己的一个肾脏。匿名虽是为了保护捐赠者的利益,却也会让供应链变得不透明。受赠者购买身体组织时,不用担心身体组织最初究竟是如何取得的。这样的医疗隐私是让人体部位得以变成商品的炼金术的最后一道手续。
对于任何市场,隐匿原料来源通常几乎都是个烂主意。人们说什么也不会让石油公司隐匿钻油平台的地点,也不会允许石油公司遮掩其环保政策。若钻油平台故障,导致数百万桶石油流入海洋,人们会要求石油公司负责。透明度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安全装置。
而站在一个犯罪企业家的角度来看,目前的人体组织摘取体制无疑是完美无比的,可以让他们肆无忌惮地彻底剥削。由于政策规定仅能捐赠身体组织,因此付钱买人体组织乃属违法行径,许多公司会像石油公司投资钻油平台那样,在移植器官的基础设施上投入巨额的资金,而实际的原料价格往往贴近于零。与此同时,重视隐私权的漂亮说辞,又让人无法得知人体与人体部位是经由何种途径进入市场的。匿名就意味着器官买家在购买人体部位时,可以不用担心来源,而且不会有人提出任何疑议。捐赠体系的结构把供应状况隐匿于道德伦理的帷幕后方,小心翼翼地处理掉道德伦理上的异议。匿名与捐赠是两记重拳,使得拿走利润的中间人得以掌控整个供应链,购买器官就像开支票一样容易。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调查了目前的人体组织摘取与采购体制所产生的问题。现今的人体交易,堪称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利润最高的人体市场。蒂特马斯的著作出版后的四十年里,全球化使得人体市场的发展速度和复杂程度都令人眼花缭乱起来,这不是在全盘控诉商业化,也不是在全盘拥抱商业化。我们就活在人体市场里,即使否认世上有基于人体组织的经济体制,人体市场也不会这么简单就消失不见。无论我们喜不喜欢,世上最受尊敬的一些机构确实私下或公开买卖人体,而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它们是如何进行的。
大体而言,我并未把注意力集中于人体市场里每天进行的数百万笔交易。因为假使没有移植技术、采血与领养计划,人类无疑会面临更可怕的后果。但我们无需关注人们在人体市场购买某部位之后过着快乐生活的幸福故事,因为那种故事讲的是世界对人体组织的需求。人体组织的如何使用并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人体组织是如何进入市场的。本书探究的是经济等式的供给面,若不了解供给面,就永远无法得知人体市场助长全球犯罪企业的速度究竟有多快。
利他主义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削弱了两者原本想要保护的高尚理想。人体市场供应链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有助于把人类变成各种部位。而负责买卖人体的掮客扮演了屠夫的角色,在他们眼里,活人就是各个人体部位的集合体。
二〇〇六年至二〇〇九年间,我住在印度金奈,这座繁华的沿海大城位于印度南部,离斯里兰卡北方只有数百英里。在这之前,我已经在印度待了几年,在遍地沙漠的拉贾斯坦邦(Rajasthan)以及达兰萨拉附近的大学研究民俗和语言。我知道自己想在南亚待上更久的时间,但并不确定自己将来是否要当个新闻记者。我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研究所毕业后,马上就开始了短暂的专业学术生涯,在印度教美国学生一个学期。
我负责的学生有十二位,我们行遍德里、圣城瓦腊纳西(Varanasi),以及菩提伽耶(Bodhi Gaya)这个朝圣中心。但在最后一站时,我的一位学生去世了,我和另一名负责人将她的遗体送回美国她的家人那里。我有整整三天的时间都陪伴在她的遗体旁,试图延缓那无可避免的腐败过程。那次是我最接近尸体的一段经验,她的遗体冷却变色之际,人之必死的肉体本质赤裸裸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她的死亡尤其让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每一具尸体都有一位利害关系人。她从人转变成物后,人们似乎纷纷露面,要求取得她肉身可利用的部分。大多数时间,我都在跟警方、保险公司、殡葬业者、家属和航空公司进行协商,讨论如何将她的遗体带回国下葬。
虽然我当时并未意识到,但是这件事开启了我对国际人体交易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发生了几起我很大程度上无法掌控的事件,才使得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主题。本书的第一部分便会直接讨论这起死亡事件,部分读者可能会觉得内容令人不安,但这是无可避免的事。
当时,在我的学生去世后,我便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教书了。因此,我开始在我位于金奈的据点,替《连线》(Wired)与《琼斯妈妈》(Mother Jones)这两家杂志写文章,也替几家电视频道与广播电台撰稿。我的报道内容涵盖了南亚的肾脏交易商、骨骸小偷、血液海盗、儿童绑架者所采取的经营手法。之后,我踏遍欧美各地,把最糟糕的情况记载下来。买家在购买人体部位前,必然会先有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可是在每一个案例中,买家大多不知道之前有哪些事件发生,这点实在让我诧异不已。
我认为人体市场很特殊,与一般经济体系不同,而这个想法始于我对印度人骨贩子与肾脏小偷所进行的调查,但这个概念涉及的不仅是被当作备用零件使用的人体。此外,不合时宜的利他主义与隐私权交织在一起,对丧葬业与领养产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一谈到人体这个主题,供应链总是相同的,这真是怪异。
我开始考虑将所有研究结果汇集成书之际,发现世上的非法人体市场比我想要涵盖的还要多。美国境内有好几起太平间窃尸大案,殡仪馆会将家属托付的遗体卖给人体组织供应公司,遭亵渎的遗体跟着就被大卸八块,用于移植手术和肌腱更换,但本书并没有提及这件事;有一些巡回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展览,据闻展览的是被处决的囚犯的塑化遗体,本书也略过了这类丑闻;有一份报告表示,英国有超过十万个脑垂体遭窃,用于制造人类生长激素,本书也只有简单提及;前一阵子,有报道指出,玻利维亚的一些连环杀人犯会把受害者的脂肪卖给欧洲美容品公司,用于生产高档面霜,本书也没有提到这件事。
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名单也跟着愈来愈长。从一九九〇年代中期至二〇〇〇年,以色列军队在交战中杀死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后,便会摘取尸体的角膜。甚至在更早以前,十九世纪初,欧洲地区缩制头颅的市场日益繁荣,造成南美洲境内的部落战争四起。想要详尽涵盖每一个人体市场,实在超乎我的能力。
而我只希望本书能让读者站在新的角度来看待人体市场。若能看出这些市场之间的共同点,或许就能想出办法,解决人体组织经济体的问题。罪犯在经济世界最黑暗的角落里行事,但罪犯的存在全是因为我们的姑息所致。我碰到的那些掮客,几乎是无所顾忌,用尽一切手段取得人体组织。他们隐匿了供应链,避免他人窥探打听。而他们背后的驱动力,正是资本主义的法则:低买高卖。
在所有者之间运输组织与人体,往往有利可图,但同时中间人也开启了通往滥用的危险大门。唯一能摆脱这些滥用的方法就是让阳光照进去,让整个供应链从头到尾暴露在外。每一袋血液都要能追溯到原始捐赠者,每一个肾脏都要附注姓名,每一个代孕子宫都要能查出代孕者的身份,而每一件领养案都要公开。本书各章分别探讨了不同的人体市场,并叙述了我所能找到的最突出的、利润最高的或最令人不安的情况,以便读者大略了解世界各地的各种人体市场。
目前,透过供应链追踪人体组织来源的权力,几乎都掌握在行政机关的手中。一般而言,这类机关往往资金不足,而且几乎都会跟他们理应监督的医院和掮客相互勾结。国际交易根本无人监管。本书所涵盖的每一个市场都充分证明了这类机关的失职。我们不该盲目相信它们会稳妥地管控人体从部位转变成商业产品的流程,我更主张交易记录应该公开,让大众知道。
彻底的透明化会招致许多不同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减少人体的总供应量。以英国为例,有一项新方案规定捐卵者的记录必须公开,这种做法几乎终结了捐赠者提供卵子给不孕夫妻的现象。现在,英国妇女前往西班牙与塞浦路斯购买卵子。
然而,采用透明化的做法后,那些不择手段取得人体的掮客就不再有机会插手了。如果买家能够追踪到原生家庭、寄送感谢函,就再也不会有人因其肾脏而遭人杀害或绑架;如果所有的领养案都是公开的,就再也不会有儿童遭人绑架,与父母分离;血液卖家再也不会被锁在房里达数年之久,就只是为了略微提高当地的血液供应量。
现在,该是停止忽视人体交易、开始担起责任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