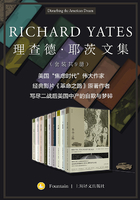
第20章 革命之路(18)
“不用亲自开车真是太舒服了,”吉文斯太太一边说,一边紧紧握住副驾驶的车门把手。每次去医院探望约翰都是由她丈夫开车,而每次她都不会忘记发出这样的感慨:能轻松地乘坐汽车是件多么惬意的事。她会指出,当一个人每天都开车,而且一开就是一整天的时候,这个人最盼望的就是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舒舒服服地坐在乘客的座位上。但是多年养成的习惯还是让她不得安宁。她不停地盯着路面,就像方向盘是握在自己手里;每次停车或拐弯时,她的右脚就会下意识踩踏座下的软垫。有时候她发现自己这么做时,只好把目光强行转移到路上的乡村景色,尽量放松背部肌肉,并且让自己的身体放松地躺进坐垫里。为了进一步展示她的自我克制能力,她甚至大着胆子把紧握着车门把手的手拿下来,安放在膝上。
“天哪,今天可真是个好天气,”她说,“你看树上那些漂亮的叶子刚开始转黄。你说还能有什么时节比初秋更美好呢?漂亮的色彩,干爽的空气;这种时节让我想起——亲爱的,小心啊!”
她的右脚用力踩向地上的软垫,整个身体弓成一个慌乱的抵御姿势,准备迎接撞击。她看见一辆红色卡车从正前方的一条岔路拐了出来。
“我看见它了,亲爱的。”霍华德不慌不忙地踩刹车,给卡车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来拐到前面去。他再次踩油门时,安慰妻子道:“你就只管放松下来,好吗?让我来操心马路上的事吧。”
“嗯,我知道了。我会的,对不起。我知道自己做了蠢事。”她深吸了几口气,然后把手交叠着平放在大腿上。她的双手紧紧靠在一起像受惊的小鸟。“每次要带约翰外出,我都紧张得像心脏里钻进了一只只蝴蝶,尤其这次跟上次外出已经隔了这么长时间。”
“病人的姓名是?”坐在前台接待处的女孩瘦得叫人不忍直视。
“约翰·吉文斯。”吉文斯太太礼貌地点头微笑,然后看着女孩拿着一支笔头被嚼过的铅笔,目光顺着铅笔滑下一长串用复写纸写出来的名字,最后停在“吉文斯,约翰”上面。
“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他的父母。”
“请您在这里签名,然后拿着这张单子到第二病区A病房。上楼以后向右拐就是了。五点之前把病人带回来。”
吉文斯夫妇来到病房的外部等候厅,按了电铃,便等待管理员出来接待。在等待期间他们只好闪闪缩缩地跟着其他探视者一起参观病人的艺术作品展览。其中一幅是病人拿蜡笔描摹得很像的唐老鸭画像,另一幅是以紫色和棕色调为主的耶稣受难景象,天空中的太阳,或是月亮,是猩红色的,颜色和耶稣肋骨里以一定频率流出的鲜血一样。
过了一分钟,一阵橡皮鞋跟摩擦地面的闷响从门后传来,夹杂着钥匙叮叮当当的碰撞声。门打开了,一个粗壮敦实、戴着眼镜的白衣年轻男人在里面说:“我能看看你们的单子吗?”他让探视者一对对地进入内部等候厅。这是一个宽敞、昏暗的房间,里面摆放了铺着亮丽塑料面的桌子和椅子,供不在特权名单上的病人的探视者使用。大部分座位都被占用了,只不过没几个人在说话。距离门最近的地方坐着一对年轻的黑人夫妇,手拉着手,如果不仔细看,很难判断那个男人是个精神病患者。除非你注意到他的另一只手死命地抓着镀铬桌腿,抓得指节都变成土黄色了,就像在惊涛骇浪中死死地抓着船舷。远一点,一位老妇女正在给儿子梳头发。年轻人看上去在二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他一边咬着一根剥好皮的香蕉,一边顺从地随着母亲的抚摸摇晃脑袋。
管理员把那一大串钥匙挂在裤子后兜的夹子上,沿着走廊往里面走,然后用洪亮的声音念出他拿到的单子上的病人名字。病房里传来各个广播频道交杂在一起的嘈杂声,但从走廊口看进去,只能瞥见一排打过蜡的油麻地毡,以及几张病床的铁支柱边缘。
不一会儿管理员就回来了。他穿着白大褂,有条不紊地在前面走着,后面跟着一小列乱糟糟的队伍。队伍的尾巴站着瘦瘦高高、外八字脚的约翰·吉文斯。他一手扣毛衣,一手拿着斜纹工人帽。
“嘿,”他跟父母打招呼,“看样子他们是打算让犯人出来放放风喽?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啊。我们走吧。”他小心地把帽子戴在头顶的正中央,这么一来,更活脱脱像个领政府救济金的人了。
在车里三个人都没有说话。直到车子驶过一排排砖结构的病房、行政大楼、垒球场,绕过门口修剪得整齐美观、中间插着国旗和州旗的圆形草坪,远远离开了医院,走在通往高速公路的柏油路上时,吉文斯太太才试探性地喊了一声:“约翰?”
她在后座上端详着约翰的脖子,揣摩着他的情绪。每次约翰坐在前排,她都选择坐在后座,这样她会觉得舒服一些。
“嗯?”
“我们给你带来了好消息。你还记得惠勒夫妇吧,你对他们还挺有好感的?他们又邀请我们过去坐坐,当然,这要看你愿不愿意。这是第一个好消息。不过真正的好消息是,他们决定不走了。他们不打算去欧洲了。你不觉得这样再好不过了吗?”说完她露出不安的微笑,看着约翰缓缓地转过头来,隔着车座后背面向她问:
“发生什么事情了?”
“呃,我并不知道详情——不过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亲爱的。我认为不一定非得‘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才会改变主意。有可能只是他们谈了一下,然后做出了新的决定,改变了原来的想法。”
“你是说你甚至没去打听?有人决定要做一件那么大的事情,然后忽然抛弃了这个计划,而你连问都不去问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
“这么说吧,约翰,我认为这不是我该打听的事。我们不该去过问别人的计划,除非他们主动提供信息。”她声调中的紧张感越来越掩盖不住,这很可能会激怒他,于是她努力用额头和嘴巴的皮肤挤出一个开朗的笑容。“我们能不能单纯为他们选择留下来而感到高兴,不去问‘为什么’呢?噢,你快看外面那个漂亮的老红筒仓啊,我以前从没注意过,你呢?这肯定是方圆几英里之内最高的筒仓了。”
“那的确是个很漂亮的老筒仓,妈妈。”约翰说,“而且,惠勒夫妇留下不走是个好消息,还有你是一个可爱的人。你说呢,爸爸?难道妈妈不是一个可爱的人吗?”
“好啦,约翰,”霍华德说,“冷静下来。”
吉文斯太太默不作声。她用手指把一盒小火柴搓揉撕扯成潮湿的小碎片。她闭上了眼睛,养精蓄锐准备应对这个她已经隐隐预见到的又一个不愉快的下午。
她的担忧在惠勒家的厨房门外雪上加霜。他们都在家里,因为两辆车子都在,但这栋房子很奇怪,看上去冷冰冰的,好像不欢迎任何客人到访。她轻轻地敲了敲门上的玻璃板,房子给她的唯一回应,就是让玻璃映照出天空、树和她向前探出的脸,以及身后的霍华德和约翰。她又敲了一次。这次她把一只手当作遮光板贴在玻璃板上,朝里张望。厨房没有人,桌子上放着一只装着冰茶之类的杯子。然后弗兰克从客厅冲了出来,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看起来就像马上要大嚷大叫,或者号啕大哭,或者要做出什么暴行来发泄情绪。她一看就知道,他并没有听见敲门声,也不知道她在那里。他不是出来应门的,而是绝望地想要逃离客厅,或者逃离这栋房子。她来不及退回去了,弗兰克已经看见她,看见她弯着身子,窥探着客厅,直接跟他四目相对。他吃了一惊,停了下来,然后尽最大的能力摆出友善的笑容来应付吉文斯太太的笑。
“哦,你们来啦,”他一边说一边开门,“你们好。赶快进屋吧。”
他们温文有序地走进客厅。在那里,他们看见爱波,而爱波的脸色同样可怕。她苍白憔悴,不安地在腰间搓捏着手指。“见到你们很高兴,”她虚弱地说,“请坐吧。不好意思我们家今天有点乱。”
“我们是不是来得太早啊?”吉文斯太太问。
“太早?不,没有。我们刚才在——大家还是先喝点东西吧。冰茶怎样?或者别的什么?”
“不,什么都不用了,谢谢。我们只坐一会儿,我们是顺道过来打个招呼的。”
聚会的气氛很别扭,吉文斯一家三口并排坐在一起,弗兰克和爱波则背靠着书架站着。他俩心神不定的,每次要交谈时,就凑近彼此,说完,又马上分开。到了现在,吉文斯太太已经猜出来他们为什么这么不自然:他们肯定是吵架了。
“听着,”约翰说。其他人停止了交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说了,你们已经改变主意。为什么?”
“呃,”弗兰克尴尬地笑了几声。“呃,应该说,我们被逼改变了想法。”
“到底怎么了?”
弗兰克侧身站到妻子身后。“这样,理由很清楚了吧。”吉文斯太太把目光投在爱波身上,第一次注意到,她穿的是——孕妇装!
“哦,爱波,”吉文斯太太兴奋得喊起来,“天哪,这真是太棒了!”她思量着在这种场合应该怎么做:她应该站起来,然后,亲亲她,还是怎样?不过爱波看来并不喜欢被人亲吻。“这太令人兴奋,”她接着说,“不知道该怎么让你们知道我有多开心,”然后,“我想你们马上就会需要一所更大的房子,对吧?”她一句接着一句地说,只是希望约翰可以待在一边缄口不语。但是约翰并没有遂她所愿。
“妈,你等等,”他说着站了起来。“等等,我不明白。”他紧紧盯着弗兰克的脸,就好像检察官在紧盯着嫌疑犯一样。“我不明白。这哪里清楚了?好吧,我现在知道她怀孕了,但是那又怎么样?难道在欧洲人们就不生孩子吗?”
“约翰,你先,先……”吉文斯太太说,“我想我们不应该……”
“妈,你能不掺和吗?我在问这个人一个问题。如果他不想回答,我认为他会自己告诉我的。”
“当然,”弗兰克低头看着鞋子微笑。“我想不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都应该知道如果无力养育孩子的话,那么最好就不要让他出生。既然已经怀上孩子,如果我们希望养活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留下来。这其实是钱的问题,你明白了吗?”
“好吧,”约翰点了点头,像是对这个回答感到满意,他的目光在弗兰克和爱波之间游移。“好吧,这是个好理由。”惠勒夫妇看起来像是松了一口气,但吉文斯太太却比刚才还紧张,因为常年的经验告诉她,接下来就要发生很可怕的事情。
“钱总是可以解释所有的问题,”约翰把双手插进口袋里,一边在房间里踱步一边说。“但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难道是你老婆劝你放弃了计划还是别的原因?”爱波正走向烟灰缸想要把烟灰掸去,发现约翰锐利的眼神投了过来,还向她露出一个炫目的笑脸。她抬起头来看了约翰一眼,很快又把头低了下去。
“啊,是不是啊?”他步步紧逼。“是不是小女人还没准备好不再过家家了?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看得出来。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她看上去很坚强,很有女性特质,能干得要命。好吧,这样看来原因就在你身上了。”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弗兰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约翰,求你了,”吉文斯太太说,“你这样说话太……”然而现在什么都阻止不了约翰。
“发生了什么事?你临阵退缩了还是怎么了?最后你确定自己更喜欢这里?更喜欢你所谓的无望的空虚?或者——哇,我知道我说对了,快看他的脸啊!你怎么啦,弗兰克,被我说中了吧?”
“约翰,你这样实在太粗鲁了。霍华德,你快……”
“好了,孩子,”霍华德站了起来。“我想我们最好还是……”
“天哪!”约翰放声狂笑。“天哪!你知道吗?如果你告诉我,你是故意把她肚子搞大,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这样你就可以一辈子躲在她的孕妇装后面。”
“你给我听着!”弗兰克喊道。吉文斯太太惊诧地发现,弗兰克紧握着双拳,从头到脚都在颤抖,“我忍够你了。你他妈以为你是什么人啊?你来到我的家,肆无忌惮地说着你那些疯话,我想是时候该告诉你,赶紧闭上——”
“他是个病人,弗兰克。”吉文斯太太结结巴巴地说,然后又惊惶失措地咬着唇。
“噢,病个屁!我很抱歉,吉文斯太太,不过我他妈才不管他是病人还是正常人,是死还是活,我只希望他赶紧闭上狗嘴,把他那些疯话全他妈留在那个狗屁疯人院里吧。那里才是真正属于他的地方。”
在接下来难堪的沉默中,五个人团团站在客厅中间:吉文斯太太还在咬着嘴唇,霍华德专注地把一件薄雨衣折叠到胳膊上;爱波红着脸盯着地面;弗兰克依然颤抖、大声喘着气,眼睛里布满了挫败和羞辱。约翰冷静地微笑着,反而是五个人里面唯一看上去心平气和的人。
“你可是给自己找了个了不起的男人啊,爱波,”他向爱波眨眨眼,然后把工人帽安放在头上。“一个对家庭尽责,对国家尽忠的好男儿。我为你感到难过。不过,可能你们都是一样的货色。看你现在的样子,我也开始为他感到难过了。细想一下,你肯定没给他什么好日子过,如果他只能在制造小孩的时候,才敢确认自己有一对睾丸。”
“好了,约翰,”霍华德咕哝,“我们赶快出去上车吧,就现在。”
“爱波,”吉文斯太太低声说,“我真的很抱歉,我——”
“是的。”约翰跟他父亲一起走向门口。“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说这么多对不起可以了吗,老妈?我说的次数够多了吧?该死,我的确感到很抱歉,因为我是全世界最可悲的混蛋了。当然,说到底,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值得我高兴的事情,对不对?”
吉文斯太太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唯一庆幸的是,约翰肯乖乖跟着霍华德走。她只需要尾随他们,走完这段路,走出这间房子,然后一切就会结束了。
不过约翰并没有打算偃旗息鼓。“嘿,倒是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到高兴,”他走到门边,停下脚步,转过身,再次大笑起来。当他伸出一根长长、黄黄的食指,指着爱波微微隆起的腹部时,吉文斯太太以为自己马上会昏死过去。约翰笑着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事情高兴吗?我高兴自己不是那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