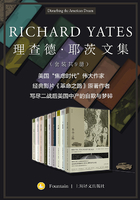
第21章 革命之路(19)
吉文斯一家离开之后,弗兰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倒了三指高的波旁威士忌,然后仰起头来一饮而尽。
“好啦,”他转过头来对妻子说,“好啦,你什么都不用说。”威士忌的火团在他胃里翻滚,把他呛得连连咳嗽。“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你觉得我刚刚的表现非常恶心,对吧?哦,还有,”他紧紧地尾随她穿过厨房然后走进客厅,盯着她圆溜溜的后脑勺,他的目光夹杂着羞耻、愤怒以及凄凉的哀求。“还有就是:那个人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这就是你打算跟我说的话,对吗?”
“显然我不需要自己再说一遍,你已经帮我说了出来。”
“但是爱波,如果你真的那么想,你就是大错特错了!”
她转过身来看着他。“我可不觉得。为什么这样想就错了?”
“因为那个人是疯子。”他把酒杯放在窗台上,这样就腾出两只手比划着来表达他说的话是多么真实,多么重要。他在胸前张开十指,然后紧握成拳头,他的手激动地颤抖了起来,“那个人是疯子,”他重复了一遍,“疯子。你难道不知道疯子是什么意思吗?”
“是的,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是的。那就是失去了跟旁人联系的能力,失去了爱的能力。”
她笑了出来。她笑得前仰后合,露出了两排完美的牙齿。她笑得眼睛眯合了起来,一波波的笑声回荡在房间里。“失……失去……失去了能力……”
她已经歇斯底里了。看着她狂笑不止,扶着一件件家具在房间里绕着圈,倚着墙壁然后又走了回来,弗兰克一时之间手足无措。在电影里,如果一个女人这样歇斯底里,男人就会给她几个耳光直到她停下来。但电影里的男人通常都很冷静,知道这几个耳光为什么要打下去,而弗兰克就没那么清醒了。他已经完全失去了主张,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她,愚蠢地张嘴,闭嘴。
她终于重重地跌坐进一张椅子里,不过笑声依然没有停歇。弗兰克猜想,笑声会渐渐转变成哭泣的——这是电影里经常发生的情节。他等啊等,然而她没有。笑声渐息,她不同寻常地平静了下来,就像刚听完了一个特别过瘾的笑话,而不是从歇斯底里中恢复过来。
“噢,”她说,“弗兰克,你可真是巧舌如簧。如果说几句话就能颠倒黑白,那么你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最佳人选。你想说的是,我是个疯子,因为我居然不爱你了,对吗?”
“不,你错了。你并没有发疯,你依然爱着我,这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她站了起来,退开了几步,眼睛闪着光。“可是我不再爱你了,事实上我连看都不愿意看到你。如果你再靠近我一点,如果你走过来触碰我,或是做别的什么,我想我会大声喊叫的。”
然后他真的过去摸了她。“宝贝儿,听我——”一句话没说完,她果然高声尖叫。
她的尖叫显然是假的,因为她一边叫一边冷冷地看着他的双眼。但这叫声尖锐刺耳,而且响亮得足以震动整个房子。弗兰克强忍着,直到声音结束才说:“你真该死。你这个肮脏下贱的……你给我过来,你这个该死的女人。”
她轻巧地从他身边躲开,然后拖来一把椅子挡在她和他之间。他把椅子揪起来,扔到墙上,一条椅腿咔嚓断为两截。
“你现在想干什么?”她继续激怒他。“是打算过来打我吗?来表达你有多么爱我?”
“不,”这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自己强大起来。“不,我不会的,你不用担心。我才懒得那么做。你根本不值得我费力气去打你。你不值得我用任何手段去对付你。你不过就是一个空虚……”他这才意识到,他的声音那么肆无忌惮,那么畅快自由,是因为孩子们不在家。没有人在,也没有人要来;这个充满回声的房子只属于他们俩。“你就是他妈一个空虚浅薄,一个徒有其表的女人……”这么多个月以来,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这样公开地、毫无顾忌地争吵。而他正充分地利用这次机会,绕着她兜圈子,冲她喊叫、颤抖、喘息。“如果你那么恨我的话,你他妈住在我的房子里干什么?啊?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你他妈为什么要给我生孩子?啊?”他像约翰一样指着她的肚子说,“为什么你不把这个孩子打掉?你有机会这么做的。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当他平缓地把下一个句子说出来的时候,他心里的重压也开始释放出来;他的语调出奇地缓慢而清晰,仿佛他从来没有试过这么明明白白地把真相揭露出来:“我祈求上天你已经把孩子打掉了。”
这无疑是最好的一句结束语。他快步从她身前走开,经过天旋地转的廊道,走进卧室,狠狠一脚把门关上,重重坐倒在床上,然后把右拳打入左手掌心。天哪!
多么狠的一句话!不过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他难道不曾希望她把孩子打掉吗?“是的,”他大声地自言自语。“是的,我曾经那么想,我曾经那么想。”他张嘴急促地喘着气,心脏像鼓一样跳动;过了一会儿他吞一口唾沫,闭上干枯的嘴唇,所以房间里只能听见空气进出鼻孔的声音。逐渐地,他的心跳放缓了,他的眼睛开始辨识周围的东西:沾染着落日余晖的窗玻璃和窗帘;爱波梳妆台上那些散发着香气的瓶瓶罐罐;挂在敞开的衣柜里的白色睡衣,整整齐齐地排放在柜子底下的三寸高跟鞋、芭蕾舞鞋,还有脏兮兮的蓝色软拖鞋。
一切都静悄悄的。他开始后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则因为他还想喝点酒。然后他听见厨房门关上了,纱门也砰的一声关上了,一种熟悉的恐惧感油然而生:“她又要离开我了。”
他连忙站起身,悄然无声地跑回厨房,希望能逮住她说些什么——什么都行——在她发动引擎绝尘而去之前。但她不在车里,也不在车子附近。她哪儿都不在。她消失了。他绕着房子跑了一圈,东张西望地寻找她的身影,松弛的脸颊随着脚步上下跳动。他再次漫无目的地绕着房子跑起来,这时他看见她的身子掩映在树林中。爱波步履蹒跚地往上爬,在树木和岩石之间越发显得细小柔弱。他全力冲过草地,纵身一跃跳过一堵低矮石墙,探身进入树丛中跌跌撞撞奔向她。弗兰克心想,这一次她是不是真的发疯了?她爬到这上面来到底是要干什么?当他终于追上她,抓住她的胳膊,并让她转过身来时,他会不会看到一抹空洞的、精神错乱的微笑?
“不要再靠近了。”她命令道。
“爱波,听我说,我……”
“不要再靠近了。难道我跑到树林里来都不能躲开你吗?”
他只好停了来,站在距离她十码远的下方气喘吁吁地看着她。现在至少他知道,爱波神志正常,脸孔澄静。然而这不是一个适合吵架的地方。这里暴露在邻居们的耳目之中。
“爱波,听着,我刚才说的话是假的。我很诚实地跟你说,我并不希望你把孩子打掉。”
“你还在说话吗?有没有办法可以不让你说话啊?”她倚靠在一棵树干上,俯视着他的脸。
“请你下来吧。你到那上面去想干什么啊?”
“你想让我再大声喊叫吗,弗兰克?如果你再说一个字,我就会叫起来。我说真的。”
如果她在山边大喊大叫,革命路上的每一户人家都会听见,整个革命山庄的人都会听见,包括坎贝尔夫妇。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得一个人先回到家里:穿过树林来到草坪,进家门。
一回到厨房他就马上来到窗户边,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爱波的一举一动。他站着——或者说匍匐在窗前,后来腿累了,他才拖来一张椅子坐下。他确保自己的位置远远地隐藏在阴影底下,这样她才不会察觉。
她在山上好像什么事也没做,只是继续靠在树上。不久以后,夜幕临近,弗兰克已经辨别不清她的身影。这时,一点黄色火光忽然跳了出来,原来她点燃了一根香烟。弗兰克盯着红色的小烟头缓缓下降,等到这点亮光出了树林,周围已经一片漆黑。
弗兰克继续注视着那里,没注意到爱波苍白的形体忽地出现在靠近得多的地方,吓了他一跳。她正穿过草坪走向房子。他赶紧离开厨房,前脚刚踏出去,她后脚就跟进来了。弗兰克躲在客厅里,听见她拿起电话并且拨通了一个号码。
她的声音很平静,跟平时没什么两样。“你好,是米莉吗?你好,对对,他们刚刚才走。不过你听我说,我想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我今天感觉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感冒了,而弗兰克今天也挺累的。能不能麻烦你今晚帮我照看一下孩子,让他们留在你那边过夜?……哦,那真是太谢谢你了,米莉……不,不用麻烦了,他们昨晚刚刚洗过澡……嗯,我知道他们会很乐意留下的。每次在你们家玩的时候都过得非常愉快。……那太好了,就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再给你打电话。”
然后她走进客厅,打开了灯,突如其来的强光让两人眯起眼睛,并频繁地眨眼。在各种复杂的情绪中,弗兰克现在感觉最强烈的就是无比的难堪。她看起来同样感到难堪。最后她穿过房间躺到了沙发上,把脸埋藏起来。
过去遇到这种情况,弗兰克会走出家门,发动引擎,驶到几英里远的酒吧,一家一家喝过去,在这些灯红酒绿的酒吧里,弗兰克会把钱撒在湿乎乎的吧台上,闷闷不乐地听女招待和建筑工人们冗长而夹缠不清的交谈,到自动点唱机翻找出几首喧闹的歌曲,然后再开着车消磨整个晚上,直到自己能睡着为止。
但今晚他无法这样做。因为他们从来没遭遇过像今天那么糟糕的情况。他身体已经疲软得无法离开大门,更别说开车到处跑了。他的膝盖像灌了糨糊,脑袋嗡嗡直响,他有点感激周围还有这栋房子来庇护他。现在他唯一有能力做的事情,就是再次走进卧室,把自己关起来。不过这一次,尽管情绪沮丧透顶,他没有忘记在走进房间之前带上一整瓶威士忌。
这一晚他蜷缩在床上,做了很多情景非常真实的噩梦,醒来时裹着衣服的全身冒着冷汗。他记得有的时候,他可能醒着,或者梦见自己醒着,他听到爱波在屋子里走动的声音;还有一次,天快亮的时候,他发誓自己睁开眼睛看见她坐在床沿,紧挨着他。这难道又是一场梦?
“宝贝儿,是你吗?”他微弱的声音从肿胀干裂的嘴唇发出来,“噢,我的宝贝儿,请你不要离开。”他伸出手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噢,请你留下来。”
“嘘,嘘,没事啦,”她说,一边捏着他的手指。“没事啦,弗兰克,快睡吧。”她的声音如此温厚,她的双手如此清凉,让他心底一片安宁。他再也不在乎这到底是不是梦境,这一刻的安详已足以让他沉入无梦的深深睡眠中。
然后黄色亮光刺痛了他——弗兰克独自一人在床上,真正地醒过来了。他还没判断出自己的状态实在不适合上班,就想起今天是个不得不上班的日子。因为今天将召开那个评估会议。于是他颤颤悠悠地起床,走进浴室,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淋浴剃胡子。
就在他穿衣服的时候,一个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希望让他心跳加速。或许那不是一个梦呢?或许她真的来过,并且坐在床上跟他那样说过话?当他走进厨房时,他的一厢情愿变成了事实。他看到的情景把他惊呆了。
餐桌上整洁地摆好了两套餐具,厨房里充满了阳光,还有咖啡及煎培根的香气。爱波穿着干爽利落的孕妇装,站在灶台前,听到弗兰克进来,她抬起头羞涩一笑。
“早安。”她说。
弗兰克恨不得跪倒在她身边,抱住她的腿,但他到底克制住了。有些东西告诉他——或许就是她笑容里奇异的羞涩——他最好别轻举妄动。他应该参与这个演出,奇怪却又隆重地装作昨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早安,”他说,避开了她的目光。
他坐了下来,铺开餐巾,心想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没有一个吵完架后的早晨能这么轻松的。不过,当他战战兢兢地喝着橙汁的时候,他也想起了,没有一次吵架像昨天那么激烈、那么严重。这是因为,他们昨天已经把所有可吵的东西都吵完了吗?所以现在无论是侮辱还是宽恕,他们已经没有更多话可说了?而生活,毕竟还要继续的。
“今天早晨的天气真好,不是吗?”他说。
“是的。你是想吃炒鸡蛋,还是煎鸡蛋?”
“哦,都可以——呃,如果不会太麻烦的话,就炒鸡蛋吧。”
“好的,那我也一起吃炒鸡蛋。”
不久之后他们就亲密地对坐在明亮的桌子两头,相互递送着黄油和面包,轻声说着礼貌用语。一开始他害羞得吃不进去,就像十七岁那年第一次带女孩出去吃晚餐,当时他觉得在女孩面前把食物叉起来放进嘴里,然后开始咀嚼是一件非常粗鲁的事情。还好跟当时一样,一件事情出来拯救了他: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来这么饥饿。
在咀嚼的间隙他说:“这样感觉还挺好的,坐在这里吃早餐,没有孩子们在旁边吵闹。”
“嗯。”她没有吃那盘鸡蛋,而且他看到她伸手去拿咖啡杯的时候,手指在微微颤抖。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弗兰克还以为她真的非常镇静。“我想你今天可能会想好好吃点早餐,”她说,“今天是个挺重要的日子,对吧?你要去跟波洛克开会。”
“没错,”她竟然记得这件事!不过他还是用多年来每次跟她谈到诺克斯公司时故作轻蔑的撇嘴一笑,来掩盖内心的喜悦,“大概是件大事吧。”
“嗯,我猜想是件相当重要的事,至少对于他们来说。你认为自己会做些什么工作?我是说,在他们派你出差之前。你很少提起这方面的事情。”
她居然对他的工作表现出兴趣?她在开玩笑吗?“我没跟你提起过?”弗兰克说,“可能吧。连我自己也不了解情况。我猜想,就像波洛克说的,‘拟定工作目标’我们大概就是围坐在他身边,听他长篇大论,然后大家都装出很懂电脑的样子。我想这个计划之所以会启动,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诺克斯要大量买进一种很大型的电脑,比‘诺克斯500’还大。我告诉过你这些吗?”
“应该没有吧。”不可思议的是,她看起来真的愿意聆听。
“是这样的,你知道通用自动计算机那一类庞然大物吗?就是人们用来预报天气或者是估计选举走势之类的机器。这大家伙一件就要二百万美元。如果诺克斯生产这个东西,就要围绕它组织一个全新的推广计划。我想这就是波洛克在策划的事情吧。”
他奇怪地感到肺活量变大了,或者空气里的氧气更充沛。他抬得又高又紧绷的肩膀,现在渐渐靠在椅背上放松了下来。其他男人跟妻子谈论他们的工作时,也会有这种奇特的感受吗?
“……基本上,它只不过是一台大极了、快极了的计算器,”他尽可能满足她对一台电脑如何运作的好奇心。“它不像其他机械一样有很多金属部件,而是采用了很多很多个真空管……”说到这里他干脆在餐巾纸上画了个图表,向她解释数字脉冲是如何在电路当中流动。
“哦,我明白了,”她说,“至少我觉得我明白了。嗯。这东西确实还有点……有点意思,你说呢?”
“呃,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嗯,从某种角度看,确实有点意思吧。不过我了解的东西很有限,我能够认识到的不过是最基本的概念。”
“你总是这么说。我敢打赌,你懂的事情要比你意识到的多得多。无论如何,你解释得非常好。”
“哦,是吗?”他垂下眼睛,把铅笔放回他挺括的华达呢外套,微笑的脸上觉得热辣辣的。“谢谢。”他把第二杯咖啡一口喝完,然后站起来说,“我想我得赶紧出发了。”
她也跟着站了起来,顺手抚平裙子上的褶印。
“听着爱波,这一切真是太好了。”他的喉头哽住了,觉得马上就要哭出来。但他设法控制住了自己。“我是说这是一顿很棒的早餐,”他眨了眨眼睛。“真的。我不记得以前吃过比这个还棒的早餐了。”
“谢谢你的夸赞,”她说,“我也很高兴,我也吃得很愉快。”
他能这样就走出去吗?什么话都不说?当他们一起走向门口,他看着她想道,是不是该说“对于昨天的事情,我觉得很抱歉”,还是“我真的很爱你”一类的话?还是什么都不说,以免再度挑起不愉快的情绪?他犹豫着把脸转过来面对着她,觉得嘴巴扭曲成一个奇怪的形状。
“那么你真的不——”他终于还是说了。“你真的不恨我吗?”
她的眼神看上去深沉而严肃,好像很高兴他问了她这个问题,仿佛这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她有资格回答的问题之一。她轻轻地摇了摇头:“不,我当然不恨你,”她为他打开了门,说,“祝你能度过愉快的一天。”
“我会的,希望你也是。”接下来该干什么就不怎么费思量了——像电影里的男主角一样,他慢慢弯身去亲吻她的唇,并尽量不触碰她的身体。
她的脸越来越近时,弗兰克看到了一瞬间的惊讶和犹豫。不过她的脸很快就柔和下来,半闭着眼,她很清晰地传达一个信息,不管多么短暂,这是一个两情相悦的、柔情的吻。直到这一吻之后,弗兰克才握着她的手臂——无论发生什么事,她终究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
“那好吧,”他的声音沙哑地说。“我先走了,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