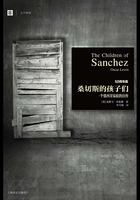
第8章 曼努埃尔(3)
跟有钱人相比,我们这里的生活很落后,也更真实。在我们这里,十岁的男孩子如果看见女人的性器官,绝不会大惊小怪。如果看见某个人正在扒别人的钱包,或者拿刀子抵着别人,也丝毫不会感到惊讶。近距离地见过那么多罪恶,人只能面对现实。再过一阵,恐怕就连死亡也吓不倒我们了。我们小小年纪就已经跟生活碰得鼻青脸肿,对不对?痂都结上了,就像一颗痣,不会消失,只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又挨上一拳,又结一层痂,直到形成盔甲一样的东西,最后就无所谓了。
有钱人可以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只看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免遭损友和秽语的侵蚀,躲过暴力造成的情感伤害,一切开销全都可以买单。他们闭上了眼睛,说起话来也幼稚不堪。
整个童年,直至之后一段时间,我都经常跟那一帮人在一起。我们没有什么头儿……他得什么都在行……可一个人只能在某个方面略胜一筹。我们不像有些帮派那样有坏孩子。我们社区就有一帮人,大家都知道他们从酒鬼身上偷钱,还吸大麻。我们这个帮派只有一个人扎过针,变成了坏人。我们那时候干的坏事也就仅限于偷偷从后面掀女孩子的裙子……仅此而已……
那个时候,我顶顶崇拜我的大表哥萨尔瓦多,他是我姨妈瓜达卢佩的独子。他令贝克大街那伙真正厉害的小子也闻风丧胆,在整个帮派的成员中,大家最怕的就是他。我崇拜他,只因为他是打架的好手。其他方面嘛,我觉得他不怎么样,因为他跟我姨妈说话的腔调十分恶心,喝醉后尤其如此。他老爱喝酒,又爱上一个女人,所以很快就潦倒不堪。他跟这个女人生了个孩子,而这个女人却跟另一个男人跑了,这个男人后来用冰刨杀死了我的表哥。
我十三岁的时候,帮派中的几个大孩子想带我去墨槽大街逛窑子。“算了,兄弟,别带我去墨槽大街。我父亲会宰了我的。不去!”可他们说:“怎么啦?同性恋还是咋的?你也该去去了。我们出钱,让她陪你好好玩玩儿。”我不想去,因为我怕得病。
过去我害怕染上性病,现在还怕。我很小就有这种害怕的心理。有一次在浴室,我看见一个人的阴茎烂掉了半截,还流着脓水,那场面让我怕极了。后来,有人带我去博物馆,我又看了些孩子患梅毒的图片……卡萨—格兰德有个孩子患上淋病,复发过四五次。他拉尿的时候痛得嗷嗷直叫,医生给他治疗的时候,我也听见他号声震天。
父亲也吓唬过我一次。我十二岁的时候,脚踝关节有些疼痛,疼得我只能踮着脚尖走路。结果让他看见了,他以为是别的什么事情,于是有一天把我堵在卧室里。“把裤子脱下来,我看看。小混蛋,你去墨槽大街搞过几个女人?我可不想自己的孙子变成独眼龙或跛脚的傻子!把裤子脱了让我看看!”
“不,爸爸,我没事儿!”要脱了让爸爸看,真是难为情得很……我那儿已经开始长毛了……唉,我羞得把脸别了过去。可他光看看还不满意。他带我去看医生,那个庸医给我开了些药,尽管我什么事儿也没有。
所以,我不想跟那帮小子去墨槽大街。可他们告诉我,如果事后在那玩意儿上挤点柠檬汁,就不会染病了,于是我们还是去了。我、阿尔维托,还有另一个家伙找了一个小姐。我很紧张,根本是有心无力,双腿不住地发抖。另一个人趴到她身上直接干了起来,完了之后,他说道:“该你了。”
“好吧,”我说。“可如果我得了病,你他妈的要拿钱给我治病吗?”
“你那熊样还是个男人吗?”遭到如此奚落,我只好硬着头皮挺了上去。我趴到那位小姐的身上,她的动作非常夸张,我却没感觉到一点乐趣。我当时就想,这骚婆娘经验十足,一定跟谁都可以睡觉。我一点都喜欢不起来。可同去的那帮小子对我的表现十分满意,于是事情就了结了。
从那之后,对性的热衷攫住了我,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它。晚上,我的梦里全是女人和性,看到女人就想扑上去。找不到女人的时候,我只能自己满足自己。
现在回想起来,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恩诺开始来我家做工。她跟我们同住一个院子,每天来我家煮饭打扫卫生。她儿子也是我的朋友。我之所以打她的主意,是因为我知道雷蒙多,也就是艾莱娜的弟弟搞上了她。我当时想:“大马车啊,为什么只有雷蒙多骑得?别人也想骑啊,对吧?”可她说:“嘿,小坏蛋……你去问问你爸爸答不答应吧。”父亲好像也为她伤透了脑筋!
我跟我家的用人总是没戏,因为我爸爸老是捷足先登。拉查塔也不例外。她很胖,我并不喜欢。她想让我放了学再吃饭,这令我感到非常不爽。要是我回答说不,她就会说:“不想吃,是吧?好,那我多吃点。”说着说着,她那两瓣肥屁股就坐了下来,把我那份饭菜一扫而光。
不过,她毕竟是个女人,我有一次跟她说起了……嗯……这个事儿。“算了,”她说道。“你那么小,会做吗?”可我不放手。“唉,”我对她说。“可能你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我会啊。来吧,让我试试!”
“行啊,怎么不行?”她终于同意了。“去我家吧。”于是,我跟着去了她家,可她又改变了主意。“不行!你还是个孩子,这些事儿你在哪儿学的?回家去吧。”说着说着,她就扯到了我爸爸身上。
在那之前,我已经在居民区泡过几个女孩儿了,学校也有……胡莉塔,我的表妹,住在院子中部的那三姐妹,玛利亚……大概有八个吧。可那都只是玩……爸爸妈妈的游戏,因为我还小,根本没法跟她们做点什么。
后来,我在舞会上遇到了帕琪塔,她跟她们完全不一样。她是个舞蹈皇后,我们都很喜欢对方。跳舞的时候,她紧紧地贴着我,跳得满脸通红。一天晚上,我带着她去了旅馆。
嘿,一进入房间,我就对着她的脖子和双臂吻了起来,她也爱抚着我。我脱了她的鞋子,还有袜子……当时最令我激动的是……她轻轻地挣扎着,有点害羞,那更刺激了我。她就是那种类型的人。我想把手放在什么地方,可她偏不让。嗯,我一点一点地得寸进尺,终于体会到了一种全新的激情,因为她算得上是我们称之为骚的那种女人。你只觉得被她吸着,吮着……哦,只要我跟她出去,总要来个十次八次。实际上,她算是个老手,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体位啊,忍住啊之类的。我因此也才知道,女人也喜欢干这事儿。可她并不是为我而生,因为不止我一个人上过她。被别人上过的女人我都不太喜欢。
有一个小伙子名叫老鼠……后来被人杀死了……嗯,他曾经想教我拉皮条。他对我说:“哥们,急不得,先找个马子跟她跳舞,然后让她爱上你。接下来,你就把她给睡了,再把她卖到夜总会去。”他是个跳舞高手,所以迷住了很多女孩。我一个劲地说不,因为我根本不喜欢他那样的主意。后来,他把我和阿尔维托介绍给他的一个女孩儿认识,想安排我们一个一个地陪她跳舞,招待她喝啤酒,等她喝醉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她作践一番。
于是我们上阵了,先是灌她啤酒,她喝三杯,我们才喝一杯,直到我们几个都受不了为止。我们给她下了两颗安眠药,可她竟把我们三个灌醉了!她抛下我们三个,独自出门扬长而去。老鼠简直不敢相信,他说:“我他妈真是操蛋!竟然让那娘们给耍了?”那个女孩算是让我们跌了跟头。
我和阿尔维托沮丧极了,我俩真是一对活宝。他搞过一个女孩,还是个处女,所以,现在在某个地方,他还有个儿子呢。可他不拿这当一回事儿,想把她给甩了。“哥们儿,”他跟我说。“没办法,只有你把她接收了。你可以跟她上床,跟她睡觉,这样我才可以说‘你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背叛了我’。”出于对朋友的义气,我无视其中的龌龊,帮了他。
当时,阿尔维托负责替他叔叔照看一个露天的二手服装摊。那一带的摊子沿街道两旁一溜烟摆过去,位于一个大市场的外面。他那个摊子专营“白衣服”,也就是内衣,我不上课的时候就帮阿尔维托卖货。他在账目上做手脚,营业额根本不上报,于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去看电影。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每天都出去看电影。
我们有时候会把同一部电影看上三四遍,于是,我们买来几张面皮,用这张裹上豆子,用那张装上米饭,再用另一张裹上冰淇淋或者鳄梨,总之是带了一大堆零食。每个人都会喝上两三瓶苏打水,吃几个橘子,再来点瓜子、糖果、坚果……嗨,反正每次都要留下一大堆垃圾。全部都由阿尔维托付钱。他每天的开销大概有二十五比索,不过都是他叔叔的钱。
眼见生意不断下滑,阿尔维托的叔叔卖了服装摊,我们来钱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接手服装摊的是个女孩儿,名叫莫德斯塔,我们经常跟她聊天。她有点喜欢我们,经常请我们打台球吃玉米饼。她并不迷人……脸上全是粉刺,一只眼睛有白内障……不过她的身材很惹火,屁股很小,胸脯很丰满。每当我和阿尔维托没钱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就会过去看她。
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提前设计了一下。服装摊有一个柜台,后面是墙壁,她就坐在两者之间。我跳进柜台,对她说道:“嗨,莫德斯塔,生意还好吧?亲爱的,你一天比一天水灵啊。”
“哈哈,死鬼,又来了。”她回答道。
“不,是真的,你什么都好。明摆着呢。”你看,我这么说就是要点她的火,是吧?
她终于说道:“听着,曼努埃尔,谁知道你做起来究竟怎么样呢?”她还是个处女呢,对吧?
“唉,以为我傻呀。我才不会告诉你,你要想知道,就得跟我做呀。”她坐在一张凳子上,双腿叉开。“看吧,我会让你知道的,或多或少……”我把手放到了她的大腿上……“然后你就知道了,明白没?”
阿尔维托示意我把她放到地板上。当时正值中午,周围有很多人。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我已经把她放到柜台下了,阿尔维托扯了一张床单盖住我们。我解了她的上衣,抓住她的乳房,又吻又咬。
周围人来人往,床单上下起伏。阿尔维托后来对我讲,路人都看见了上下起伏的床单,他于是不住地掐我,要我停下来,但我根本没察觉,也没听见什么。就在我跟她享乐的过程中,阿尔维托从她的摊子里打开了几个童装抽屉,我们后来就又有钱看电影了。
之后,我又去看过莫德斯塔几次。有一次,我脱了她的裤子,突然看见流血了,于是一下就停住。我害怕了,因为我以为她得了坏病,或者是哪个地方溃烂了。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女人有月经。
我觉得月经很脏,也许是因为我搞过的很多女人没有讲卫生的习惯吧。多原始啊!要是说有什么东西让我受不了的话,那就是女人的气味。不止一次,我在床上东吻西摸,一切都做得好好的,等到分开大腿的时候……哎呀,那味道实在难闻,我的兴趣一下就没了,只好叫她去洗一洗。我对不干净的女人一直很过敏。
家中艾莱娜的病情每况愈下,她脸色苍白,行为古怪,爸爸带她去看了医生,结果患了肺结核。只要我们惹她生气,爸爸揍我们就更凶了。有一次,他怪罗伯托推了她一把,让她加重了病情。她倒地的时候磕在水槽边上,位置倒是在肺部上面一点,但我觉得那不是她生病的根源。事情的起因是她和罗伯托吵了一架,她感觉头晕,然后就倒了。后来,父亲说是因为我们的过失,才导致了艾莱娜死亡。
我父亲的嫉妒心总是非常强。有一次,我觉得艾莱娜想抛下我父亲,去跟一个个头非常矮小的屠户过日子。我父亲察觉之后,有一天比平时提前下班回到了家。他抓起一把刀子,直奔肉摊而去。我和罗伯托拿着石头和棍子跟在后边,以防他需要帮忙什么的。我们看着他走进肉铺,跟那个屠户说了起来,可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回到家,把艾莱娜痛骂了一顿,但并不像当初骂我母亲那么大声,那么龌龊。
还有一次,因为他的一个侄子,他差点就对艾莱娜失去了信任。我父亲跟家族失去了联系,很偶然地找到了这位侄子。我父亲碰巧在《漫画》杂志上看到一则启事说:“戴维·桑切斯先生寻找于1922年离开瓦清朗格种植园的赫苏斯·桑切斯先生。”我父亲给他去了信,戴维于是从韦拉克鲁斯搬来跟我们住在了一起。他是我父亲的哥哥的儿子。我连叔伯们的名字都说不上来!戴维和他母亲是唯一健在的两个人,他们以为我父亲肯定也一早过世了。每逢亡灵节,他们都要为我父亲的灵位敬献蜡烛和食物。
于是,我父亲在拉—格罗里亚餐馆替戴维找了份活儿,我们一家人相处得还很不错。可有一天,我爸爸回家的时候,碰到艾莱娜正坐在戴维的大腿上。我对戴维的印象一向是没有丝毫恶意的一个人。在我所有的亲戚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他依旧保留着乡村的淳朴,丝毫没有城里人那种腐朽劲儿。他的心灵很纯洁。所以我说,他对艾莱娜别无所求。应该是她在追求他,可结果呢,他只好回到了韦拉克鲁斯。
万望老天原谅我,我甚至觉得父亲怀疑过我和艾莱娜。我确信无疑,因为当一个人发怒的时候,他看人的眼神会很特别,而父亲当时就是以那样的眼神看我的。我当时想不明白,现在总算看出来了,他怀疑我和艾莱娜的关系。
为了避免罗伯托和艾莱娜无休止的争吵,父亲在卡萨—格兰德又租了一间房子。我们几个孩子住六十四号,艾莱娜和她的母亲桑迪托斯则住在一百零三号。艾莱娜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索利达德也在六十四号住过一段时间。我们几个人跟他们都相处得很好。桑迪托斯为人很好,也非常讲道理。她一直对我们很好,时至今日都还如此。奇怪的是,跟父亲不同,她从来没有因为艾莱娜的死而责怪过我们。
我现在根本不生艾莱娜的气,对她,我甚至开始感到有些感情和怜悯了。我陪她去过肺结核医务室,看他们给她治疗气胸,把一种注满空气的管子推进她的肋骨里去。我那可怜的父亲非常担心,尽其所能给她找了最好的医生。他送她住进了综合医院,并经常让我给她送水果和饭菜。
我觉得,是在艾莱娜住院期间,父亲开始往家里拿鸟笼的。我当时想:“好奇怪啊,父亲竟然买了几只鸟。”我记得他跟母亲吵过几次架,因为母亲想让他买几只鸟儿放在家里。第二天,他又买回来几只鸟。他一直买一直买,直到我家的墙上到处挂的都是鸟笼子。当那些鸟儿突然一起鸣唱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啊,好听极了,让我觉得好像身处乡间或者森林。
父亲要我和罗伯托早晨六点钟起床给鸟儿们喂食,为此我恨透了那些鸟。我一向懒得早起,每当听到父亲朝我喊叫:“曼努埃尔,罗伯托,起床了!”我简直难受死了。
头几天听到父亲这样叫我的时候,我会答应:“唉,爸爸,我腿不舒服。让罗伯托去喂它们吧。”可罗伯托很快就看穿了,我只好跟着起了床。我们得用大砍刀把好几公斤重的香蕉剁碎,再拌上面粉和其他青饲料。接着,我们要把饲料放进一个个鸟笼里,给它们换水,还要清扫它们的排泄物。
一天,我父亲吩咐道:“曼努埃尔,你把鸟儿拿去市场上卖了。”想到我可以帮帮父亲,想到他觉得我还有用,我就高兴不已。可从内心来说,我对干这样的活儿还有些害羞。我拿着鸟笼子——一个一个地摞在一起,穿行在市场里,想方设法把那些鸟儿卖出去。
有一天是星期三,父亲跟着来了,他想看我卖得怎样了。我们在那儿站着的时候,森林部门的一个人出现了,要我父亲出示动物销售许可证。我爸爸根本没有什么许可证,而且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因此非常紧张。我猜想他当时给警察的贿赂比罚款还多。
那之后,他只向邻居和工友出售鸟儿。自从跟居住在陶罐大街的一个禽鸟大经销商成为朋友之后,他结交了很多客户。我父亲先是卖鸟儿,后来又卖鸽子、火鸡、小鸡和小猪,因为在当了这么多年的工人之后,他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商业天赋。他醒悟得有点晚,可他总归明白,做那样的营生来钱更多。
我十四岁大的时候,隐隐地知道我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安东尼娅和玛丽莲娜。那之前,我根本不知道父亲还有一个老婆,而且还有好几个孩子。不过我记得,在我十岁大的那一年,父亲有一次带我去拉—格罗里亚餐馆替他打下手。在回家的路上,当我们走到罗萨里奥大街的时候,爸爸对我说:“你在这个街角等我一下。”然后他就走进了一家租户。我心想:“爸爸进去干什么?他要去看望谁呢?”我当时有点嫉妒。我甚至在想,妈妈觉得爸爸还有一个女人的想法到底对不对。
现在我终于弄清楚,他当时去看望的是卢裴塔,也就是我那几个同父异母妹妹们的妈妈。小的时候,我对她知之甚少,即便到了后来,我也很少跟她说话。
有一次,我半夜回到家里,发现妹妹的床上躺着另外一个人。罗伯托依旧睡在地板上他自己的老位置,父亲睡在床上。我蹑手蹑脚走到妹妹的床边,俯身查看那个人到底是谁。我父亲一定在黑暗中注意着我的动静,突然说了一句:“是你妹妹。”
“我妹妹?”
“是的,你妹妹安东尼娅。”
唉,就这样,我一声不吭地上床睡了。之前,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起过她。我禁不住想:“这个妹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急切地盼望着天亮,好让我看看这位新妹妹。
作为一个女孩子,尽管她聊起天来十分可爱,十分快活,但并不引人注目。相反,她对我们几个兄妹时常有一种不太友善的心理,或者说是有点怨恨吧。从一开始,她就讨厌我父亲,不断地找他的麻烦。她会讲脏话,也会跟他顶嘴,我真想抽她一嘴巴。咋说呢,有一次我父亲跟她说,有些事情她不应该做,而她竟说:“只要我高兴,我就可以做,关你屁事……是谁不公平?到底是谁啊?”她就那样对我的父亲大吼大叫。
那之后,我完全不喜欢安东尼娅了,尽量地跟她保持一段距离,原因之一是我怕自己会把她当成女人,而不是当成妹妹来对待。尽管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却几乎不大说话。
可我弟弟罗伯托很喜欢她。不知道父亲怎么听到了这件事儿,反正他是察觉了。搞不清罗伯托是把她当女人来喜欢,还是当妹妹来喜欢,总之他对她喜欢得不得了。
就在这时,住院治疗的艾莱娜没有什么好转,接着就回家了。当她的情形变得非常严重的时候,父亲让我们去叫瓜达卢佩姨妈找来了牧师。牧师问我们,父亲之前是否结过婚,我们都说没有。接着,他就主持仪式,让我父亲和艾莱娜结了婚,这样她的灵魂才能够升天安息。我相信,我爸爸现在还戴着结婚戒指。
一天下午,我回到家的时候,玛塔说道:“快进去看看艾莱娜。”我进去才发现,她已经死了。几天前,我父亲还充满了信心,因为她的体重一直在增加。他以为这样的信号足以说明她的情况有所好转,可谁想到她还是死了。那一幕我记得很清楚。棺材就摆在屋子的中间,几个角上都点了蜡烛。屋里有几个人,我父亲站在门廊里。他看到我之后,说道:“看看你们这些龟孙子做的好事!害死她的就是你们这几个小杂种!”
我明白,他那是出于悲伤,出于绝望,可我父亲长期以来都是那样。我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反正只要有事情,他就会说:“这对你们没好处,你们走到哪儿,人家都不会给你们好脸色。”他总是希望我交不到好运。那天,父亲让我感到无地自容,我躲在门后面,在心里对自己说:“原谅我,艾莱娜,如果我曾经伤害过你的话,请一定原谅我,一定原谅我曾经对你做过的错事儿。”我只能这么说。
罗伯托在那里为她的逝去而痛哭,康素爱萝也在那儿,而我的父亲由于受了悲伤的打击,为她的过世不断地怪罪我们。她停放了两天——跟我母亲不一样,然后,我们把她埋在了同一个墓地里。我父亲买了一小块“永久性”用地,并用砖头围了起来。他还用钱请了一个人看管墓地。
唉,把她埋葬之后,父亲对我们的态度更加刻薄更加生硬了。他对我们的怨恨与日俱增,老是责怪我们,说是因为我们他跟她才过得很不幸福。家里的时间越来越不好过,我在外打发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就在我们常去打发时间的那家服装摊子对面,有一家餐馆名叫林氏咖啡屋,是一个中国人开的。有一个漂亮女孩儿在那儿做服务员,名叫格瑞塞拉。她那一头卷发很黑,但皮肤很白。我一看到她就喜欢不已。“嗨,你看她那眼睛!哥们儿,”我对阿尔维托说。“多完美呀!天生尤物!你看她长得多美呀。如果我把她钓到手,你愿意赌多少?”我就那样说说,并没太当真。
“真的吗?你说要钓她,是真的么?她看都不看你。别做梦了!只有衣着光鲜,兜里有钱的人才带得走那个女人。”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那家餐馆吃饭,看着格瑞塞拉从身边走过,我感到有点不自在,因为我还不太会使用刀子和叉子……在家里,我们从不使用那玩意儿,因为我们吃的是玉米饼……不过,我很快就学会了,因为从那以后,我天天都去那儿用餐。我已经养成了习惯……实际上,在那样的地方,在其他餐馆,我浪费了十四五年的时间。
我问林先生能否给我一份活儿干,可那儿没有适合我干的事情。他教我烤面包,后来,我有时就在他的店里替他烤面包,以此冲抵我的饭钱。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跟阿尔维托打了赌,我要把格瑞塞拉弄到手让她做我的女朋友,于是我就动了起来。那需要钱,于是我对父亲说:“爸爸,我想挣点钱。我虽然在上学,但可以同时找点活儿干。”我把这事儿跟姨妈的丈夫伊格纳西奥说了,他说:“行,怎么不行,跟我一起卖报纸吧?那没什么不好的。”
第二天,我就跟伊格纳西奥卖起了报纸。我们去布卡雷利街等着批发“晚报”和“画报”。报刊的售价是一毛或一毛五,每卖出一份,我们能赚到四分半。我拿到报纸之后,姨夫说:“快跑吧。”
我问道:“往哪儿跑?”
“嗨,想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你得一边跑一边喊:画报,晚报!”于是,我就跑了起来,从卡巴利多特罗亚跑到了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接着跑上巴西大街径直来到了佩拉维洛,我在这里掉头又往回走,从我的家门前跑了过去。卖完报纸之后,我回到了中心广场。一到那里,我就把钱交给了伊格纳西奥。“很好,你看你赚了两毛钱呢。”我回到家,洗了洗脸,梳了梳头,就去上学了。
一开始,格瑞塞拉根本不喜欢我——甚至一点都不喜欢我。我之所以明白,是因为我有一次在里间的位置上吃晚饭,她竟对我视而不见。她一直都在跟阿尔维托聊天,还对他说:“要是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的话,千万别带曼努埃尔那个电灯泡,因为我根本不喜欢他。”
那番话对我的打击确实很大,“她怎么可以那样说话?我又没对她怎么样。”于是,我这样安慰自己:“可能就因为我想让她做我女朋友吧。”她还对其他服务员说:“他人倒是不错,可他不做事儿。什么事儿都不干,就像个傻子一样拿着几本破书浪费时间。我敢打赌,他连学都没去上。他既不上学,又不做事情,那我跟他有什么好处呢?”好吧,我很高兴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于是决定找点活儿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