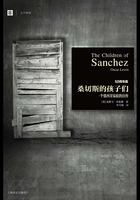
第9章 曼努埃尔(4)
六年级的期末考试即将来临,我很担心考不及格。老师们对我的评价不好,想把我赶出学校,可父亲向他们求情,希望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也就答应了。我通过了考试,终于毕业了。我多少有点失望,因为家里没有人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指望着父亲会祝贺我一下,或者给我一个拥抱,可他并没有这样做。就连我十五岁生日,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那可是男孩子真正成为男子汉的时刻,他都没有这样做。就连跟我说话的腔调他都没有改变一下!
毕业之后,我对父亲说,我不想再学习,想去找事情做了。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可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一心想让格瑞塞拉做我的女朋友,所以只想着要找一份工作,挣点钱。父亲觉得很恼火,因为我连学个技能的想法都没有。我在想,如果他能够跟我像朋友那样谈一谈,我也许就继续学下去了。可他说:“那么说,你是想找事情做了?你以为一辈子有人把你支过来支过去是那么好的吗?我还想给你个机会,可你自己把它抛在一边。好吧,当你的白痴去。如果你想这么做,尽管去做好了。”
阿尔维托早已在一家生产玻璃灯具固定装置的厂里做工。他既不会看书也不会写字,但他头脑聪明,挣的钱也不算少。因为我们俩想要在一块,于是我就到他的厂里去找活儿干。我跟厂长说我会操作机器和钻头,他就收留了我。
但是,我老是打碎玻璃制品,金刚砂让我的手指尖脱皮出了血,我感到一阵阵钻心的疼痛,只好坦白说我之前根本没摸过那些机器。于是,他们又安排我去打磨玻璃。打磨这活儿倒是很轻松,可是很脏,因为打磨用的材料是煤灰。接着,他们又教我用机器给挂件定形。你得用三个手指夹着一片玻璃,然后把它紧贴在飞轮上进行切割。我很快就上了手,他们也就让我留下了。艾莱娜的弟弟雷蒙多那时跟我住在一起,我还把他也弄进了厂里面。我跟他共用一台机器,我们俩一个星期就能做出两三千个挂件。
老板对我们很好,每到星期五,他会买票让我们去看拳击比赛,需要做到很晚的那几天,他会催着我们去吃晚饭。不过,那个死老板也懂得怎样刺激我们。他会对我说:“嘿,奇诺,雷蒙多说他干活儿的速度比你快。”
“啥?蛮牛一头!”我反驳道。“我是他的师傅,他怎么会干得比我快呢?”
然后,老板又会跑去跟雷蒙多说上一番,当然不会让我听到啦。“喂,奇诺干活儿的速度比你快两倍吗?他说他试都不试就可以超过你。”于是,我们两个傻蛋就展开一场比拼,加快进度,给老板做出更多的产品来。老板以这种方式让我们替他做了双倍的活儿。
薪水给得很少,而且因为我跟那帮小子一起在食堂吃午饭,所以到了星期六,我拿到手的就只有七个比索。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对爸爸说:“爸爸,你看,我的薪水还剩了五个比索,给你吧。”那段时间,父亲因为艾莱娜的去世对我相当刻薄。他正坐在餐桌旁,我于是把那五个比索放在了那里。他在那里站立着,狠狠地瞪着我,抓起那张五个比索的纸币朝我扔了过来。
“我不需要你这个小杂种的施舍。那点小钱自己拿去跟你那帮狐朋狗友花吧。我不需要你给我什么东西。我还壮实,还能够劳动。”那番话让我很受伤,因为天知道,我只有那么点钱。第二次,我还想把钱交给他,可他仍旧是同样的做法。从那之后,我就一分钱都没给过他!
后来,另一个老板给了我一份工作,在玻璃上钻孔。他开的价是计件支付,我每完成一件,他付给我三毛五分钱。其他地方给的报酬比较低,我考虑到可以多赚钱,也就接受了这份工作。整整一个星期,我干得又快又辛苦,竟然钻出了几千个孔!到了星期六,也就是那个星期快要结束的时候,老板说:“来,小伙子,让我们算算你能拿到多少钱。”那老头既不会认也不会写,于是请另一个小伙子给我把工资加了加。“让我看看,奇诺一共做了多少件。”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珠似乎都要鼓出来了,我的工资加起来一共是三百八十五比索。
“不行,年轻人,绝对不行!你才这么点年纪,我怎么可以付给你三百八十五比索呢!我还不如把整个工厂给你得了!我辛辛苦苦白干不说,还要供养你们这帮家伙。我是老板,就算老天爷高兴,我一个星期也不过挣五十来个比索。不行!我不可能给你那么多钱。问题是你干活的速度太快了。”
“可是,老板,既然你按件向我支付报酬,我当然得加快速度啊,对吧?你当初答应的也是每件三毛五分钱,不是吗?”
“是倒是,可我没想到你竟然要拿那么多钱!我只能给你一百比索,要就要,不要拉倒!”唉,我只好收下那点钱,可从此我也就不喜欢替老板干活儿了。
哦,对了,就在我刚刚开始做工的时候,格瑞塞拉做了我的女朋友。每天晚上,下了班之后,我都要去咖啡屋看她,直到深夜十二点才回到家里。我们一起去看过好几次电影,我开始感觉到自己爱上了她,那是一种真正的感情。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玩扑克和赌博。我第一次玩扑克是在一个星期六,我下了班回到位于卡萨—格兰德的家里的事情。就在附近的一个储水罐边上,有我的几个朋友跟其他几个人在一起,其中多明戈和桑提亚哥是我的朋友,桑提亚哥这小子因为杀了人,目前还在蹲大牢。桑提亚哥说:“嘿,看啦,劳动模范来了,王八蛋竟然变成了劳动模范。”
“对呀,你这蠢蛋整天只知道压马路,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不干正事吗?”我们经常这样子相互说说玩笑话。多明戈知道我口袋里装着那一个星期的薪水,于是对我说道:“哥们儿,来吧,我们玩一小会儿扑克。”
“大哥,那玩意儿我玩不来呀。算了吧,我才不当傻瓜呢。”
“我教你呀,我来教你怎样赢钱!来吧,我们只玩五分钱的,来,坐下。”
唉,他们知道我从来不会说个不字,于是,我们几个在储水罐后面可以照得见天井灯光的地方蹲了下来,围成一个圆圈。我自然输了,可也学会了规则。我学得很认真,整个星期不断地找人东问西问。我学得快,一个星期过后我就成了好手,可这既是长处,也是短处。说到玩扑克,我总是手气非凡。这样的手气似乎没有尽头,甚至超乎想象。
不经意间,我已经深深地陷入了玩扑克的旋风之中。如果哪天不玩上一两把,我就会觉得很不自在,于是总要找人玩上一阵子。我一开始只玩五分钱那么大,可很快就拿一个星期的薪水来做赌注了。我总是踌躇满志,以为自己要赢。即便不停地输钱,输到哪怕只剩五个比索的时候,我仍旧在心里想:“试试吧,也许老天爷都希望我靠这五个比索来翻本呢!”好吧,不出所料,十之八九,我把最后的五个比索都输出去了!
那帮小子会说:“小子,咋回事?莫非有人给你发牌的时候使诈吗,拿上来……别玩傻把戏……别把小牌藏起来……他妈的,不出老千,别人就不会怀疑了!”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有一次,我输了七十比索,不过那是因为那个名叫德尔芬诺的赢家提前走了,没给我们留下翻本的机会。他经营着好几辆大卡车,有很多钱,可他眼见赢了钱,就起身说道:“我得走了,我要去参加一个……老天,我差点忘了还有这么个鬼约会。”
眼见他起身要走,我的怒火陡然升了起来,因为我一把都没有赢过。“狗杂种,”我说道。“他当我们是傻子呀。”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通常在这一天聚在天井里踢足球。我去浴室洗了个澡,就在我抓起衣服往外走的时候,一头撞见了德尔芬诺。
“怎么了,奇诺?”他问道。“你小子想报仇吗?报仇是需要金钱和胆量的哟。”
“好吧,别以为老子是好惹的,走着瞧。”
他去叫来了多明戈和鸟儿,这两个人都是他老家恰帕斯的同乡,于是我们坐下开始玩了起来。一开始,我们玩的是“碰对”,看到我赢了钱,德尔芬诺就想改玩纸牌。
“好吧,”我说道。“啥玩意儿我都在行,不管你玩什么,这次你恐怕要点本事才能从我手里拿走这些钱。”
于是,我们玩起了扑克。呵,那可是应该记住的一场比赛啊!我一开始下了两比索的注,下到三十比索的时候,鸟儿认输了。接着,德尔芬诺下到了五十比索……他拿到的应该是一手好牌……他每拿一张牌,就要往上面吹一口气,然后放到胯下去擦一擦,为了来点好手气呗。
“你他妈应该弄热了再射出来,”他说道。“射出来才是一团一团的……我已经摸了三个七点,你可要想好了啊!”他说归说,却不让看牌,看见没?不过,我已经可以毙了他,因为我摸到了三张王,还有一张K。我很平静地下了超过五十的注。
“操你妈!”他说道。“你还真的全押上了。他妈的,你这混蛋那么有把握!”
“当然,老子全押了,但我有防身武器。老子我也不是吃素的。好你个王八羔子,别抖啊。把烟拿稳了,你的爪子在发抖!”
他又拿着牌在胯下擦了擦,但我已经吃定了他,因为我又摸到了一张王牌。
“你对着那玩意儿又吹又摸,老子就只有啃奶头的份儿了!”
他发现我的手里有四张王牌,于是说道:“操你妈!打死老子都不信。你那不是手气,肯定是老千!”
“喂,发牌的是你,又不是我。我那小宝贝今天很争气。要是没有傻瓜,我的大哥……”
那一场赌博下来,我赢了一千比索。然后,我站起身来。“伙计们,我得去……我都忘了还有个他妈的约会……他妈的,我差点给忘了。”
我跟你讲,我在卡萨—格兰德大名鼎鼎,算得上玩扑克的小小奇才。我发牌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盯着我的双手,可我发誓,我从不作假。只怪我运气好,好得出奇!我经常赢钱,有些小子发下毒誓,再也不跟我玩牌了。有人建议我去高级一点的赌场,可赌场的牌都做了记号。他们带我去过赌场。我对朋友们说:“我来这里只是想试试手气。我有点小钱花就很满足了,对不对?”
因为手气好,我在赌博上越陷越深。可糟糕的是,我在赌博上没捞到任何好处,因为每次赌完之后,我都会带上各位朋友和他们的女人,一起把赢来的钱花个精光。我赢了钱,可没做过一件正事儿。
父亲得知我赌博的事情之后,自然非常生气。可家里没有人知道我究竟靠赌博赢了多少,又花了多少。
每天晚上,我都会去咖啡屋看望格瑞塞拉。她围着几张餐桌忙得团团转,我多数时间只得在厨房里跟她同在那里做工的朋友保拉闲聊一通。好玩的是,我虽然疯狂地喜欢着格瑞塞拉,却宁愿跟“矮妹”,也就是保拉说话。我发现她很善解人意,于是便让她替我说两句好话,以便哄格瑞塞拉开心。当她看出我在吃某个小伙子的醋,或者因为跟格瑞塞拉吵架而不开心的时候,她就会说:“别担心,曼努埃尔。别在意她那么做,因为我知道,她打心眼里是喜欢你的。她这样跟我说过。”她经常跟我说这样的话,让我感到舒坦了许多。
事实上,我跟格瑞塞拉的关系很不稳固,我总在担心会不会失去她。我经常做梦,梦见她无耻地背叛了我,因此弄得自己很紧张。她长得很漂亮,追求她的男人可不少——那样子,她倒觉得很幸运。有些顾客会给她五十比索的小费。可她爱的是我,不止一次,她也很吃我的醋。后来我们终于崩了,因为我执意要跟矮妹一起去查尔玛朝圣。
保拉之前告诉过我,她要跟她的妈妈和妹妹德利拉一起去查尔玛。我也想跟着去,于是对她说:“就你们三个女人呀?那不行,我得跟你们一块去。”当我把这事儿跟格瑞塞拉说了之后,她说:“哦,你真要去吗?我看,你还是不要去。”
每当我们出现分歧的时候,我总会拿那件事儿把她训斥一番。我有自己的行事原则,我也向她表明过,尽管我真的很爱她,但我不会赖着她。我跟她这样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男人会为了女人而大打出手。不过你要是欺骗了我,我绝不会为你跟别人打架。”
大约在我动身前往查尔玛之前两个月的时候,咖啡屋来了个普埃布拉的小伙子,名字叫做安德烈斯,我发现他在关注格瑞塞拉,而她也在饶有兴趣地留意着他。就在我动身前往查尔玛的那一天,我把这事挑明了。
“安德烈斯你听着,你跟格瑞塞拉之间那些事我都看出来了,如果你还算是我朋友的话,你得跟我坦白。跟我说实话,我保证不会动你一个手指头。”
“别,曼努埃尔,格瑞塞拉既然是你的女朋友,她怎么会跟我好呢?”他说道。“她喜欢的是你,我可不是跟你玩阴招的那种人。”
同一时刻,矮妹和她的妈妈正在为朝圣旅途准备玉米饼和煮鸡蛋,按我们的话说,就是准备路上的盘缠。我们扛着几个大包,坐公共汽车来到了桑提亚哥—特米斯腾格。那一年跟我们同去的有阿尔维托。我们几个人——我、阿尔维托,还有矮妹——一路上十分开心,一边祈祷,一边唱歌。我们趁着黎明的美景,穿过了一片片树林。松树的香味,乡野的味道十分美妙,行走在山峦之巅,我们时不时可以看到远处的小村庄,个子矮小的印第安妇女们正在做玉米饼。
离神庙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棵高大的蒙特苏玛丝柏树跟前,朝觐者一般都要在此稍事停留。在通往查尔玛的路上,这棵大树真是个宝贝疙瘩,上面挂满了女人的发辫,小孩子的鞋子,以及其他足以表明朝觐者信念的种种物品。树干极其粗大,我猜要十个人才能合抱。那棵大树生长在两座山峦之间,一条小河从它边上流过。嗨,我们这些朝觐者走到这里已是疲倦之至,于是满怀虔诚地把双脚浸泡在似有疗效的河水里,身上的疲乏和不适顿时一扫而光。进了查尔玛,一条道路蜿蜒曲折直通神庙。进入教堂,跪在清凉的暗影里,看着查尔玛这尊至高无上的救世主的塑像,我的心灵总能得到巨大的满足。他好像只为迎接我一个人的到来,这令我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因为我当时对他充满了极大的虔诚。我祈求救世主赐予我力量,向我展示一条挣钱的路子,好让我娶得起格瑞塞拉,祈求她不要抛弃我。
一路上,我和矮妹绝对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相反,我希望阿尔维托和保拉能够成为情人,这样我们四个人就可以经常出去玩了。一路上,整整七天的时间,我跟保拉讲了我和格瑞塞拉之间的麻烦。可后来,我发现她看我的眼神很有些不一样。有一次,我装着被一只毒蝎子咬了一口。我晕了过去,然后人事不省。她被吓呆了,可怜的人啊,仅仅为一个普通朋友,你不可能吓到那个分上。于是,我问自己:“老天!这是真的吗?她可能爱上我了。”可我根本没想过要跟她有任何瓜葛。
我对着查尔玛之神的祈祷失灵了,因为我一回来,安德烈斯就告诉我,格瑞塞拉已经是他的女朋友了。我很生气,很想敲碎他的骨头,可我得遵守不动他一个手指头的诺言。“好哇,安德烈斯,除非她亲自来跟我说。”
“哦,”他回答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从现在起,我不许你跟她还有任何牵连。”
“哦,是吗?”我说道。“那么,现在你跟我之间就不再是朋友之间的事儿,而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事儿了,我就让你看看,我比你更像个男人。”接着,砰!我狠狠地一拳揍过去,把他打了个仰八叉。我把他一把提起来,靠在墙壁上,对着他的肚子,砰!砰!砰!
我找到了格瑞塞拉。“你好,”我对她说道。“我给你带了件礼物,是我在查尔玛买的一个小镜盒……可安德烈斯跟我说了你们两个的事儿,我就把它踩碎了。”我凑过去问道:“格瑞塞拉,安德烈斯真是你男朋友吗?回答我,别害怕。”
她站在那里,十分忧伤地看着我。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点了点头。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想抽她两个耳光,可我从来不对女人动手,那会让她明白,我有多么爱她。我克制住自己。“好哇,真好!恭喜你啦,格瑞塞拉!你看我只知道赌钱,无论输赢,都只会老老实实地赌。这次我输了,是不是?没事儿,格瑞塞拉,跟我握握手,我们还是朋友,别难过。”
她非常愤怒地站在那里,放声大哭。“滚蛋吧,”我这么说了一句,就转身离开了。
对,这件事儿让我很不开心。我换了工作,转而为几个西班牙人做起事儿来。刚开始的薪水是每天八个比索。星期天他们照常支付我工资,所以我每个星期能够挣到五十六比索。我现在能够挣到更多的钱,也无须上交给我的父亲。
说到格瑞塞拉这事儿,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她这么对我,我一定要报复她,我要找一个跟她很亲近的人,让她真正地难受一下。我要让她也尝尝这种滋味。”我立马就想到了矮妹,于是便对她展开了追求。从那之后,我每天都去咖啡屋看望保拉,我要她做我的女朋友。
“可这样做不对呀,因为你还爱着格瑞塞拉。你怎么能跟我这样说话呢?”
“不,我跟你这样说了,你才去对她那样说,让她觉得我是真的爱过她。可实际上我不再爱她了。再说,我每次来的时候,不都是在跟你说话吗?”
我不知怎么会跟她发生争执,可追起矮妹来总归是难度非常大。
持续了一个月的样子,其间她老是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后来,她终于说了句:“嗯,好吧。”到此,她终于答应做我女朋友了。
为此,保拉和格瑞塞拉狠狠地吵了一架。保拉说:“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安德烈斯是他的朋友,你们不也跟他玩了损招吗?再说,你跟他又没结婚,他只不过是你的情人而已。现在,他是我的情人,我很爱他。”
接着,格瑞塞拉说道:“可问题是,安德烈斯真的不是我男朋友。我之所以这么说,只是想看看曼努埃尔是否爱我,因为安德烈斯跟我说过,曼努埃尔一直都在耍我。”
安德烈斯做通了格瑞塞拉的工作,要她来试试我,于是他们上演了一出戏,让我掉进了陷阱。这样一来,我才感到自己根本不爱保拉,可出于永恒的虚荣心,也就是墨西哥人那愚蠢的大男子主义,我不可能自取其辱去跟格瑞塞拉重修旧好。我全身心地爱她,我真想对她说:“回来吧……让我们认认真真地
……”但我把尊严和虚荣看得高于一切。我在心中告诉自己要跟她讲实话,可又害怕她会取笑我的恋恋不舍。我们之间就这样耍着手腕,一点一点地,谁都没有了意愿,各走各的路了。
于是,我继续去看望保拉,并约她出去。我让她辞了咖啡屋的工,她后来另找了一份工作,编织小孩衣物。
有一次,我察觉保拉对我撒了谎,于是我认为她在欺骗我。她跟我说她要去克雷塔罗看望她生病的妹妹,可就在她走了之后,德利拉说漏了嘴,说保拉实际上跟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性朋友一起去了韦拉克鲁斯。保拉回来之后,我问她:“保拉,克雷塔罗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嗯,还行。”
“你妹妹呢?”
“唉,她病得很厉害,可你知道,有些人说话总是喜欢夸大其词。”
说到这里,我扇了她一个耳光。“少跟老子废话,你根本没去克雷塔罗,少来骗我,你不是去韦拉克鲁斯逛了一趟么。”
“谁跟你说的?”
“总有人啊,”我说道。“这么说,你真是去了韦拉克鲁斯喽?”啪!我又扇了她一个耳光。我当时真是气极了,于是打了她。
她哭了起来。“是的,曼努埃尔,可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要是我做了什么坏事,我最亲爱的母亲将不得好死。实际上,是我的女朋友要跟她的男朋友一起出去,于是她让我一起去,好对她有个照应。”
我很肯定地认为,保拉一直在骗我。“算了,小姐,”我对她说道。“我在你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捞到,如果你那么容易让人捞到手,那你就跟我来,我们马上去找旅馆。”
“别这样,曼努埃尔。”
“别什么?”我说道。“你不是跟别的男人出去了吗?如果你想做站街女郎,那你就跟我走,你告诉我要多少钱。你不过值个五六毛钱吧,我可不想给那么多钱。”
她在那儿哭个不停。“曼努埃尔,跟我走一趟,求求你跟我走一趟。”唉,我的内心期盼着她没有做任何坏事儿,于是来到了她朋友的家里,那女孩证实了保拉的说法。
我仍旧不完全相信,所以管她愿不愿意,那天晚上我带着保拉去了一家小旅馆。
我要说明一下,在墨西哥,至少从我这个例子看来是这样,即便我相信我的女朋友真的爱我,可我依然充满了怀疑,仍然会吃醋,对不对?于是,到了某一天,男的会说:“既然爱我,就要证明给我看。如果你爱我,那你就要跟我走。”我根本没想过要举行世俗的,或者是教堂婚礼,根本没想过,我所认识的男男女女大多如此。我一直是这样想的,如果某个女人爱我,而我也爱她,我们又愿意在一起过日子的话,那一纸法律文书完全无关紧要。如果我女朋友提出要求,要我跟她履行结婚手续,给她修一栋房子,我马上就会有一种受伤的感觉,我会对她说:“这么说,你并不是真的爱我!如果我们的爱情需要设定一些条件的话,那算什么爱情呢?”
贫困也是一个因素。如果一开始就要看婚姻的归途,那么穷人就会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钱来举办婚礼。这样一来,他就会不举行婚礼而照样过日子。他会跟一个女人过日子就行了,就像我跟保拉那样。再者,穷人没有钱留给他的孩子,也就不需要向他们提供法律保障。要是我有一百万比索、一栋房子、银行存款,或者是某种实物的话,我会立马公证结婚,以保障我的孩子们具有法定继承权。可我这个阶层的人一无所有啊,所以我说过:“只要我认自己的孩子就行了,别人怎么看我根本不在乎。”
世俗婚姻不像宗教婚姻那样需要花费很多钱财,但也排除了法律责任。我们有种说法:“婚姻的幻想止于床上。”我可不愿意为了今后可能成为败局的婚姻而给自己套上法律的枷锁。如果我们现在对彼此的了解不够深入,又怎么知道生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这里的女人也大都不指望婚礼这回事儿,她们甚至觉得做情人比做老婆好。现实情况是,女人可以跟男人走,可不等五六个月的蜜月期过完,她就会强烈要求那个男人跟她结婚。不过,这只是传统女人的做法,她们所需要的是用链子把男人们拴住。
我们坚信,做情人是一回事儿,做男人和女人又是一回事儿。如果我要某个女人做我的老婆,我会觉得对她要承担诸多责任,那跟我们结了婚没什么两样。婚姻改变不了什么!我和保拉就是这样。
一连数月,我们继续偷偷摸摸地去旅馆开房,可我并不感到满足。我觉得自己从内心里想摆脱我的父亲,想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离开那个家,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于是,我在一天晚上对她说:“拿个主意吧,保拉。你看啊,我要走这边,可你的家在另一边。从现在起,我不想让你回那个家了,你看怎么样?”
“不行,曼努埃尔,”她回答道。“我的妈妈,还有那几个弟弟妹妹怎么办?”
“算了,你并不爱我。两条路随你挑,如果你还要回你那个家,我们今后就再也不要见面了。如果跟我走,你就是我老婆了,需要跟我生活在一起。”
哦,她终于打定了主意,没有回家,跟了我。我们就这样结了婚:我刚满十五岁,她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