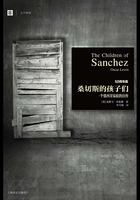
第7章 曼努埃尔(2)
不过,罗伯托一直很难对付,我敢说没办法对付。他很倔强,为了一丁点小事就可能跟人干上一架。艾莱娜说:“把地擦了。”罗伯托会说:“为什么要我们来擦?你才是家庭主妇。”就这样,一场争吵发生了,等到父亲回家的时候,艾莱娜会假惺惺地号啕大哭。于是他抽出皮带,给我们俩一顿好打。他还会让我们擦地板,洗碗碟,而艾莱娜坐在床上哈哈大笑,惹得我们愈发生气。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正围着餐桌吃饭,有我的后妈,我的两个妹妹,罗伯托,父亲和我。我喝咖啡的时候,偶尔转过头看了父亲一眼。他当时正瞪着我和罗伯托,好像很讨厌我们的样子,只听他说:“看你们的吃相就让老子恶心,看看你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兔崽子。”我们什么也没干,可他竟然那样说我们。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跟父亲同桌吃过饭。
没了母亲,我们几个小孩子本应该更加团结,互相支持。可我们一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父亲总要在我们两个男孩子和两个妹妹之间横插一脚。他横在那里,不让我履行一个大哥应尽的义务。要是母亲健在,肯定是另外的情形。她深信传统,年幼的应该尊敬年长的。要是她还活着,我的两个妹妹也许会尊敬我和罗伯托,我们也不会滥耍威风。
在墨西哥有这样的思想,老大应该照管下面的弟弟妹妹,也就是让他们懂得规矩。可父亲从不允许我这么做,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两个妹妹,因为我没法纠正她们。他会说:“你是谁,王八蛋?你有资格打她们?老子才有资格。你们两个龟孙子谁敢碰她们一下。”
我的两个妹妹,尤其是康素爱萝,总想在我们和父亲之间制造恶心。她知道怎样才能惹他来揍我们,或是揪我们的耳朵。从一开始,父亲就不让我们跟她玩儿,也不让她乱跑,因为她个子太小,因此,嗯,我没太把她当一回事儿。康素爱萝是个很令人心烦的孩子,真的,没有谁比她更烦人。我轻轻拍她一下,她就会哇哇大哭。父亲回到家的时候,她就开始揉眼睛,把眼睛揉得红红的,他就会问:“怎么回事,孩子?怎么了,乖女儿?”接着她就开始添油加醋。不过就是轻轻扇了她一下,她却会说得像着了火似的。“爸爸,你看,他打我的胸部!”她总说我们打她的胸部,因为她知道我们打她那儿准让爸爸发火。他有点惯她,因为她骨瘦如柴。接着呢,当然了,他会给我们一顿好揍。
“骨瘦如柴”——我们就是这样称呼康素爱萝的——总是在我父亲面前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像她是受苦受难的修女诗人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卢斯。虽然吃尽苦头,忍辱负重,她依旧非常小气,铁石心肠,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她老是以自我为中心,唉,我那个妹妹让我和罗伯托十分抓狂。
我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对我们男孩子如此苛刻,对女孩子如此偏爱,对她们说话是一个腔调,对我和罗伯托说话又是另一个腔调,也许是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旧体制下的缘故吧。有两三次,他回忆起自己过去的日子,对我们说,我的爷爷对他很严格,经常打骂他。因此,他觉得要我们尊重他,必须首先得像个男人的样子,然后才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从没跟他顶过嘴,一直非常尊重他,事实上我们还很崇拜他,可他为什么对我们是那样的态度呢?
父亲打骂我们倒不是因为他性格残暴,而是另有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为了他跟艾莱娜的爱情。对他而言,老婆比孩子重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打骂我们就是为了替她出气,哄她开心。从内心来说,他是爱我们的,希望我们多少有点出息,一旦发现我们做了坏事,他就觉得我们在骗他,让他觉得很失望。他曾经说艾莱娜是圣人,而我们是一群混蛋,居心不良,不愿意了解她,不想让她过好日子。不过,依我看,他和艾莱娜的婚姻既有感情也有感激,而我父亲呢,唉,太过专情。我觉得他对艾莱娜的爱不如他对我母亲的爱,母亲是他的初恋,也是他的真爱。
说到我的后妈呀,我还是不说为妙吧,因为我知道那对我也不会有任何好处。我总是叫罗伯托不要乱说,可他觉得没有理由不说,反正那个女人不是他的亲妈。艾莱娜对两个妹妹要好些,因为她们是女的,而且太小,根本不知道跟她对着干。可我们两个男孩子已经长大了,分得清。
有一次,我们正在聊家事,我无意中告诉艾莱娜,我母亲有时候会深情地称我父亲为“老公猫”。艾莱娜一听就说了我母亲的坏话,差点把我惹急了。我母亲爱我父亲有她的方式,也就是有个昵称,艾莱娜没有资格侮辱她。我跟她大吵了一架,父亲回家后把我揍了一顿。不过,她平时说话伤我的时候,我总是默不作声。我呢,唉,总是小心谨慎,而罗伯托就像是个火山口,只要一碰,他就爆发了。
只要有什么不对劲,把什么东西弄丢了,不问青红皂白,受责骂的总是罗伯托。有一次,他因为一件我做的事情被训了一顿,自此以后,我觉得十分愧疚。我也就做过那么一次。还有一次,我的朋友桑提亚哥对我说:“从你家里偷点什么东西出来,我们去看一场电影吧。”我一下子就发现了爷爷传给父亲的那尊耶稣受难像,于是从家里拿出来跟他一起卖掉了。
那天晚上,他们到处找,到处找,怎么也找不到那尊塑像。然后,他们以为是罗伯托偷了,就把他揍了一顿。我很想坦白,但看见父亲非常震怒的样子,也就害怕得闭住了嘴。这件事儿我跟谁都没说过。反正就那样,只要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受责骂的总是罗伯托。
妈妈过世以后,罗伯托就开始偷拿家里的东西。家里如果丢了东西,多半是他干的。耶稣受难像之后,我再也没有偷拿过家里的东西。罗伯托继续偷,他还小,是个小贼,有些东西是他那帮朋友让他拿出去的。比方说,爸爸拿回家一打鸡蛋,罗伯托会拿上一两个到外面去卖了。他用这种方式来搞零用钱。我可怜的爸爸入不敷出,日子很难啊。只要有需要,他总会给我们买鞋子买衣服,给我们买最好的学习用品,但有时候一连几天,我和罗伯托的零用还不到五毛钱。我常羡慕我的同学,他们总有棒棒糖或其他零食可吃。唉,那个时候我们经常感觉不爽。可爸爸挣不来那么多钱,满足我们几个的要求。现在我终于理解了。
上到五年级,我交了第一个女朋友。她叫艾丽莎,是我朋友阿丹的姐姐。我经常去阿丹家唱歌,因为他会弹吉他。艾丽莎的父母把她看得很紧,不过他们认可我跟她的弟弟交朋友。我抓住机会,开门见山地要她做我的女朋友。她比我大,比我高,我只有十三岁,得站在什么东西上才能吻到她。我带她一起看电影,又吻又抱。但跟女朋友也只能那样,如果上了床,差不多就算结婚了。
为了那帮朋友,我顾不上学习。不过我的老师,也就是埃弗拉多先生是个相当不错的人,你我都是男人,完全可以那么说,我也算是他的朋友。我刚进学堂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后来回忆起总觉得心满意足的事情。我们班上有个男生名叫布斯托斯,算是学校的霸王,因为他跟小不点们比拳头总能轻易取胜。入学的第一天,老师们有会要开,布斯托斯就来看管我们班。他要我保持安静,可语气很不友善,我于是回敬道:“嗨,虾爬,别冲我吼叫。”
“叫我别吼叫?”他回答道。“那你有种喽,好好好。”
我说道:“我不一定有种,可你要以为你个头大,就跟我一样够胆,那伙计你就错了。我住在特皮托,从不跟别人说废话。”
对,就在教室里,我重重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他的鼻子和嘴巴立即鲜血直流。男生们立马起哄:“哇,布斯托斯,一个小孩子就把你揍扁了。”从那以后,他们就给我起了绰号“二十号”,因为那是我的点名顺序号。因为我把全校最大的块头给收拾了,立马在学校里声名大振,大家纷纷议论,说什么二十号打架很有一套。从此,再也没有男生敢惹我的麻烦,我个头虽小,但长得结实,出拳有力。
何赛法·里奥斯是我真正爱上的第一个女孩,她长着黄头发,白皮肤,十分漂亮。有个男生名叫潘乔,他的父母比较有钱,他也长得很帅。是的,我爱何赛法爱得发疯,可她却喜欢潘乔,而潘乔对她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很嫉妒,一直想找潘乔打一架,这样何赛法就知道我比他强了。可潘乔根本不想跟我打,因为他知道布斯托斯就是我搞定的。
有一次,校长的圣徒节到了,全校各班都要表演节目以示庆贺。我们班什么都还没准备。一天,我很早就来到了学校,学校里一个人都没有。一如往常,每当感到开心或者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唱唱歌。我没发现埃弗拉多正在听我唱歌。他走进教室说道:“曼努埃尔,你看你的声音多好,我们就用这个来庆祝校长的圣徒节吧。”我当时不明就里,可没过几天事情就来了。一年级表演了跳舞,二年级表演的是朗诵,三年级做了别的表演,依次终于轮到了五年级,只听他们报幕说道:“五年级,第一个节目,一支献给校长的歌,由曼努埃尔·桑切斯·威雷兹同学演唱。”哦,老天!我一无所知,吓得要死,何赛法就站在第一排。
我躲到桌子底下,不愿意出来。每个人都在看着我,还是布斯托斯把我拽了出来。我被同学们像个囚犯似的拽了出来。我登上台,唱起了那时候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爱、爱、爱……你的爱,我的爱,希望的爱……”一时间,我的嗓音更加清脆,实话实说,我还能唱得更高一些。我一边唱,一边紧张害怕,一边不住地偷看何赛法。接着,犹如大梦初醒,我听到掌声响了起来,响亮极了。哦,我觉得骄傲极了,何赛法也在鼓掌,而且鼓得比任何人都起劲儿。我在心里想着:“啊,上帝呀,莫非她今后会对我刮目相看了?”嗯,从此我巴不得他们让我唱歌。
那天下午,我问何赛法:“我有事跟你说,你愿意跟我见面吗?”我记得很清楚,当她这样回答我的时候,我真是高兴极了:“六点钟在我家旁边的街角等你。”我当然开心极了,于是准时在六点钟过去了,可她没有现身。就在当天,潘乔也找她说话了,所以,她自然而然地跟他走了,按这儿的人们的说法,就是让我“苦等山顶吹残笛”。
嗯,学校的日子日复一日,我每个星期至少逃学一次,还跟同伴们学起了抽烟。我们走在一起,其中一个家伙一边说“怎么样,来两口?”一边把烟递到了我的手里。我深吸三口,然后递给另一个人。
我得背着父亲抽烟。如果他毫无征兆地进了家门,我甚至只好把点着的香烟吞进嘴里。他抓过我一次,那时我十二岁,跟一帮朋友正在天井里抽烟。当着大伙儿的面,他说道:“好哇,小杂种,竟然学会抽烟了?你就抽吧,等你回屋来,小王八蛋,看我不……”从此,当我讨要香烟的时候,他们就会揶揄我:“别,小子,你爸爸要揍你,我们可不给你烟抽。”
我到二十九岁才第一次敢当着父亲的面抽烟。那也算是一种小小的反叛,是吧?我这么做还是有点不自在,但我就是想让他看看,我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回首往事,我好像不太有家事。我跟家人的关系不太明显,在家里的时间很少,我甚至都记不起我们做了些什么。再说,我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记得清。我不大喜欢中规中矩的事情,只有那些最好、最坏,或者激动人心的事情长留在我的记忆中。
不是我忘恩负义,可说起我父亲……唉,事实是,他经常虐待弟弟和我。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我们为睡觉的那块地方付出代价,为我们吃的面包付出代价,以此来羞辱我们。的确,他很负责也很尽责,可老把他自己的倔强强加给我们,从不让我们说出内心的看法,也不让我们跟他亲近。要是我们问他什么,他会说:“小子!你懂个屁!闭嘴!”他每次都不让我们说话。
在一定程度上,我不回家他有过错。我从没觉得那是我真正的家,因为我连朋友都不敢带回去。到了下午和晚上,喜欢阅读的父亲会把我们赶到天井里来。“滚出去,驴蛋儿们。老子累了一天,还没法安安静静看会儿报纸。滚出去!”如果非要待在屋内,我们得保持绝对安静。
也许我有点过于敏感,可我父亲不近人情的做法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他的累赘。如果没有我们几个,他和艾莱娜的日子会过得更好,我们就像一群拖油瓶,他只是不得不带着而已。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吃饭的时候,他满怀仇恨地瞪着罗伯托和我的眼神。我跑到厨房里哭了起来,心中的郁结让我吃不下饭。
有好多次我都想说:“爸爸,我们到底把你怎样了?为什么你总觉得我们一无是处?为什么你拿我们当犯人一样对待?你难道不知道有的孩子沾染恶习,对家人恶言相向,甚至于谋害爹妈吗?”当然,等到哪天,如果我有胆量的话,我会好好跟他说这番话。
然而,无论何时,当我想对父亲说说话的时候,总觉得如鲠在喉。面对其他人,我的话多得多,对吧?可面对他的时候,我总觉得喉咙里有东西,说不出口。不知道是因为我对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尊敬,还是一种害怕。也许就因为这样,我宁愿躲开父亲,甚至家里的其他人。我们之间有一道鸿沟,有一种不和睦,尽管我很敬重他们,可每当看见他们遇到的那些事儿我都觉得非常难受,于是就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对,这当然是一种自私的态度,可这样对我自己和他们的伤害都会小一些。
我原来经常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实际上,大街才是我的生活场所。我一般下午才去学校,上午我要跟朋友们一起去鞣皮厂做工,也就是在皮革上雕花。只在拿课本的时候,我才会回家。我还是在家里吃饭,可一吃完饭我就溜出去了。我这样做真是不想跟后妈惹麻烦,也不想挨打。我父亲也懒得说,我猜这样对他也比较好。
我从小就喜欢劳动。我肯定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劳动了,因为自从我做了头一份事情,父亲就经常安排我做事儿,而我一拿到钱就立马交到他的手里。记得父亲第一次一边拥抱我,一边说“我终于有个帮手”的时候,我的心里真是乐开了花。我在离家几个街区之外的一家鞋厂打杂,一直干到深夜,有好几次甚至干通宵。那时候我可能还不到九岁吧。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做腰带,后来又到大街上兜售过彩票,还跟艾莱娜的弟弟一起干过一段时间,替外祖母的堂弟的一位石匠儿子打下手。上学期间,我还到一家面包店当过守夜人。我舅舅阿尔弗雷多也在那儿做工,他教我做各式各样的饼干。回顾过去,我的一生似乎都在劳动——只不过那些工作都不怎么有创造性,那么,他们为什么老说我是个懒家伙,这也不是人,那也不是人呢?
读到最后一年,他们给我发来了退学通知书。埃弗拉多先生很欣赏我,但他也教不好我。父亲令我纠结不已,我觉得老师对我也不公平。从此,我对学习完全没了兴趣。说到语法,说到动词变位,我都是白痴一个,只有数学还算马马虎虎。不过我在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方面可以说是出类拔萃,这两门课令我十分着迷。
说到运动和体力,我在班上数一数二。我一直是短跑好手,六年级时的一百和两百米短跑都得了第一名。我也喜欢跟汽车有关的东西,甚至曾经梦想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不过,这全都落了空。
我们仍旧住在古巴大街,跟外祖母离得很近。她依然会来看望我们,给我们送些小点心、小糖果,或是衣物之类的东西,也会打听继母对我们怎么样。有一次,因为父亲打了我,我就跑去了她那里。我想跟她一起生活,可父亲当天晚上就把我弄了回去。
我对日期记不大清,但我记得我们搬到卡萨—格兰德的日子,因为那天是我父亲的圣徒节,也是在那一天,我的外祖母去世了。当舅舅派人带来死讯的时候,我父亲说:“真是给了我一份很好的大礼啊!”
头一天,她就派人来叫我们,我有一种印象,她早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她过世的时候,耳聪目明,给每个人都留了遗言。她对我说道:“跪下,孩子,我要睡觉了。照顾好你的弟弟妹妹。你一定要学好,生活才会善待你。孩子,别淘气,否则你妈妈和我的灵魂都得不到安宁。”她要我们随时替她念天父经,否则会觉得食不甘味。然后,她又替我们祈了福。我的喉咙里一阵哽咽,可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便强忍着没有哭出来。何塞舅舅照旧喝他的酒,在她的屋外手舞足蹈。
瓜达卢佩姨妈和几个舅舅替外祖母做了清洗,穿好了下葬的衣服。那天,他们在床上铺了张干净的床单把她放在上面,然后再去买棺材。他们四个人合力把她抬进棺材,在上面摆放了醋盘子和洋葱,以吸附死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浊气。我们赶过去替她守夜的时候,她的头部和脚边各点燃了两根蜡烛。一整夜,人们坐在那里喝着浓咖啡,吃着面包,讲着荤笑话,令我感到非常气愤。我父亲坐在一边,跟几个舅舅说着话。我听见他说:“阿尔弗雷多,你看看我们这种情况。忤逆、不和有什么用?这就是结局,这就是现实。”他们一直有矛盾,可父亲好歹帮着解决了葬礼所需的开支。
啊,我们就开始了在卡萨—格兰德的生活。那儿的孩子被称作卡萨—格兰德帮,老想惹我打架。我在学校里打架从来没输过,因此当那一帮人把我团团围住,派出最强的一个来挑衅我的时候,我对他说道:“来吧,小子,你完蛋了。”
我们干了起来。双方都流了血,但他更惨。之后,只有一个人敢跟我打架,那小子的诨名叫做蠢驴,因为他的阴茎很大。有一天,他把我弟弟的牙齿整掉了一颗,我因此找上了他。我和蠢驴狠狠地干了一架。我一拳打得他哇哇大叫,等他发现用拳头占不了我便宜的时候,竟然动起了口。我肩膀上还有印子,就是他用牙齿咬的。从此,他成了我的好朋友,甚至比我自己的弟弟还亲,因为我们根本不分彼此。蠢驴是我现在的哥们儿,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名叫阿尔维托·埃尔南德斯。
从那一架开始,我跟上了阿尔维托。我有点喜欢他,尽管我的观点时常跟他相左。不知为何,他的想法还没说出口,我就已经开始反对了。可在大事情上,比如有人想跟我们其中一个干上一架的时候,我们总是团结一致。我们每天都见面,阿尔维托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一句话,我们穿了连裆裤。我们彼此信任,患难与共,互守秘密。他经常请我的客,因为他在做工,钱比较多。
阿尔维托比我大一两岁,可他在各方面,尤其是对女人很有经验。他有波浪一样的卷发,眼睛很大。即便他是个乡下孩子,说话像个印第安人,但女孩子们都喜欢他。他懂的事情多,这让我吃惊不已。我还是个学生娃的时候,他已经在帕丘卡一家矿上做工,擦汽车、端盘子,沿公路线边流浪边干活。他从未上过学,因为他从小就得自己养活自己。他的日子比我还要艰难,因为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才是个婴儿,而他的父亲根本不管他。一开始是他的外祖母照看他,后来又交给他妈妈的一个妹妹看管。他就跟这位姨妈和她的丈夫一起住在卡萨—格兰德。
尽管我比他小,阿尔维托还是跟我说起了床事,比如各种姿势、女人的舔舐等等。说起女人啊,他这个龟儿子!即便到现在,我敢说,他也是弄小妞的好手。我们都叫他“一天三次”,因为他骚劲十足。嗨,我们有一次出去卖报纸,他站在汽车边上,看见女司机的衣服翻起来露出了膝盖,他竟然把手伸进裤袋打起了飞机。
我们一帮小孩经常去浴室,透过墙上的小洞偷看女孩子洗浴。有一次,阿尔维托跑来告诉我们,漂亮的克洛蒂尔德正在洗浴,于是我们四个人租下了紧挨她的那间浴室,看她洗澡。她全身赤裸,让我们看了个遍。我们一边偷看,一边把手伸进裤袋,上下摩擦,比赛看谁最先射出来。
阿尔维托和我都是卡萨—格兰德帮派的成员,总共有四十人的样子,我们常在一起玩诸如驴子之类的游戏,或者讲下流故事,并且对于自己维护着卡萨—格兰德的声威时常感到自豪不已。理发匠大街、漆匠大街,或者铁匠铺大街那几帮家伙根本占不到我们的便宜。在舞场上,我们睁大眼睛,确保他们不会打卡萨—格兰德各位女孩子的主意。
每逢9月16日,总有一帮人拿着棍棒前来挑衅我们。我们一般会让他们从一个门进来,然后让看门人的儿子——他也是我们这一边的人——把另一道门上了锁。等他们全都进来之后,他又会跑过去把第一扇门同样锁上。然后呢,我们就在天井里教训他们,石头啦,水桶啦,棍子啦等等全让他们挨个够。
我们从不让任何人占半点便宜,我和阿尔维托总是迎头而上……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打架的好手,总是担任前锋率先冲向其他帮派。那时我们经常打架,现在都还时时梦到。我梦到自己和阿尔维托被五六个人围在中间,我跳起身来躲过他们,向上一跃抓住电线,谁都抓不到我。然后我高喊着:“嘿,我飞起来了!”接着,我竖直双腿,落回到地面,对阿尔维托说道:“哥们儿,上来。”他爬到我的背上,我又飞了起来。“看见没,他们拿我们没办法了!”我一直飞呀飞,直到越过了电线。突然,我一下子重心不稳,掉了下来。这样的梦我一做就是好多年。
事实上,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近距离地看惯了生活的实质,一定要学会自我控制。有时候,我很想大哭,就为了父亲对我说的那些话,可不行,因为生活,因为愤世嫉俗都教会我们,带着面具生活吧,于是我又笑了出来。因为他,我说不上受苦,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纯粹是无耻的玩世不恭,没有灵魂……因为我给别人看的都是面具。但在内心,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深有感触。
我已经学会掩藏自己的害怕,只能以胆量示人,因为从我的观察来看,你给别人留下怎样的印象,别人也就怎样对你。因此,当我内心极度害怕的时候,我总是装得若无其事。那当然有一定的作用,看着自己的朋友被警察逮住时吓得瑟瑟发抖的样子,我就觉得那点苦算不上什么。如果一个小伙子表现得畏畏缩缩、眼含泪花、祈求怜悯,别人也就敢欺负他了。在我们那一带,你要么天不怕地不怕,要么当个大傻瓜。
不光墨西哥人,我相信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崇拜“有蛋”的人,我们就这么说的。那些动辄挥拳踢腿,丝毫没脑子的人到头来会出人头地。有胆挑战比他岁数大的、比他强壮的人,会更受人尊敬。如果有人冲你吼叫,你要吼得比他更大声。如果有哪个杂种敢对我说“操你妈”,我会对他说“操你妈的平方”。如果他上前一步,而我退后一步,那我就没面子了。可如果我也上前一步,欺凌他,戏弄他,别人对我就尊敬了。打架的过程中,我从不认输,也不会说“够了”,哪怕对方杀了我我也不会。我宁愿去死,笑着去死。我们说一个人要有点男人样,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