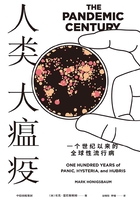
译者序
TRANSLATOR'S PREFACE
“所有人的生活里都有一部历史。”
——威廉·莎士比亚
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是位有趣的作家。
当他在著名媒体《卫报》和《观察家报》发声时,他是一名出版了多部畅销书的获奖作家和资深记者;当他为国际医学顶级期刊《柳叶刀》撰稿时,他又是一名专业的医学史学者。翻开这本书,你不仅能感受到他出色的文字把控能力,更能体会到他在医学科普、医学史领域的造诣。对于他的这本《人类大瘟疫》,英国著名医学史家威廉·拜纳姆(William Bynum)的评价是,本书对流感的讨论极为精彩,可读性很强。《柳叶刀》也点评道:这本书“引人入胜”,“精彩地描述了疾病的定义和分类过程,并指出文化因素极大地左右了我们对疾病的感知,影响了我们对瘟疫的反应”。
然而,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的这本书并不“好读”。
这是一本时间跨度长达一个多世纪,内容涵盖了8种重大流行病的史书。作者的讨论涉及了病毒学、分子生物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科学哲学、医学史等多个学科。在翻译本书时,我们一方面钦佩作者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又不禁忧虑:对于文科读者来说,这本书似乎显得太“科学”;对于医学读者来说,它又好像有点太“社科”了。倘若投入大众市场,它更是看起来缺少“噱头”,不够“快餐文学”。究竟会有多少人愿意翻开一本论述“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的判定”“冠状病毒的发现过程”“气溶胶如何在建筑物中传播”等专业知识的传染病史书?又有多少读者能静下心来,在一页页充斥着学术名词的纸张中,细细品读疫病流行中的病原学研究、公共卫生应对,以及复杂的社会影响?
2020年年初,全书译稿将毕,一场大疫忽然降临。新型冠状病毒袭来,多地隔离检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入“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仿佛就在一夜间,历史与现实魔幻般地叠合到了一起。那些曾经只见于医学杂志上的病毒学知识以及流行病学研究都成了新闻热点。它们与无数个无意或有心的传言混杂在一起,共同冲击着大众的眼帘。那些凝结于书中的悲伤、恐惧、欢欣、无畏、迷惘、愤怒……统统重现于我们身边。
* * *
传染病从未远离人类。就在一个世纪前,西班牙大流感横扫全球,留下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恐怖的死亡数字。在那之后的一百年里,类似的剧情一次又一次上演。现代医学高歌猛进的史诗吟唱,始终伴随着恐慌、悲伤和忧虑的协奏。人们不曾想到,令人闻风丧胆的鼠疫会降临在自诩“天使之城”的洛杉矶;人们更从未料想,可爱的家养小鹦鹉会带来致命的鹦鹉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军团病、艾滋病、SARS、埃博拉、寨卡……瘟疫在全球四处生根,没有哪个国家敢标榜自己绝对安全。
人类不断地从一次次瘟疫中总结经验教训,开发新的诊疗技术。但正如细菌学家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所言,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尽管有了新的医疗技术以及普及的疫苗和抗生素,但人类“本质上比以前更容易受到伤害”。是人类的学习能力不足吗?是我们的医学家们还不够努力?或者,我们需要跳出思维惯式,重新审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吗?
我们常把对抗传染病喻为一场战役,将病原体视作虎视眈眈的敌人。但比起“对抗”,也许“平衡与失衡”才是更为贴切的隐喻。彻底消灭病原体的理念是难以实现的。我们看到,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在多次瘟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自然状况下,病原体与动物长期共处,已然达成了某种平衡,而人类有意或无意地入侵自然领域,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病原体便跳跃到人类身上——本书关于鼠疫的一章,讲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
除了生物因素之外,社会、文化因素也加剧了传染病的蔓延。首先,全球化使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疫情流行时,我们已无法寄望于躲进某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一隅偏安。其次,文化习俗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疫情的传播,饮食、丧葬、节日习俗等都可能推波助澜。而这正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冲突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具现。在第八章的埃博拉防疫史中我们看到,简单粗暴地取缔习俗可能会适得其反,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时,我们需要谋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此外,在每场瘟疫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恐慌、流言与不信任情绪总是如影随行。瘟疫来袭时,我们总是希望迅速获取准确、全面的信息,但是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却用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种近乎不切实际的期盼。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中,纽约公共卫生官员们担心影响战事,刻意夸大流感对德军的影响,而对美军的疫情轻描淡写。20世纪初洛杉矶鼠疫暴发时,出于对城市形象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市政领导、商业和新闻业巨头压制疫情报道,宣称“绝不会刊登有损城市利益的内容”。
信道可以被管制,但焦虑与恐惧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它们时常为流言蜚语营造出滋生的温床。2003年4月1日,香港正陷于SARS疫情困境中,某家报纸的网站上发布消息,称香港即将被宣布为“疫港”,惊恐万分的人们匆忙将消息转告亲友,四处抢购食品和生活物资。然而,那则消息实际上只是一名14岁男孩的愚人节恶作剧。另一方面,污名化与偏见常与流言相伴,在SARS流行的高峰期,多伦多的唐人街宛似鬼城,食客们都不敢前去消费。艾滋病流行初期,患者群体背负着巨大的道德污名,他们受到排挤,被指责纵欲、犯罪、有药瘾,甚至连因日常输血而被感染的血友病人也未能幸免。
在恐慌中,许多人会寄望于科学。诚然,科学的理性、中立和审慎是抵抗流言的利器,但我们必须谨慎地承认,科学亦有局限。正如书中所展现的:有时科学观察会出现失误,就像在没有认清流感病毒之前,我们一直将细菌视作流感的病原体。有时科学研究又不够迅速,正如当SARS疫情急需特效药和疫苗时,医学界却只能给出隔离建议和支持治疗。艾滋病的科学纷争历史更是向我们昭示,当科学家陷入名利、荣誉之争,经济利益、名誉诉求甚至国家荣耀混杂在一起时,疾病的本相就会陷入重重迷雾之中。
除了前述问题外,在最后一章论述寨卡疫情时,作者还提及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寨卡瘟疫正炽之时,报纸竞相报道,巴西政府和各色组织争先恐后地参与疫情防控,然而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当地政府与大众又一次陶醉在“抗疫胜利”的笙歌之中,仿佛一切问题都已随着疫情一起终结。部分曾经承诺的科研经费没有按时到位,一些原有的康复支持项目也慢慢消失。作者痛心疾呼:虽然寨卡疫情已宣告结束,对它的恐慌也逐渐被时间冲淡,但巴西贫民窟的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本质改善,传播寨卡病毒的蚊虫依然在充塞垃圾的河道中滋生,因寨卡而致畸的婴儿也未得到应有的照护和补偿。若相关社会条件无法得到改善,谁也无法保证寨卡疫情不会卷土重来,谁也无法预料下一场疫情将会侵袭多少国家,将多少原本就已深陷贫困的家庭推向苦难的深渊。事实上,疫情的反复并非没有前例,就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埃博拉疫情于非洲死灰复燃,并于2019年7月17日再度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状态至今仍未解除。
* * *
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为这本书拟定的副标题是“一个世纪的恐慌、歇斯底里和狂妄自大”,将这样三个“负面”的词汇置于文前,乍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妥,但通读全书之后,便可知晓作者绝对不是想要传播恐惧,也没有过度悲观。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一次次瘟疫流行之际,总有严谨、奋进、勇敢、无私的力量汇聚起来,支持人类渡过难关。但威胁持续存在,前路坎坷艰难。在多年前反思SARS疫情时,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院长、国际知名流行病学家罗伊·安德森(Roy Anderson)曾提醒我们,抗疫胜利所带来的自满将是最大的隐患。
我们不该因为人类在某些大瘟疫后幸存,就无视自己曾经的傲慢与纰漏。回首瘟疫史,在纪念人类展现出的智慧、力量与勇气的同时,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些痛苦的离别、牺牲和哀愁。
在本书中,每一章传染病的故事都非常复杂。可是,世界本就如此,它不会因为我们一厢情愿的期待就变得简单。谦虚的科学家会说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谨慎的历史学家会强调了解历史不能预知未来。但面对复杂的传染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不做旁观者,我们可以从历史经验、科学原理和理智辨析中汲取更多,反思更多。希望面临那从未远去的传染病风险时,这些知识与反思能够使我们更加安全,更加理智,更加勇敢,更加友善。
谷晓阳 李曈
首都医科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
医学伦理学与医学史学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