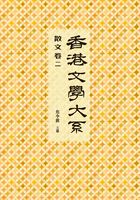
易玲
香港新年雜景
一、花市燈如晝
在一百年之歷史中,雖然是幾經人事,但若果從歷史之一貫行程來回顧,又是何其短而速。我已經留連過香港之若干次除夕與新年,我對於為除夕與新年特有之風光景物,實在尋覓不出與故鄉比較差異之新奇,一年一年運替了,這印象也如夢如烟幻滅。
這真是一個東方的城市,或許遠從大西洋,角城來的鐵蹄會給市城的臉目踏破,然而,在傷疤和淚光血跡之下,在那僻居的角落,正流着亞細亜傳習的神采之江河呵。我流浪到島上的第一個除夕,那印象就是花市,那設在高士打道一角之花市,不,那簡直是砌結於人海上的花市了。
我也無暇去研究人們為甚麼特別愛好花,但如歲晚那特設的高士打花市熱鬧繁雜的情形,委實可以給每一個老於香港的人去回憶。過去香港有一百五十多萬人,如果廿個人之中有一個是那裏的主顧的話,已可以顯見其交易之盛了。不知道從那個年頭起始,政府佔有了花市的支配權,在每年歲晚,大概是我們農曆十二月十五日左右,長長的高士打道被間格成了若干個攤位,做買賣的出高價去投承,最高的達百餘元,最低限度也要三四十元。於是政府平白多了一筆進款,而在三數日之間,高士打道已成為另外一個世界。在二十世紀高峙之洋房脚下,出現了接比的茅舍,這是被稱作柵或棚廠之攤位。攤位的主人多般設計了門面裝飾,用五光十色的電燈或是光亮十足的汽燈,也有特別裝上「八仙賀壽」,「天姬送子」等能夠自動的箱畫,更為打起鑼鼓來。賣花的,有盆裁,有散枝,有生花,有紙花,有蠟花。花的品種,如水仙,吊鐘,桃,梅,茶花,桔,菊,鳳仙……等應有盡有,不下百數十種。做買賣的雖不能算是專門,但大都是慣於經營此種生意的。有遠到福建或廣州灣去選擇名花菓樹,即如吊鐘一類,十之八九是來自本港以外的地方。所以,設一個攤位,每每需要數百元資本,獲利亦以數百計。餘外有賣買古董的,食品的,洋貨的,年紅紙料的,年宵玩具的,樂具的,亦不下二十餘種。普通稱為「賣年貨」或「賣年宵」。最熱鬧的時間多在晚上,特別是除夕一夜,那些紳士淑女們,如遊龍一般的往來道上,連絡不絕。他們或許不盡是為買物而來,是遊玩而來罷,似亦不盡是,大抵年深月久,逛「花市」,趁「年宵」已成為一種習慣,並且被作為體面的舉止了。
而元旦的日中每家特設的「桌圍」,那盆景花瓶,香菓,以及那香烟飄繞銀屏佈置,許多許多名貴而特別染上珠光豔紅的東西,則是多半來自花市上。
如高士打道一樣,但規模較小的花市,在九龍半島油蔴地附近尚有一個,這裏的市民們,真是有點「年宵」熱罷!
二、除夕之話
我們中國人過新年的熱鬧,那高潮不但在元旦,而且在除夕及上元節上湧出。香港是一個萬商雲集的地方,自然減少如「家家紅蠟待春光」一樣的情調,但商場除夕的氣象,也夠我們尋味了。除夕本來是新年前夕,有如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夕一樣,大家都該喜氣滿臉,如準備聖誕禮物一般來佈置元旦景象的。其實,事實並不如此,商場中的除夕,往往就是一個「難關」,或是競爭最後的一日。所謂難關者,原因我國商場老例,一年的債務,多在除夕結算。每逢這一天,商店的老板們真是忙得不可開交,或是煩惱得不成樣的。如果是收賬款的,一日之中他要打上好幾十次電話,或出入幾十次門檻。
「喂!最遲到五點鐘,請你老先生預備,…………」
欠人錢的接到這樣的電話,真是不知如何打算,除了「唔!唔!」的答應下來之外,可沒有別的辦法了。如果籌不出款來,只好深深避居在別的地方。然而,店中和家裏也忙着要辦「年宵」了,孩子們要新衣服,親戚朋友也要打點禮物,伙計們趕着要薪水……,這些都是頭痛的問題,望着時鐘,年紅管快又要燦爛向人笑了,他却過不得年。
除夕又是商店僱員們的難關,俗語說:「半夜定去留,明晨送君別。」這是特為這難關而說的。原來商店下年度僱員們的留任與否,老板多在除夕半夜决定。手指打着算盤,肚子也打着算盤,一年的盈餘計算了,每個僱員也從頭檢討過了,下年新伙伴的名單,早在肚子裏。一到除夕,僱員們便眼巴巴望着天光大白,如果老板只給自己一個月薪水多少「紅利」或「出店」,則「喃嘸阿彌陀佛」,下年度還是伙伴,如果老板特別客氣,除了「紅利」或「出店」之外,尚多送了兩個月薪水,那就嗚呼哀哉了!職業將與除夕一同逝去。所以我說除夕是個難關。誠然,不少人懷着幸福與愉快的心情去度歲,他們從身上,家中或各種事事物物上打算,正如教徒們佈置恭祝聖誕一樣的去佈置一個理想的,充滿珠光豔紅的新年景象,來為自己,及自己的親人,愛人們祝福。但是,在珠光黯紅的背後,確實有着不少人在瑟縮地度着一秒一分的時光,即使是不為難關壓迫的,但最低限度也得張羅一筆度歲的使用,假如是一家大小,更加是六親俱在的,這筆使用實在不少。誠為這一家的主人開一張支銷單罷,起碼有三四十項必要的用途。窮人們每每會咒罵除夕,也有不少人嘆道:「人家過年我過月,」這真是一幅凄凉景况的寫照。
東方式的城市,人們恒年就在這難關中渡來,而又渡去。
除夕尚有兩種令人永不會忘記的特殊現象,雖然這都是屬於商業範圍的,但這正尖銳地表示了人們是如何希望延長剎那的時間,那種向難關掙扎的姿態。
除夕商店夜市,通常在十一時左右便告結束,一年的經營,即止於此。就是高士打道花市,充其量也只是延至十二時而已。但竟有營業通宵達旦,至第二年元旦早晨的,是理髮店和當押店。我國人有一種習慣,就是每逢節日大多數必定剪髮,如五月節端陽,七月節七夕,八月中秋節等。市民們多正正經經到理髮店剪髮,除非是真個窮漢,或在思想與生活上已非純粹中國市民的人是例外。過年當更不在話下,即使是窮漢,或是半西洋化中國市民,似乎也不能例外了。有些因為職務與工作關係,如商店的僱員們,非到除夕十二時後是沒有閒暇的,就算在十二時候,還是要剪髮,所以除夕理髮店特別生意好,而且是一直營業到天明。在街上爆竹聲響的時候,理髮師手上的器械,尚要在黑髮草原上耕耘呢。
這也是我國人過新年習俗之一,這種習俗非常普遍,但從來未見有人十分注意。我曾經檢閱過許多古籍,關於新年的形形相相,差不多也有記述,但却少了這一點。是故我國人剪髮過新年的用意,我不能知道,如我這樣的人,相信亦不會少數。大抵這可以與過節剪髮相齊並論。這種事實在我國的鄉村尤見普遍。據我的推測,或者與我國人之所謂「轉運」有關。節日在中國每稱為小運,年節稱為大運,清人紫陽山人筆記云「閩廣以冬節大於年,冬為四時更始之末,天運之基也。」又見年節是大運。當然人人都希望「今年比去年好的」,過年什麼都新,剪去頭髮,以示脫舊運,亦未嘗不有點意思。所以,理髮一節,不啻為我國人某種心理之反映。而略帶有民族與歷史的色彩也。
至於當押店在除夕營業通宵達旦,則是古已有之,又見於前人筆記中。大抵此是應一般貧苦人家之需求而設,或是起於當押店老板之生意熱。除夕是一年中最後的一夜,過去一年中之事事物物,要在這一夜中結束,未來一年中的事業,亦要在這一夜中有個定算。更是那些窮苦市民,一方面要應付臨門債主,好歹要結算多少舊債,要不然,今後是難望再有交易了。一方面要張羅過年使用,假使一切應酬都免除了,但起碼三四日之糧食及其他食品,新年必備之年紅紙料等,則是不能缺少的。然而,一輩子鬧窮的朋友,去那裏張羅這筆使用?如果有職業的,應有多少薪水收入已經决定了,否則去借債,這個時候人人都不會放債的。結果,就拿着僅有之棉被或大衣去押了,換來幾塊高利貸錢罷。所以,除夕押物的人特別多,當押店的先生往往有應接不暇之勢,而除夕又是人們押物機會最多的時候,當押店的老板多是看清楚這個時間,所以當押店也和理髮店一樣鬧起通宵達旦的營業來了。那些肩頭滿荷着東西,走入當押店的人,出來時雖然是必定兩手空空,但好像也無暇去傷悼這些被囚的東西了,還是匆匆忙忙的加緊了脚步。這一夜或許是以後的夜,便有如落寞的詩人一樣,瑟縮於新歲之嚴寒下做夢了。
除夕夜後一時,黑漆漆的天空下該是空寂的,人們正好去休息一歲之重負與疲勞,但新的熱鬧則接踵而起,那是家家戶戶的爆竹聲,人聲,就在一片鬧哄的聲音中,元旦來到了人間,來到了海島之街市。
三、元旦備忘
這雖然是回憶的情景,但百數十年之後,這種情景恐怕還要為未來的人作一貫的同樣的回憶罷!居在這裏的人,特別是我們的中國人,對於過新年不但要懂禮法,同時也要有「常識」,這兒我想告訴讀者的,是元旦備忘之東西罷。
在元旦與人見面,大家慣說「恭喜多賀」,「生意興隆」,「橫財順利」這類的話,那是必要的,原因大家都希望今年比去年好,而且要好得多多。簡言之是大家說吉利話,即使仇人見面,也多笑臉迎人。
由家裏或商店出門時,許多人要從「吉書」上選擇一個「好時辰」,因為這是一年之始,生怕遇有甚麼相忌之事。即使懶得擇時辰,回家時也一定要到市場逛逛,買些如「生菜」,「生魚」,「猪肉」這類東西,以象徵「生」及「吉利」。而最重要是不能亂購東西,譬如買一雙木屐,買一個木盆或其他木做的器具,有「常識」的人都是不幹的。因為棺是木做的,而死人才購棺。推而論之,買木與購棺有連帶關係。象徵死或不吉利。普通是多買糖菓或紅瓜子之類的東西,取其甜蜜與豔紅之意。
商店廚房伙計,即俗稱之「伙頭」,元旦燒飯有一鐵則,就是寧可燒生飯,但决不可燒焦飯。因為焦飯大多緊貼着鑊底,使人容易想起「起底」。在廣東人看來,「起底」云者,等於商店拆本或甚至「關門大吉」,拉倒之意。但生飯則不然,普通作為象徵「生意興隆」解。
諸如此類的忌諱,盛行於一般市民之習慣中。元旦日我們不妨稱之為「忌諱」之日。因為一行一動,似乎都要考慮和選擇,極力使之與吉利好兆頭接近。
我國人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忙着,從沒有休息。這恐怕是世界所無者。只有元旦例外。大家都閒着,商店關起門來,伙伴可以盡情玩去。這也可以顯見人們是如何盡情快樂,來享受這難得的一天。同時,元旦之飲食都特別豐富,往往擺設了豐富的酒席,大家狂飲大醉而止。
元旦過後第二天,俗稱年初二,又名曰「開年」。而至上元節,其間都是充滿元日新氣節的日子。雖然是平凡不過的日子,但慣於作着樸素及原始之古典情調回憶的我們中國人,將那些日子一一囘味過來,未嘗不可以得到一點苦澀的餘味。
選自一九四三年一月香港《新東亞》第二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