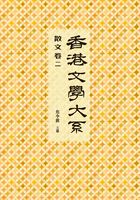
陶惠
去年今日——香港攻略戰身歷記
埋首沙中的鴕鳥
「意外地接到了○○的請帖,他按照西洋規矩在一週前發出請柬。
「晚上和妻到利舞台看『東亞之光』。散場時遇見王醫生,又和他一道再去逛嘉年華會,坐『鱆魚列車』和『飛機』,後者最為刺戟。下次還想試試。
「王醫生說我更『發福』了,他主張再打兩盒賜保命。妻也慫恿我。不過那個牌子似乎太貴了一點。
「回家時看見巴士運兵。○○說今日有十二艘準備撤退用的船突開往星加坡,妻的消息是九龍昨晚戒嚴。寫到這裏我又聽見轟然一聲,極似大炮。
「如果又逃難怎末辦呢?
「今日午睡一小時。」
這是去年十二月七日午夜寫的日記。在寫牠的我今日看來,這日記每個字都是舊香港滅亡的徵兆。我們在當時過着絕對個人主義的生活,沈浸在嬌奢淫逸的享受主義的泥沼中,却譏笑「日本的泥足」,滿足于片面的宣傳,像一個懶惰的魚兒企圖吃不勞而獲的餌而終于被漁者所捕一樣,我們「埋首于沙中」等待「那末一天」……
當我這個「鴕鳥」還埋首於被褥中的時候,隆隆的高射炮聲,混合着嗡嗡的機聲和沈重而巨大的爆炸聲驚醒了我。那是八日上午八時左右的事情——即我看了一部「證明」日軍厭戰的影片以後的第十一小時。
是演習還是打仗?
是演習還是真的打起來了,這個問題,直到我去訪問了一位「日本通」兼國際專家以後,還不曾解决。那位專家和我一樣,也是給炮火驚醒了好夢的:「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接着我打了幾個電話,最後才由一個記者口中知道「這不是演習,這是真的戰爭!」
香港人在當時真如一個美國記者所諷刺的「埋首沙中的鴕鳥」。平民如此,政府當局未嘗不如此。香港在表面上雖然具備着一切現代的防禦,很可以宣傳成「金湯之固」,然而實際上比棉花還軟弱:沒有一個人真正準備用血來作代價的。日機不必轟炸,當牠向香港飛來的瞬間,香港政府的命運便决定了。
紊亂之紊亂
八日早上出外時,我便發現香港政府已失去了牠百年來的統治權。馬路上是一片紊亂之紊亂,一切法規都失去了效力。我等了半點鐘還搭不到巴士或電車。英國人的面孔變色了,背也駝了,對中國人似乎不大用鄙夷的眼光斜視了。警察們既不「警」,也不「察」,他們看着窮人們伐「皇家」的樹木,這是當時香港的一大禁令;看着「爛仔」們搶東西。英國兵士走不到三步路便要攔住一架汽車送他到目的地;我不知這是趕時間還是根本走不動!
防空洞成了許多人的免費宿舍。有的人不但帶了細軟東西,連床、鍋、爐子、馬桶也搬了去,吃、喝、拉、撒、睡一律「防空化」——這就是香港政府訓練民間防空的成績。
商人,不用說,是「乘時而起」了。他們的價錢和日機攻擊的次數成正比例。譬如,一袋五華牌麵粉,昨天是五元,第一次空襲後便變成六元或七元了,而麵粉并不是香港人的常食。而在幾天之後,你尋遍全香港也買不到一袋麵粉。即使有店家肯賣給你,你也未必有足夠的「散紙」。五十元的「小牛」沒有一家商店肯找換,「大牛」更不待言了。
搬與買
苦力們在平時不能算作人類,但在戰時就走運了。因為身邊有一筆遷移費的人,都在尋覓一堆安全的沙,將他的腦袋深深地埋進去。他們從東搬到西,從西搬到東,從中環搬到跑馬地,而當香港政府所有徵發來的汽車停在跑馬場,給日機作了最好的目標以後,跑馬地的寓公們又要借重苦力了。
駝鳥們一面搬,一面——買。糧食自然是大買特買,即非必需的奢侈品也一樣被屯積。太太小姐們不甘落後,和老爺少爺們競爭購買,「荷里活」的化裝品,糖果,特別是「朱古力」。每人只許買一件。好的,他們有辦法:買了一件交給另一個人,再去買一件。動員家中老幼大小,男女僕人,從公司開門起,一直買到「存貨沽清」。真的「沽清」「啦嗎」?非也。「奇貨可居」「啫」。
香港政府,有關方面,一再籲請「合作」:這就是居民對這一呼籲的答覆。沒有一個人能阻止這種紊亂,因為香港是從中國人手中奪去的,英國人在一百年後便償付這筆到期的血債。中國人的不合作,寧說是宿命的。沒有一個主子能從奴隸得到合作——如果那個奴隸曾經自由。曾經自由的人不會重為奴隸。
仇英暗流高漲
這種仇英的暗流表現得最尖銳的是在雙十字旗下「混飯吃」的「華員」,義勇軍,義勇警察,防空員。當一個華人的義勇軍向一架「番鬼老」的汽車作手勢,實行臨時「徵發」的時候,那「番鬼老」像沒看見一般筆直駛了過去。但前面又有一個士兵向「番鬼老」招手了,「老番鬼」立刻停車,因為那個兵士的膚色和他一樣。於是問題來了:那個中國人會用他的性命來保護那個「番鬼老」的性命麼?
即使是阿Q,也要說「不」吧!
每個英國人,甚至每個白種人,只要有一張身分證明書便可以在「香港大酒店」或者「聰明人」吃免費飯。但華人的防空員,義勇警察每天只有一塊錢的伙食津貼。香港政府在召募這班「幹部」的時候,為了防止「第五縱隊」的活動,專選那些殷實商人的子弟,也就是支持香港繁華最力的花花公子。公子哥兒陪英國人喝喝威斯忌是綽綽有餘的,要他們打仗,那就等於擠公牛奶了。
打雲頭的高射炮
我第一次目擊日機空襲是在銅鑼灣避風塘,那是九日上午的事情。距我身旁卅碼的廣場上放着三架高射炮。有幾架日機在九龍那邊盤旋,我和幾十個行人在一個中國人和一個英國人的防空員的命令之下,藏在灣景樓「琴齋書舍」的騎樓下。英國人的面孔原是白中泛紅的,這是變成北歐的貧血病者了。他用一條上等的印度棉紗手巾塞着口,叫我們也照樣實行預防,以免兩耳被爆音震壞。接着,日機三架向我們避難的這邊飛來,從地上看起來,飛機比匯豐銀行大門口的「英國獅」至少小三倍吧,——這就是說飛機的高度顯然在一般高射炮的射程以外,然而我身旁的高射炮却隆隆地響了起來。一團團的黑烟球,在空中浮着,日機在他們上面繼續作水平飛行,沒有一架有過企圖避開防空炮火的動作——這證明英軍的高射炮的性能,特別是炮手的技術——正如那位英國防空員的口頭禪:GOD DAMN!
日機俯衝轟炸
第二次看日機轟炸是在半山上一個友人住宅的屋頂上,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親見俯衝轟炸。兩架日機飛到西南方的雲中。一兩分鐘後一架首先飛出雲外,向東北方駛去,另一架以最大速度向有無線電台和我不知道的軍事設施的昂船洲俯衝,在一個很近的距離投了上十枚炸彈,除了命中該地外,還命中了對面的(九龍)煤油庫,一股濃烟冒出來,接着是大火。
這是十一日的事情。那時炮戰也開始猛烈了。一個開小差回來的義勇警察說,如果九龍明天不失,他不姓○。沒有一個人相信他的話。大家都以為九龍至少可以守到援軍到達時,那情形彷彿是日軍特別留着一條路讓援軍「到達」似的。這是反常識的幻想,也是英國一貫的誇大宣傳和多年的奴化的,寄生性的殖民地教育的反作用!對于日軍,這種心理的形成,正是求之不得的。
英文報的哀鳴
九龍陷落之後,英文南華早報發表了一篇題目「維持治安」(Keeping Order)的社論,一反昔日傲慢的口氣,哀鳴地承認軍事失利,而對于華人的不合作,則拉扯到「爛仔」身上,說香港最可慮的是治安。那個向來不曾為難民請命的英國代言人,現在對勞苦大眾深致同情了,主張加設公共食堂,「窮人們沒有飯吃怎不搶刧」?大主筆說。至於軍事方面,大主筆宣稱只須捱過這末一兩星期,渝軍便會來解圍,而「香港與九龍再度合而為一」。自閱英文報以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英帝國的代言人這末重視中國。同一報紙(包括「電聞」報)在歐戰爆發之初當陳友仁主張重慶參戰的時候,大主筆嗤之以鼻,說重慶那有資格參戰!這個沒有資格的重慶,如今却成了香港政府馨香以禱的救星了!
悲劇的楔子
我的悲劇(如果可以這末說)是從十七日午後開始的,今日想來,這個悲劇是契機于三年來的享樂生活,而以一種愚昧的「聽天安命」主義為其促因。為了清靜,「光猛」,我在中環「混飯吃」,却在北角吃飯——住家。我的一位房客在十一日就搬走了。他曾當過軍官的,對我說夜間燈火管制事實上不必要,因為香港沒有空軍,幾架飛機在開戰的五分鐘便給炸光了,日機白天喜歡炸那裏便炸那裏,不必夜襲。他又說英軍的高射炮的技術比中國至少差十倍,可是他忘記勸他的同胞之一的我早日搬走。我在前面曾非難過那些「搬」「買」家,其實我真應該效法他們。
我的寓所在七姊妹,與電燈公司和煤油庫為隣,而斜對面是一個高射炮陣地。從香港的東區到中區,如不爬山,非從我家門前經過不可。在開戰的頭幾天很安寧,附近沒有中一枚炮彈或炸彈。可是在西環大吃炮彈之後,災難便輪到我們頭上了。十七下午起,炮彈換了方向,開始向銅鑼灣以東飛來。我從鵝頸橋買一袋麵粉囘去,至少有廿個炮彈從我頭上「嗖」過。經過灣景樓時,看見幾個英國兵橫在機關槍旁懶懶地抽着紙烟,狼狽得有如落水狗。戰爭已使兵士們伸不直腰幹,還談甚麼「死守」?我直覺到香港末日的迫近了。
家在火線下
當天傍晚炮聲漸稀,我到騎樓上去看看四周和街面上的情形,發現五百碼外的游泳棚,從華人會到銀行公會完全被大火吞噬了。再掉頭向另一邊看看,天啦,我們的芳鄰——煤油庫——起火了。直到這時我才覺察出我的家是在第一道火線下,如果不想死,得設法逃出火網。然而母親不主張逃,她堅持着她的炮彈有眼睛,菩薩保佑每一個善良的人們的哲學。另一方面,事實上我們已不能安全地逃出火網,由我家到灣仔或跑馬地的馬路或山上的小路,都在火網之內。於是我只好滿足於現在的命運了。第二天即十八號,大炮幾乎完全集中向我們寓所附近猛轟,從早上到下午,平均每兩分鐘必有一發,我們整天躲在樓梯下。「通——嗖——拍——或者——通掛」,「通」是九龍那邊開炮,「嗖」是炮彈破空而過的聲音,「拍」是擊中了山,「通掛」則是殃及一個住宅。每「通掛」一次。我們身旁的牆壁便像三夾板被人靠着似的那末向後彈去,(感謝鋼骨水泥!)於是石灰與玻璃碎片齊飛,而妻和兩個兒子嚇得半天合不攏嘴來。
老人家的勇敢
但母親却不怕「拍」或「通掛」。她堅執着與寓所共存亡,怎末也不肯到樓梯下躲躲。她老人家趺坐在蒲團上,念金剛經。我雖不像妻兒那樣嚇得毫無人形,每聞「嗖」的一聲之時,却也全身緊張得窒息。勇敢的是母親,六十三歲的母親。和她老人家一樣勇敢的是我們的一個本家嬸母,她幫我們作飯的。在每兩分鐘必有一炮的密集的猛轟中,她照例有條不紊地烹調食物,連鹹淡都不弄錯!
但我終於將這兩位老勇士硬拉到樓下去了。這是一幕人類的戲劇。我沒有法子說服她們,我用了最後一着:拚。我宣稱如果她們不下去,我也不下去。這一來,兩位老人家只好妥協。
廚房打了一個大洞
就在她們避入樓下的時候,一顆炮彈命中了廚房,從廚房牆壁一直打到浴室。這是偶然還是天定?刧後餘生的我,在某一意義上,寧相信是後者。我至今還不信真有神這個存在。但相信「信仰可以產生力量」這句名言。人在危急時鎮靜或恐慌,勇敢或懦怯,和個人平時的安靜與反省工夫大有關係。安靜帶來反省,反省產生信仰,而信仰在生死關頭便是鎮靜的代名詞了。兩位老人家都是信佛的,在喃喃的誦經聲中,心神得以專注,不致為外物所動。比這更重要的是她們心目中都有一個幸福的西方極樂世界:死。
我沒有這種信仰,反之,一些知識却增加了我的畏懼。武器的威力我比兩位老人家更明白,因之,飛機的急降聲或炮彈的嗖嗖聲對我便有如喪鐘了。妻是信上帝的,但她信上帝的緣故,我想,一半是為了在禮拜堂展覽她的新裝吧。(上帝在上,希望祂不要看到這篇東西!)所以她在開戰第一天便「面無人色」了。兩個兒子尚不解人事,糊糊塗塗,逍遙自在。大兒子有一次將警報聲模倣得十分到家,竟使他的母親嚇得半天才緩過氣來!
登陸了!
大約在夜間八九點鐘的時候,連珠般的炮聲漸稀,機關槍聲大作。不知怎的,我頗喜歡機關槍的「拍拍拍」之聲。如果大炮聲如獅吼之可畏——或者如河東獅吼,機關槍聲該是琵琶的美妙的樂音了。從九龍「撤退」以後,入夜便聞斷續的機槍聲。今天晚上,却響個不停。而在一陣緊密的「拍拍拍」之後,我聽見雜沓的步伐聲,繞過我們屋後通電燈公司的一條路。機槍聲越來越密。登陸了?這個觀念閃電般地浮上腦海。幾分鐘後,我們聽見吆喝聲,喊叫聲。許多年來沒有聽那包含着極多的爆發音的日本男性的日語了,但終於聽出了一個甚麼「トツタカ」,但我還不確實。妻嚇得索索發抖,我全身緊張得像扭緊的鏈條。兩位老人家緊抱着她們的孫兒合十念佛。
英軍之釜底遊魂
槍聲停了,四週靜寂得可以聽出自己的呼吸。一會,遠遠的起了一陣嗡嗡聲,像飛機那末地低沉而固執地嗡着。我們常常會將汽車引擎的爆發音誤會成飛機聲,電車頂上的「電棒」與電線的摩擦音誤會成炮彈破空而過的嗖嗖聲。這次又是一個照例的誤會。但,就在我們聽出來那是汽車時的瞬間,一陣緊促的步槍聲,突然發出,當中還夾雜着幾聲大的爆炸聲,火光從騎樓門縫射了進來,汽車立刻戞的一聲停止,接着又是萬籟俱寂。
這不是登陸是甚麼?我試開封閉在防空燈罩中的電燈,沒有了。試開水管,沒有了。這時又來了一輛汽車,在另一陣劈拍蓬中,遭受了同樣的命運。我這時已有充分理由斷定日軍不但登陸,而且完全控制了我家門前的這個東西交通的要道。汽車是從西邊開來的,沒有任何抵抗,可見車中乘者不多,從此也可推出英軍還不知道登陸成功。英軍草包到這樣的田地,在世界戰史上恐怕尋不出前例來吧!
太像中國軍
同一戲劇重演了四五次之多。接着天也發白了,我從門縫中窺見日軍在對面山腰上佈置小銅砲。兩三個人便抬了一架,很敏捷地在山上奔跑着。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日本陸軍。日軍給我的最初的印象是太像中國軍隊。火野葦平氏在他的作品中說中日軍隊在同一條路上走着,竟分不出敵我來。我當時看見這段記述還以為是「白髮三千丈」一類的「文學筆調」,現在終於由我自己的眼睛證明了。
但當時我最迫切的問題倒不是證明K=Y,而是决定如何應付這一個未知數。從八日到現在,十一天來忍受種種痛苦都是為了苟全性命于戰時,現在如果還不肯死去,當然要繼續這一努力。我應該老實說我還不想離開這人間世,這既不是因為妻兒太可愛,也不是因為人間有甚麼特別值得留戀的東西,而是因為我被一種強烈的本能或尼采稱為「生之意志」的東西驅策着。
如何面對現實
於是全家以我為中心開始討論,我應該如何面對這一個現實。母親廣徵鄰人的意見。其中有的主張我化妝成「做粗事的人」,有的堅持我應該藏在廁所裏,有的說我最好是權充和尚,因為日本人也是信佛的。但另一個立刻反對他的意見,說我頭頂上既無和尚的表記,而光頭大有被誤認為遊擊隊的可能。總之,議論是紛紛得像每一個委員會議一樣。
但我拒絕了一切建議,甚至連西裝也不肯換成長袍。這并不是母親的固執在我血液裏起了作用,而是因為我認為任何統治者都需要與土地同樣重要的人民。我深信像我這樣的人民該是一切統治者所企圖獲得的吧。我永遠不會斫公共的樹,永遠不會從一個等候輪流的行列的後面擠到前面,永遠不占據兩個座位,沒有任何嗜好——除了抽抽香烟外,永遠照付一切帳單。我想,我似的公民,不但不應受到日軍的歧視,還應該得一個獎狀吧。所以,我决定用本來的我在這個突然作一百八十度轉變的新環境中生存下去。
英武的日憲兵
一陣皮靴沉重的步伐聲從樓下上來了。來了!妻飛機一般的衝到廚房去。接着是所有在坐的人。二兒子首先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大兒子擰了他一把,叫他「勇敢一點」〔。〕「Open Door」,外面的人喊了。我遲疑着,難道是一個開小差的英國的勇士?這未想着。一個鄰人,即主張我應該暫時做做和尚的,生怕我開了門,死死拉住我。但敲門聲更急,門在搖晃了。我突然挺直了腰幹,像傳奇中的那些英雄一樣,大踏步走去開門。
一個至少比我高三寸的偉男子全副武裝地站在門前,右子握着一桿駁殼槍、右臂上挽着一個「憲」字的臂章。左邊是一把長劍,飯碗大的一個拳頭握着劍柄。不是英國的儒夫:這是和我同文同種的日本的勇士。
他進到屋內來環視了一下,用廣東話命令道:「統統落去」!然後一個向後轉到對面鄰家去了。
我們遵命「落去」。我一人當先,後面是這一棟房子所有的住客。從匍匐在地上準備射擊的機關槍兵的足旁,我們被領進一個印刷場的裝釘部。
戲劇化的瞬間
再怎樣呢?不知道。X還是K。一些女人們在家家私議着。門外突然發出一排機槍聲。雖然那聲音還是有點像白居易描寫的琵琶聲,但我已無心賞鑑了。我堅握着啜泣的妻的手說:「如果我死了,你改嫁吧!」但我又要求她許諾我當命運臨到她身上時,她應該以一死保持她的人格。母親和嬸母流着淚禱告,祈求慈悲菩薩搭救芸芸眾生。我也流了一兩滴淚,但硬將其餘的淚忍住了。兩個兒子哭成淚人兒一般。
時間慢得像蝸牛,天已黑得對面不見人了。我想,現在該是判决我們的命運的時候了吧。那末,我是束手以待斃呢,還是設法逃出去?在這種場合,每個人都會想到後者的。對面彷彿有一條出路,我裝着小便去看了一下。牆大約比我的身長高一倍,上面有鐵絲刺,那是為了防小偷的,然而如今却成了我這個善良公民的墓標了。我怕我在未逃出之前便會給刺傷,而傷比死更難受!最糟的是牆外如果有一位哨兵,那末,我即使有善良公民的證明書也將百口莫辯了。比這些都重要的是,這一切只是一個猜測,我與其憑着臆斷來冒險,不如靜候命運的宣判吧。這一考慮使我重新躺在水門汀上,而且因為我已經有了死的决心,滿弦般的神經立刻鬆弛下來,所以一會便睡熟了。
感謝日本武士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我的一個麼凡陀游水表已經失去了,突然發出的一陣呼喊聲使我驚醒過來,看見房子的一端,滿堆着紙張的部分,熊熊火光閃着。火,火,火!大家發狂般地喊着。我為首領着家人衝出屋外,向銅鑼灣那邊逃去。在煤油庫餘火的照明下,踏着屍首,炮彈破片,折斷了的電線,躓躓跌跌的,奔向前去,前去到那裏,誰也沒想到。母親是小腳,真辛苦了她老人家。
當我們跑到避風塘附近的時候,一個日軍命我們站住,經過了照例的檢查,用電筒領我們到四樓的一間房子裏避難。感謝這位日本武士,如果不是他攔住了我們,我也許已經和我的家人去了「極樂世界」吧!因為前面就是第一線,而在漆黑的夜間被誤會打死,真是平凡得像踏死一隻螞蟻一般。
「一大樓」至少有五十個人避難。主人似乎是一個混血兒。我向他問我們的命運,他也不知道。他說日軍叫開他的門,領了許多難民進來,這就是事件的始末。繼我們而來的還有幾個婦孺。這時候鐘指着一點,我又安靜地睡了一覺。更正確地說,恐怕是耐力不及六十三歲的母親吧。
天剛發亮時,一個穿短衣裳的中國人上來向我們說他懂得日本話,我們願意走的跟他一道去。他只再三說他懂得日本話。誰叫他來的,他也沒有說。去甚麼地方他沒有說。有些人不願意走,但我和家人和十來個其他的難民接受了他的建議。到大門口,他向我們這一行人說,銅鑼灣那一方面不能去,北角這一邊却可以去得的。這位翻譯先生的「傳話」工夫並不高明,我們這些聽者直到這時才明白他的意思是叫我們逃生,而不是叫我送死,一顆心才放了下來。我想,中日交涉如果不經「翻譯」之手,事實也許不會有吧!
侵略者的償還血債
我們决定就近去○○街,一個友人那裏避難。到了電氣道我才敢向四周張望一下。一眼看見九龍天空上懸着一個汽球,繫着一面幡幟,上面寫着日軍佔領香港的字樣。走到清風街口,看見一個白髮的老英國人死在一架嶄新的摩利斯小轎車的車門上,一隻腳擱在地上,頭斜靠着半開的車門。雖然英國是中華民族的一個老敵人,但我對這位儀表不凡的老紳士却生了憐憫之情。他的服裝說明他是一個防空員,該是一個甚麼公司的大班,一個英帝國最好的公民吧。他的祖先曾將同一命運安排在中國人的身上,現在,由中國人同種的日本人索還血債了。這個死者沒有功罪,他只是償付先人的血債而已……
接着又看見了幾個英國兵士和無辜的印度兵士的屍身。煤油庫還在燃燒,我們住的那一排房屋還在燃燒。這是意料中的,所以雖眼看着火焰從自己的廚房的彈洞中吐出來,并不傷心。只是默念着完了,一切都完了,這一句話而已。……
火線上叉麻將
到了○○街,看見樂天的同胞們在街上口講指劃的情形,聽到劈劈拍拍的牌聲,我真不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戰爭并不曾影響這個老民族絲毫。我不知這是超人的能耐還是——壓根兒神經麻木。這裏不是沒有受到損害,一家商店的後牆給打了一個大洞。附近是一個堡壘,流彈是不免的。然而這條街的人們能夠在火藥與血腥氣中打八圈!
我應該說我懷着一種近乎憤怒的感情走進了友家。這是友人的家啊,不是我的家,我已沒有家了!我已失去了卅五年來「念茲在茲」,不借全力以支持之的家了!
雖然朋友再三嘆惜我的損失,我亟于要到手的是一頓早餐。已經有一天一夜沒吃東西了。在死亡線上掙扎着生存的慾望控制了一切,一點也不覺得饑餓,甚至連最小的香生也不叫餓。現在,一經置身于離死亡較遠的地方,饑腸便如大炮般怒吼起來。
英美色情文化的俘虜
我一氣吃了四大碗,還想吃,但母親和妻向我遞眼色了。大兒子不弱于我:五小碗。沒有我愛吃的炒腰花,沒有我太太下廚弄的油爆蝦;只是一碟腐乳,一碗山水弄的醬油「神仙湯」而已。如果戰爭給了我許多壞處,牠至少給了一個好處,使我得到一個反省的機會,而從這一反省中我發現自己全是英美色情文化的俘虜,和所謂物質文明的奴隸。
我一向是非彈簧床不睡的。但在十九日夜睡了半夜水門汀,半夜地板之後,今晚躺在板床上,雖然給擠得沒有動彈身體的餘地,却有登天之感了。阿拉伯的一個古詩人說人類的天堂之一是躺在女人胸脯上,不,人類的唯一天堂是在死中得生之後躺在板床一角,一面餵臭蟲一面酣睡:像我現在這樣。
第二天在牌聲中過去,雖然間或也聽到彈丸的爆音,在這一天曾和日軍接觸過幾次,那又是一個永不能磨滅的記憶,但應該在另一篇文章寫出來,因為這篇東西已經給拉得很長了。第三天,我們聽見說我們住的那排房子并未完全燒光,只有一棟房子遭遇了囘祿的命運。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我想馬上去看看,然而這一天起炮聲又密了,且有英軍打來的流彈。但這個家完好無恙的消息的確是一個不能忍耐的誘惑,我們一家老少六口終于總動員。
黃種人第一次看到的奇蹟
我穿着一件借來的棉袍子(這時我已被迫同意穿長袍了),于思滿面,駝着背一顛一拐的走着。妻臉上是媒烟子,頭髮(那原是她從電影上學來的Up-and-Down型!)散披着,我看見却有東施之感。兩個孩子一面走一面捉身上的臭蟲——香港的僅次于「爛仔」與鼠的名產。路上很多彈穴,柏油路面從油光變成了灰暗,到處是彈丸的破片,火藥與血腥氣。迎面來了一個行列,兩個日軍領着一大羣吃得飽飽的,甚至還將面孔剃得光光的英國人。最後是兩個日軍殿隊。這是一個我們黃種人第一次看到的奇蹟。我的背脊骨立刻挺直了一點,雖然我神經過敏地恐懼着這當中會有一個我以前跟他做個小書記的大班,而他向我「哈囉」一聲時所可能引起的誤會。
我家門口躺着兩個英國兵或印度兵的被燒得只剩腦袋殼的骸骨,旁邊不遠還有幾具完全的屍首。在母親和嬸母的「阿彌陀佛」聲中,我們跨過了牠們,一腳踏上了有血跡的石階,便彷彿進了唐僧被妖精蒸食時的那個蒸籠了。熱得真難受,但家太可愛,我們怎末也得去看看我們的家。
小鷄與大炮
果如那報信人說的,全家完好如故。門像我們走時那末開着,兩個小鷄子還在咕咕地叫。騎樓的一個門給燒倒了,但牠後面的書架却沒有着火,母親說這是她的菩薩威靈顯聖。糟糕的是房子熱得像蒸籠,又時有流彈光顧,我們顯然不能冒險來住。於是决定搬一點食物,再去叨擾友人。我們雖有六個人,十二隻手,但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做做小苦力,拿這末二三十斤東西。在平時,一個「小牛」,可以雇幾十個廉價的苦力,現在時過景遷,苦力們都準備做富翁了,我們只好向那藏在內衣領邊的「小牛」嘆氣。妻和我用出吃奶氣力算是搬了半袋麵粉,二十斤米,孩子們替我拿「文明的食糧」——香烟,茶葉,火柴。母親捧了她的菩薩,嬸姆抱了她的經書,一行六人在歡送一般的炮聲中凱旋○○街。走了一半路的時候,妻忽然記起小鷄子已經有好幾天沒吃飯了,得回去餵餵。我怕背一個殘忍的惡名,不敢駁他。但——謝謝上帝或菩薩,就在這時候,一顆炮彈在我們身後不遠的地方爆炸,每個人都幾乎跌壞了手中的東西,小鷄子的存亡問題不復為太太關心了。
現實的教訓
現在,我們有了家,有了食,我可以吃第五大碗,二兒可以吃第六小碗了。然而,這只是這末說說而已。第二天,在暴力下便失去隨身所有的東西。第三天再回去時,發現家中雜物除書報和笨重的傢具外,掃數被刧,我們安慰自己道:「當牠是燒掉的吧。」這雖是阿Q的論理學,却也是人在無可奈何時聊以自慰的唯一良法。
我的家,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真令人興四大皆空,甚至空亦為空之感。但我并不打算遁入空門,相反的,我要更深入到人世裏邊。給我最大的鼓勵的是日軍。我羨慕那小小的石子怎樣在短短的時間長成巨大的岩石;我羨慕那結實的身體,那寬肩膀,那粗胳膊,那黑黑的方面孔。他們每個人不是都和我一樣有着一個美滿的家嗎?為甚麼他們能捨棄一己的安樂,獻身于事業?我和他們是一樣的圓頂方踵的人,我為甚麼不能效法他們?
從迷夢中覺醒
一月廿八日我回到那個殘破的家,寫了下面這樣的日記:
「現在我又坐在我的寫字台前了,雖然所有抽屜都給人家拿去。從八日到今天,特別是從十九日到今天,我的遭遇真是像章囘小說上描寫的『公子落難』似的,缺乏的是俠客……
「三年來慘淡經營的事業和家庭,瞬間燬于砲火中。但我并不灰心。我已預見到這個巨變的終極,將是真正幸福的開始,如果我能像躺在對面的那位日本戰士那末勇敢。
「橫在前面的是兩條路。一條是從反省中獲得信念與决心,從克己中獲得自我訓練,以敢死隊的精神和惡勢力作最後的决鬥,這條路看來是很長,很苦,但他的終點却是失去的樂園。
「另一條路是繼續英美個人主義的享樂生活。這似乎是一個幸福捷徑,然而終局却是入地獄。
「勇敢的,遠見的毅然走那條遼遠而崎嶇,但最後證明是一條生路的路。他們盡了他們的義務,却也得了他們的權利。懦弱的或短視的走那條似乎安樂其實是死路的路,得到暫時的神經末梢的滿足,却失去了他的一切所有。
「只有這兩條路。這之間沒有中庸,沒有妥協。
「你走那一條路?」
選自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香港《新東亞》第一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