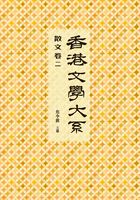
葉靈鳳
吞旃隨筆
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屈原:九歌
伽利略的精神
凡是涉獵過藝術史的人,大約都知道義大利著名的比薩斜塔,那傾斜着突出在地面上的白帽蛋糕型的建築物,至今還不曾倒;可是很少人會知道,就在這斜傾的塔上,從一百八十尺的高處,伽利略曾經將一些重量不同的球體,同時拋下來,同時落地,證實了他的落體定律學說,打破當時物體下落的速度和牠的重量成正比例的謬見,使得一旁目睹的腐儒駭得呆了。這是中世紀科學史上的佳話。
具有這樣震駭世俗的大胆實驗精神的伽利略,晚年為了堅持他的地球運動主張而被捕下獄,正是意想中的事。據說直到今天,羅馬城裏還保存着伽利略被禁的那間屋子,釘着一塊紀念牌,寫着
「一六三三年,伽利略主張地球繞日而行被禁處」
一六三三年,羅馬正是「宗教裁判」的世界,凡是不合教會口味的東西,都要被目為異端,伽利略在這樣黑暗的勢力下,公然擁護哥白尼天文學上的新學說,肯定太陽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的行星一面自己旋轉,一面繞日而行。這學說不僅推翻了當時教會所主張的地球為宇宙不動的中心論,同時更不啻取消了在這宇宙中心的地球上,代表着神而統治人類的教會的地位,這當然使得教會無法容忍了,於是伽利略被教皇召赴羅馬,宗教裁判所開始審問伽利略的異端邪說。起先還僅是作學理上的辯難,後來就老實不客氣的用刑訊來威脅了。也許伽利略這時年紀已經太老了吧,據歷史家的記載,跪在十個紅衣主教的面前,伽利略終於被迫推翻自己的學說,撤消地球一面自轉一面繞日而行的理論,承認地球並非繞日而行,而且是不動的,可是當他自己打完自己的嘴巴,站起身來之後,却自言自語悄悄的說:
「我雖然取消了我的主張,然而地球仍是動的。」
這末後的兩句話也許是好事家的附會,可是在當時被「宗教裁判」所認為異端邪說的「天體運行論」,到了一八三五年,教會終於不得不加以承認,而從梵諦崗的禁書目錄中將牠撤消了。於是伽利略一度被辱的地方,便永遠留着一個人類愚昧的記號。
勝利的到底是知識和真理。
火綫下的「火綫下」
對於日本軍隊進攻香港的戰略,我不知道當時英軍參謀部的判斷怎樣,至於作為一個市民的我,對於日軍的攻擊方式,可說完全估計錯誤了。根據我們的推測,日軍進攻香港的重心,大多數將在西面,如果不從鴨巴甸洲着手,至少將在堅尼地城海傍一演「敵前上陸」的拿手好戲,而對於摩星嶺要塞區的爆擊,必然是猛烈的,因此全港的最安全區,該是跑馬地一帶,因為即使戰事發展到市街戰的階段也罷,等到越過中環區而進展到灣仔區時,無論如何也該成為尾聲了。根據這樣的「預測」,住在西區的我,當香港戰事爆發後,正如大多數的西區居民一樣,立即倉皇從西區避難到東區。那知戰事的演進恰和我們的預料相反,當時在跑馬地防空洞裏所領受的十幾日的交織砲火的滋味,那進退不得的狼狽的情形,現在想起來,誰都要啞然失笑吧。
遺棄在西區的家,當砲火停止以後,萬里長征似的從跑馬地步行着回來一看,叨天之幸,房屋並沒有中砲彈,物質上似乎並沒有甚麼損失,可是仔細一檢點,作為文人的我,所蒙受的意外損失可有點驚人了。
由於鄰人的好意,我的架上的書籍,「抗戰大事記」也罷,邱吉爾的言論集「汗血眼淚」也罷,凡是有點那個的,都不翼而飛了。而打開抽斗一看,從朋友往來的信件,以至個人的名片,未寫完的原稿,總之,凡是有字的東西,幾乎全都不見了。整理完竣的「讀書隨筆」原稿不見了,擱置了五年未能付印旳創作集「紫丁香」不見了,更使我吃驚的是,花了一年心血才譯了一半的巴比塞的「火綫下」的原稿,每一個抽斗都找遍,也杳無影蹤了。
那裏去了呢?鄰人笑嘻嘻的說,說是恐怕有人來查問時有點那個,有些給我燒了,有些來不及燒的都扔在後邊山溝裏了。
想到開始翻譯「火綫下」時曾向書局預支過五百元法幣的稿費,後來法幣和港幣的匯率愈差愈遠,便提不〔起〕精神動筆,老闆屢次來信催稿,始終是懶懶的應着,現在率性連既成的這一半原稿也燒掉了,萬一將來有機會再見到那位書店老闆時,也許那時像「中日事變」之類這麼重大的問題早已獲得圓滿和平的解决了,而我這問題却反而不容易解决;一想到這情形,我不覺暫時忘去了眼前的一切,對着窗外覆着長長的野草的山溝,茫然起來了。
完璧的藏書票
鄰人的好意,雖然使我在這次戰爭中喪失了全部存稿和好些書籍,可是由於他這同樣的獨到的眼光,我的另一份「財產」却幸運的被保存了。這便是我所收藏的現代日本愛書家的藏書票。
據他的解釋,最能動人情感的莫過於「他鄉遇故知」,因此,對於征塵滿面的士兵們,如果有一點東西能打動他們的鄉情,最容易被他們所珍視,因此也最容易獲得他們的好感,而由於這樣的好感所產生的方便,决非在門口貼上一張「特殊家屋,立入嚴禁」之類的玩意所可比擬的。根據這樣的理由,我的鄰人善意的將我的一些原稿和書籍肅清之後,便鄭重的將我所收藏的這一份日本藏書票放在桌上,而且放在最觸目的地方,好像希望凡是走進這屋子裏來的人第一眼就見到似的。
說起這一份藏書票,歷史已相當悠久了。「一二八事變」後不久,我隻身寄住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家公寓裏,每日浸在書堆中,開始對於書籍的版本,裝幀,插畫,收藏各方面,任情的涉獵起來。偶然從中國藏書家的收藏鈐記研究到西洋藏書家所用的貼在書上的「藏書票」,不覺立時着了迷。可是關於藏書票的研究資料,中國方面固然絕對的沒有,就是西洋方面也很稀少而不易獲得,因為這是「書的樂園」的最後的三昧境,不是一般將讀書當作消閒或視作畏途的人所能理解的。後來偶然在內山書店的書架上,讀到齋藤昌三氏所編纂的內田魯庵隨筆集「紙魚繁昌記」,知道藏書票在日本已相當的流行,而且齋藤昌三先生恰是日本藏書票界的權威,著有僅有的研究藏書票的專著「藏書票之話」。
這一發現使得我很興奮,我立即托書店老闆內山完造氏寫信向日本去定購,隔了不久,回信來說這書早絕版了,祇有偶然遇着機會還可以在舊書店裏得到。這答覆當然使我很失望,可是還不是絕望,憑着愛書的熱忱,我當時就寫了一封信給這書的著者齋藤昌三先生,他那時正是「書物展望」的編輯人,詢問他可否為我這異國的書物愛好者設法,找一冊這部書,並再供給我一點關於日本方面的藏書票資料。我在信內還附寄了一張我自己所用的藏書票,證明我確實是一個有同嗜之雅的人。果然,齋藤先生接了信很高興,隨即將他自己所存的一部「藏書票之話」贈給了我,並且還寄來了一批日本藏書家所用的藏書票,以及日本藏書票的研究資料,這其中包括了大正十五年八月出版的「柳屋」第二十九號「藏書票之卷」,大正十四年第四卷第七號的朝日畫報「日本藏票會作品」圖片,以及博多明治製菓賣店所舉行的第二回藏書票展覽會的出品目錄。這些資料都是十分珍貴而且稀覯的,大大的增加了我研究和收集藏書票的興趣,正如後來齋藤先生在「書物展望」某期上所說,「中華民國上海的葉靈鳳氏,正在藏書票熱中」。由於齋藤先生這樣的鼓勵,我隨即加入了日本藏書票協會,認識了該會主持人小塚省治氏,並開始和日本的愛書家和藏書票蒐集家交換藏品。我現在還記得,遠在台灣的蒐集家緒方吾一郎氏,大連的須知善一氏,當時都不遠千里寄了藏品來交換。
由於衣食的奔波和人事的變遷,十年以來生活上雖然不再有餘裕可以供我享受恬靜的「書齋趣味」,可是我愛書的熱忱始終未替,而且不時還藉着偶然的機會為我這一份藏品增加一點資料。同時,由於我個人幾次的介紹,中國讀書界也多少知道了一點「藏書票」是甚麼東西,而且居然還有一二位同好的愛書家製一張貼在自己的書上。
紙魚蝕紙裝的「紙魚繁昌記」已經在廣州戰火中失去,「藏書票之話」則和我的其他藏書堆集在上海已經六年,也不知道情形怎樣。在這次香港戰爭中,我以為帶在身邊的這一份中國僅有的藏書票收藏怕也難免失散了,然而竟能倖免,這使我在安慰感激之餘,不得不佩欽我的那位鄰人獨具眼光,火下留情了。
多年不曾和齋藤先生通過消息,不知他近況怎樣,「書物展望」這樣的刊物不知在戰時還能繼續出版否。目前的香港還未進入「讀書的季節」,也許等到秋高氣爽,燈火可親之時,有機會將這一份歷刧倖存的藏品,整理一下,舉行一次小小的展覽會,作為一個紀念罷。
七月二十日
選自一九四二年八月香港《新東亞》創刊號
秋鐙夜讀抄
「今年的七月,甚麼地方都沒有去旅行,就在這巷中,浸在深的秋的空氣裏。」
「這也是十月底的事。曾在一處和朋友們聚會,談了一天閒天。從這樓上的紙窗的開處,在凌亂的建築物的屋頂和近處的樹木的枝梢的那邊,看見一株屹立在沉靜的街市空中的銀杏。我坐着看那葉片早經落盡了的,大的掃帚似的暗黑的榦子和枝子的全體,都逐漸包進暮色裏去。一天深似一天的秋天,在身上深切地感到了。居家的時候,也偶或在窒人呼吸似的靜的空氣裏,度過了黃昏。當這些時,家的裏面,外邊,一點起燈火來,總令人彷彿覺有住在小巷子中間一樣的心地。」
讀着魯迅所譯的島崎藤村的這段散文,不知怎麼樣,覺得簡直就像自己心裏所要想寫的似的,就信筆抄了下來。是的,「今年的七月,甚麼地方都沒有去旅行,就在這巷中,浸在深的秋的空氣裏」,回想起初夏時曾經决意要利用這近年難得有的閑暇,多讀幾部許久想讀而沒有時間和心情去讀的書,現在對着山背後湧上來的日漸明淨的白雲,聽着山溝裏愈加清脆的水聲,知道秋天已到,這計劃又成空了。
夏天讀書的計劃既不曾實現,對着這「沉靜得窒人呼吸」的秋天,我又燃起更大的雄心了。許多年不曾寫小說了,利用今年這秋天寫幾篇小說罷。我曾經在宋皇臺下住過一些時候,就將那幾位南渡君臣悲壯凄涼的末日,試寫一篇歷史小說罷。
從友人處借來了宋史,厓山集,以及關於文天祥,陸秀夫等人的資料,在燈下檢着有關的一切,從本紀以至列傳,任情的涉獵着。
這也許就是「英美思想應該從東亞驅逐出去」的原因之一罷,近幾年來,我對於西洋現代文學,古典作家,藝術史,翻閱得比甚麼都熟悉,架上僅有的幾冊線裝書,不僅沒有去動過,而且早給逐漸添置的西洋文化史,藝術史之類,擠到書架背後去了。現在翻閱着為了寫小說而搜集來的南宋末年史料,一種久已疏遠的似曾相識的情緒又甦醒了。我於是放任着自己眼和手,將一些線裝書都搬了出來,從正史讀到野史,從散文讀到韻文,每晚在燈下,將闊別了許久的舊時愛讀的許多作品,重行盡情地溫讀了一遍。
小說當然不曾寫成,可是却乘便讀了不少書,「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這種意外的收穫,我不能不歸功於眼前這時代所給與我的啓示。
十幾年前,讀詩詞,愛讀的是唐五代詞。李後主的「憶江南」和「浪淘沙」,韋莊的「當時年少春衫薄,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差不多開卷必讀。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心情真有點使人臉紅。現在念着「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雖覺得這仍然是一首絕妙好詞,可是像舊時那種為詞裏的意境所顛倒的心情,却怎麼也喚不起了。
在燈下展開稼軒詞。這位南宋詞人,正是我近年愛好的作家之一。在這半山區,斗室孤燈,玩味着他的蒼涼的詞意,真使人的心上感到份外沉重: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闌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休說鱸魚堪膾,儘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
還有他的另一闋「水龍吟」:
「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人言此地,夜深長見斗牛光焰。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闌却怕風雷怒,魚龍慘。 峽束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歛。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繫斜陽纜?」
這後一首,去年春天,曾拗不過一位好事者的糾纏,拿了一張斗方宣紙要我寫字,便歪歪斜斜抄了給他了。
同樣的,在詩的方面,二十歲以前只曉得讀王次回的「疑雨集」。(這次日本畫家山口蓬春氏過港時,曾特地托人領路買了一部石印的「疑雨集」帶回去)後來慢慢的知道領略李義山,黃仲則,龔定盦了。近年則一直愛讀陸放翁,尤其是他的「臨安春雨初霽」:
「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駐京華;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短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試分茶;素衣莫起風塵僕,猶及清明可到家。」
老杜和李太白,則始終不曾好好的讀過。對於他們的領略,也許要留待中年以後了。
○ ○ ○
離騷誠不愧為百世辭章之祖,正如大自然,在任何時間,用任何心情去看,都有一種前所未見的新的發現。劉勰評得好:「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細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不讀離騷,怎麼也談不上讀過中國文學作品。
我久有一個心願。作為作家,應該為屈原寫一部可讀的同情的文學體裁的傳記(不是飣餖考據式的)。作為出版家,應該將離騷根據最完善的底本,配上蕭尺木的插畫,印一種字大悅目,可讀可藏的現代版。
又是心願,許下的心願真是太多了。夜將深,我於是攤開擱在手旁的楚辭!
「思美人兮, 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鬱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愧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憑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
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鬱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愧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憑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
一陣山風,着帶一隻青蚱蜢從窗口撲了進來,我嚇了一跳,攤開的楚辭也被吹翻了幾頁: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去年冬天,曾在一個學校裏授離騷,差不多就講到這附近,戰爭便發生了。
○ ○ ○
重要的南宋史料,可以補正史之不足者,有「填海錄」,「二王本末」,「南渡錄」,「平宋錄」等。後兩種,我手邊有神州國光社編印的「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本,翻了一遍,所記的大都是臨安失陷前後三宮北狩的事,與我所要參考的二王末年事蹟無關。最適合的該是「二王本末」和「填海錄」,其中一定可以找到一些厓山小朝庭和秀夫沉海的資料,可惜怎樣也找不到這兩種書。
我佛山人的「痛史」,作於清末,也是以南宋末年的故事為題材,反映當時瀰漫着的種族革命思想而寫的章囘小說。雖是經過渲染舖張,再用來作為寫小說的參考未免不甚可靠。可是其中有許多地方,針對着當時清朝末年的時政,倒也寫得很痛快淋漓,如寫元朝的太監們對被虜的南宋皇室情形:
「……那太監奉了旨,便到三宮住處來,大叫道:聖旨到。老蠻婆子小蠻子快點跪接。太皇太后看見全太后這般狼狽,正自凄涼,忽聽得聖旨到,又氣又惱又吃驚,正不知是何禍事,只得顫巍巍的向前跪下。全太后不知就裏,也只得帶着德祐帝跪下來。太監向全太后兜胸踢了一腳喝道:沒有你的事,滾!這一腳踢得全太后仰翻在地。那太監方才說道:皇上有旨,封老蠻婆子做壽春郡夫人,封小蠻子做瀛國公,快點謝恩。太皇太后福了一福,德祐皇帝叩了頭,太監喝道,天朝規矩,要碰響頭謝恩的。太皇太后沒奈何,低頭在地下碰了一碰。太監道:還有兩碰,太皇太后只得又碰了兩碰。太監道:說呀!太皇太后道:說甚麼?太監道:蠻子真不懂規矩,你說謝皇上天恩,快說!太皇太后沒奈何,只得說了……
「忽然外面又闖進兩個太監來,大叫道:聖旨到。太皇太后德祐帝只得仍舊跪下,低着頭,不致仰面觀看。只聽得那太監齊聲道:奉聖旨,老蠻婆子和那小蠻子仍舊住在這裏,交理藩院看管。那賤蠻婆子攆到北邊高牆裏去,只許她吃黑麵
 ,不准給他肉吃,快點謝恩!太皇太后德祐帝只得碰了頭,說了謝皇上天恩。全太后却只呆呆的站在一旁不動。一個太監大喝道:呔!這賤蠻婆子,還不謝恩麼?全太后道:這般的處置,還謝恩麼?太監又喝道:好利嘴的賤蠻婆子,你不知咱們天朝的規矩,那怕綁到菜市口去砍腦袋,還要謝恩哩,這有你們蠻子做的詩為證,叫做『雷霆雨露盡天恩』呀。全太后沒得好說,只得也跪下碰了頭。」
,不准給他肉吃,快點謝恩!太皇太后德祐帝只得碰了頭,說了謝皇上天恩。全太后却只呆呆的站在一旁不動。一個太監大喝道:呔!這賤蠻婆子,還不謝恩麼?全太后道:這般的處置,還謝恩麼?太監又喝道:好利嘴的賤蠻婆子,你不知咱們天朝的規矩,那怕綁到菜市口去砍腦袋,還要謝恩哩,這有你們蠻子做的詩為證,叫做『雷霆雨露盡天恩』呀。全太后沒得好說,只得也跪下碰了頭。」
亡國君臣的受辱是活該的,寫得生動如畫的倒是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的奴隸的嘴臉。
○ ○ ○
南宋末年的人物,可以寫小說的,除陸秀夫外,還有賈似道和文天祥。前者的貪污糊塗,後者的神忠耿介,都是絕好的小說資料。僅是一首正氣歌,就值得我們為他嘗試了,你看: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勵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鷄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哲人日以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試想,在湫塞潮濕,陰暗不見天日的牢獄中,傳出了這樣的金石之聲,這不僅是值得描寫的小說的戲劇的場面,而且也是再好不過的有聲有色的電影場面。
選自一九四二年十月香港《新東亞》第一卷第三期
鄉愁
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
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屈原:「九章」
一
很少人知道我的家鄉是南京。
我不大提起我的家鄉,並不是因為這家鄉不值得我的懷念,而是因為我對於家鄉的事情實在知道得太少。從小以來,我就承受了父親的命運,開始離開了南京,最初是為了知識,後來是為了衣食,在長江上游和下游的幾個城市裏消磨了我的童年和少年。嚴格的說,教育我的地方是上海,而我理想的家鄉則是北平。南京對於我,實在祇是一個名義上的家鄉而已。除這以外,南京對於我疏淡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南京在我的記憶中沒有甚麼可懷念的地方,而是因為我不想向旁人去分沾她的光榮。自從南京建都以來,冠蓋京華,聽說甚麼都改變了,幾次想回鄉去瞻仰一下,可是怕親戚們誤會我是衣錦歸來,又怕滿朝新貴誤會我是來謀差事,一再躊躇,二十年來,我便不曾踏過家鄉的一寸土地。
也許是真的老了吧,近來,走在擠滿了人可是又寂寞的街上,對着始終是陌生的不斷開着花的香港春天,浮上我心頭的不再是七年來使我戀戀不忘的上海,而是模糊黯淡的家鄉景像了。
二
正如高爾基在自傳中所描寫的那樣,家鄉所給與我的第一個印象,也就是人生的第一個印象,是一種使我終身苦痛的印象:
一個夏天的深夜,在一間古老而陰沉的大屋內,煤油燈光下,躺着一個中年婦人,旁邊睡着一個五六歲的孩子。有誰將這沉睡的孩子從大床抱了出來,他醒了,靜開眼來,看見桌上有一堆的黃豆,有人正在用紅頭繩縛着這個婦人的腳。
這個小孩便是我,牀上躺着的是我的母親。母親是染了當時流行的急症突然死去的,據姊姊後來告訴我,當晚晚飯過後,母親還揹了我哄着我入睡,却不料半夜得了急症,醫生還沒有請到就斷了氣了。桌上的黃豆是救急用的,腳上縛的紅頭繩是一種迷信,預防有甚麼意外。
這陰鬰的記憶支配了我的童年生活,也影響了我的性格,更使我對於家鄉的印象染上了一層灰黯。在我的記憶中,家鄉是沒有春天的。
三
十五歲以前,隨着寄食他鄉的父親,也曾囘過南京幾次。使我至今還記着的,是從下關進城,坐在馬車中所見到的沿路的垂楊。這夾道的楊柳樹,似乎在魚雷學校和日本領事館一帶,長得特別茂盛。「白門楊柳好藏鴉」,這句詩頗能恰好形容了那盛況。有一次,似乎是南京剛經過了政變不久,坐着馬車從這條路上經過,透過密茂的楊柳樹,曾見到路傍的麥田裏,仆臥着不少屍體,黑色的背上寂寞的落了好多楊柳葉。
南京另一個使我難忘的地方,是那荒涼的玄武湖。從湖上望着籠罩垂楊的雉堞,那一種烟水迷濛的景色,確是一種近於詞意的風流瀟洒的美。從坍廢的臺城故址上遙望着湖面,更可以領略到江南水村的烟景。我就曾在這地方消磨了一個無言耽想的下午。現在囘想起來,二十歲以前的我,就能理解這一種逸閒趣味,倒有一點頗值得驕傲的地方。後來聽說玄武湖改成了「五洲公園」,祇要一想起這名字,我的想要再去看看的意念立刻就被打銷了。
成為政治建設中心二十年了的我的家鄉,存在我的記憶中的就是這些陰鬰灰黯,可是却又使我十分珍惜難忘的印象。我之不常向旁人提起我的家鄉,便是不想使旁人知道我的家鄉僅存在於我的幼年記憶中,而今日的南京,早已不是我記憶中的家鄉了。
據說,有些動物,在瀕死之前,本能的要將自己所經過的地方重走一遍。屈原所說的「狐死必首丘」,正是這同樣的意義。如果我近來時常想念家鄉,也是這同一預兆,則我希望就從這一篇短文上,滿足了我的動物本能罷。
選自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香港《華僑日報·文藝週刊》
憶江南
山川
在香港住了這許多年,不知怎樣,對着每天開門就可以見到的山,祇覺得有一( )隔閡。雖說清風明月並不要花錢買,但對着眼前這覆滿了常綠植物的黃沙土的山,總覺得牠是這裏的地主,而我不過是一個客人。我同香港的山做了這許多年的鄰居,牠始終生疏的站在窗外,從不曾來到我的几案間。
香港的山,近在眼前的簡直是街道,從遠處望過來却又成了島,决不是江南風景中的綠水青山的山。雖是滿山鬱鬱蒼蒼,却是沒有冬天,也沒有春天,剛以為不是開花的時節,却從意想不到的高聳喬木上,開出了幾乎使人不敢相信的大紅花來。
這樣的山川,這樣的草木,對於我,雖是在這裏已經住了許多年,却怎樣也是陌生的。
浮動着紫氣的故鄉的紫金山,倒影蕩漾在水裏的西湖湖上諸峰,這樣的山,誠然使人一見之後怎樣也不會忘記,但特別親切的存在我的記憶裏的,却是蜿蜒在江南沿岸的那些不知名的大山。許多年以前,在鎮江的一個中學校裏念書,校舍建在西郊的一座小山頂上,從操場上望出去,東面可以見到橫在天末的一線長江和那號稱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西面一帶,一眼望過去,是一望無盡的連綿的羣山。這些山,雖然事實上是遠在十幾里之外,但我們總覺得好像近在幾席之間似的,不僅山上的烟霧變化,我們有把握可以領會,就是藏在山坳裏的幾間白堊瓦屋,也覺得好像曾經置身其間似的。秋來了,山色漸漸的蒼老,由紫碧褐黃,漸漸的變成灰黯,灰黯得像是沉沉入睡了。終於,經過一個特別清寒寂靜的夜,一覺睡來,從操場上越過校園的牆,牆外的松林,松林下的山谷,一直到對面的大山,一眼望過去,盡是白皚皚的雪。
下雪天照例特別冷,然而這寒冷却不是無情的,從冷的裏面同時也帶來了春天的萌芽。幾次雪落雪溶之後,山色又漸漸的從沉睡中甦醒了。
江南的山,大都是黏質的黃土的,春天一到,被鑽出地面的嫰牙所掀動,土地便發出一種帶着滋潤的香氣。星期六下午,獲得了離校的許可,踏着傾斜的山路走下山去的時候,嗅着了從四週發散出的這一種土地的香氣,我們覺得自己確是也在生長着了。
從香港的黃沙泥和草根之間所散發出的潮濕的氣息,雖是在這春天,使我嗅到了也覺得皮膚發癢,同時還想像到這將使我架上的書脊發霉。也許正因為這樣,雖然在這裏過了六七個春天,我始終覺得自己仍是一個陌生人。
草木
除了香港以外,我曾到過廣州以及廣州附近的幾個著名的城市。在我所走過的地方,我從不曾見到有像江南那樣隨處可以見到的竹林和垂楊。以幽勝著名的碧江蘇氏的花園,所見到的也祇是數不清種類的仙人掌科學植物及尋丈的白蘭花而已。
沒有垂楊,沒有竹,便不易領略風,雨,日光的情趣,更不易領略水的情趣。
當然,在這草木茂盛的南方,儘有許多可愛的花木,剛直的紅棉和穠膩的薑花正可以代表了兩個不同的極端,然而除了兒女英雄之外,詩人要想寄托一種風流瀟洒,甚至輕淡的哀怨情懷,南方便沒有這樣的植物了。
西湖靈隱道士的萬桿修竹,南京城裏的夾道垂楊,置身其間的那一種輕逸的愉快,不是身受者是無法領會的。除這以外,在江南,任何一個三兩茅屋的小村落,任何一道僻靜的小河,總有一片竹林和幾樹垂楊。竹林裏滿舖落葉的地面總是輕鬆乾爽,柳陰下的河邊,若沒有一條板橋,便是兩三塊亂石,這風景,是融合了鄉村生活的中國文學藝術中的基礎風景,不僅是鄉土的,而且是歷史的。
被表現在畫面上的江南水竹風景,在水墨畫的小品裏,我相信一定有很好的逸品,但我至今還沒有眼福見過。我不喜愛鄭板橋的畫竹,正如不愛喜一般中國畫的畫蘭一樣,可說是屬於個性方面的個人的憎愛。到處可以見到的高懸在商人和暴發戶壁上的鄭板橋的畫竹,不論是真跡或是膺品,我覺得總不能傳達江南竹林的空靈瀟洒的風趣。
中國畫人畫柳則是成功的。不論是點綴着兩三點暮鴉的晚秋疏柳,染着淡淡新綠的堤畔的春柳,或是濃陰如翳,籠罩着如沸蟬聲的盛夏的垂楊,中國畫都恰能捉到了那種飄逸多變化的好處,就是攙雜了日本南畫和西洋畫方法的晚近嶺南畫風,用淡綠和水墨染成的烟柳風景,也能使我見了愛好。
在香港,偶爾也曾見到一兩株楊樹,但是迎風搖曳,拂面牽衣的垂柳,則從未見過。沒有楊柳,香港也似乎沒有了烏鴉,夕暮時我們所能見到的,便也祇是躲在大榕樹裏噪雜着的八哥和麻雀而已。至於成片的竹林,香港根本沒有,香港山間雖也有一種蘆草一樣的矮矮的細竹,人家園林裏雖也有一種幾十桿緊緊的叢生在一起的青竹,但這棕櫚一樣的東西,實在算不得竹,而且根本不成林。在這暮春三月,對着從海上襲來的濕霧和季節雨,我祇有益發想起了籠罩在烟水中的江南風景而已。
蟲魚
這幾天的天氣,正是香港一年氣候中最壞的幾天。雨季剛在開始,( )燠的南風,挾着潮濕的霧,使得呼吸沉重,同時也使得一切東西都沁出水來。書櫥上的玻璃,給充塞在室內的濕氣蒸發得起了一層薄翳,隔着玻璃望過去,望着櫥內金碧斑駁的書脊,正如在江南的冬天,從街上隔着充滿了水蒸氣的玻璃窗,望着窗內生了紅紅的爐火,笑語如在天上的人家一樣。
清明剛過,江南也正是雨紛紛的時節,可是,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這時候的江南雨,不是蒸鬰潮濕,而是滋潤有生意的,從路邊的小草以至藏在少女心頭的戀情,都在這種細潤如酥的小雨之下醒過來了。
一夜無聲的小雨,池塘的水都平漲了許多,在這時候,最活躍的是由蝌蚪逐漸蛻變成形的青蛙。愈是荒廢的水塘,便愈是青蛙繁殖的勝地。在江南水鄉的郊外,在這天氣,走到隨處皆是的小池塘的旁邊,從佈滿浮萍的隙間,你總可以見到初成形的拖着尾巴的小青蛙,靜靜的浮在水上不動,似乎在練習着新長成的肺,見了人來,還不知道撲的一聲鑽入水去。
香港的山溝裏,在春天,從不曾見過像在江南所見到的那種黑壓壓的數不清的蝌蚪。草間偶爾也有幾聲蛙鳴,可是除了以前曾在街市上見過幾串待價而沽的田鷄以外,我至今還不曾見過香港的蛙究竟是怎樣。十多年前,第一次避禍來香港時,寄住在九龍城宋王臺下。每當雨天,總可以聽到山脚下的草間有一種牛叫一樣的的鳴聲,襯着積水,那鳴聲汪汪然似乎特別宏大,響徹遐邇。我最初詫異香港的蛙鳴竟這樣的宏大,後來朋友告訴我,這叫着的是另一種小動物,並不是青蛙,不過究竟是怎樣的東西,叫甚麼名字,他也說不出。這次重來,住了這許多年,可是在香港這邊從不曾再聽見過那種汪汪然的鳴聲,也許九龍城那邊還是那樣吧?可是叫着的究竟是甚麼東西呢,這個謎我至今還不曾獲得解答。
香港的蟲,似乎同香港的花一樣,不分季節的亂開着,也不分季節的亂叫着。就如現在,夜深人靜,我側耳諦聽,〔雜〕着山溝裏的水聲,窗外傳來的竟有蟋蟀聲和一連串的油胡蘆鳴聲。香港的春末,倒像是江南的深秋了。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念着這樣的詩句,我想起了春夏之交的江南,想起了街上白糖梅子的叫賣聲,想起了故鄉這時新上市的竹筍,萵〔苣〕和閃着銀光的鰣魚。
人物
有一年的春天,利用了學校的假期,我一個悄悄的到揚州去住了幾天。消失了前代的繁華,寂靜的沉在回憶中的揚州,於殘廢之中含有一種動人憐惜的美麗,那種風趣正是我所最喜愛的一種典型。
正是這樣的暮春天氣,桑樹的葉子已經碧油油的,楊柳早已成陰,在揚州城外著名的瘦西湖裏,我同那時正住在揚州的一位朋友,僱了一葉小舟,緩緩的任着舟子將我們向平山堂划去。
瘦西湖的湖面很狹,也許正因為瘦的原故。那風光與西湖又迥不相同,小舟貼近岸傍緩緩的前進,岸上的垂楊幾乎可以拂到我們的臉上,水聲與岸上行人的笑語相混,彼此祇有幾尺的距離。
突然,在湖面的彎曲處,雜樹特別茂盛的地方,從樹叢中突然有人發出了嘹亮的吟詩聲: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接着,一根竹竿從樹叢中伸了出來,竿端垂着一個白布小口袋。舟子似乎和他很有默契,划到這地方,他率性停止不划了。
這個風流的乞丐是個怎樣的人,我始終不曾見過。從那嘹喨而圓潤如玉的吟詩聲推測起來,該是一個中年人了。那聲音至今還在我的耳邊,是純粹的揚州鄉音,而且我還清晰記得所念的確是這一首詩。
詩丐之類的人物到處可見,但這一個單獨被我記憶着的原因,我想,該與當時的環境和他從這行為上所表現出的個性有關。第一,他選擇了一個使人不能拒絕一點佈施的極適宜的地點;第二,念完了詩,他始終一言不發,而且並不露面,所念的又並不是自己的詩,這態度實在謙遜而又耿介得可愛。若是所念的是「結草銜環待他生」之類的詩句,而念完之後又追着船尾不肯罷休,那恐怕就早已被我忘却了。
揚州到底不愧是一個江南文物的勝地,雖然衰落了,但那裏的人物總還保持着一個舒徐的風度。這種無論什麼時候悠然不慌張迫切的氣概,大約祇有北平人可與相比。當然,揚州也有著名的「青皮」,但若按香港的「浪仔」那樣,蝗蟲一樣的將整座樓房拆得一塊板也不剩,甚至連人家門前的電燈線電燈泡也要偷,揚州的青皮是絕對鄙夷不幹的。
選自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及九日香港《華僑日報·文藝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