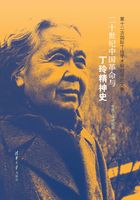
一、“与环境斗争”——丁母的社会活动
勤学
文中屡次出现“与环境斗争”一词。这词表明,丁母做好了与辛劳、困苦的环境作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心理准备。事实上,丁母面对的处境就是非常严酷的。结婚十年后,体弱多病的丈夫去世,丁母得以依赖的娘家亲母亦在同一时期离世。带着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与年幼的女儿,自家经济面临破产,丁母自己也身体虚弱。就在这一时期,丁母从弟弟处得知,女子师范学校——作为女性独立之道路——诞生了。丁母31岁才开始入学,探索她的自立道路……到此为止,小说《母亲》与《回忆》所描述的主要经历基本一致。
小说没有写的丁母波澜万丈的人生,从这里开始起程。“环境”也变得愈发严酷。独力抚养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想要坚持她的学业,其中困难可想而知。因为最初就读的常德女子师范停办(详情不明,据“后记”①记载,发生于1912年),丁母(34岁)为继续学业,带着一双儿女迁往省会长沙,考上了新成立的“第一女师”(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虽然英语课和体操课对丁母而言难度颇大,但她仍花了很大力气学习。由于校规太严格,最终丁母不得不放弃了她的学业。丁母在这个时候深刻地认识到,对于没有他人帮忙来照顾子女的女人来说,坚持学习或工作是极为困难的。
教师的工作
中途退学的丁母,在常德的邻县——桃源县的一所学校(桃源县立女子小学)获得了教师职位(36岁)。校方恳请丁母一定前来出任体操老师。丁母自言不擅体育,但她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成果之一——放足,是女子参加体育活动所必经的痛苦体验。克服这个困难拥有一双大足的丁母,应该已然当得起许多女性的模范了罢。(顺便一提,通过“运动会”在《回忆》中屡次登场可知,作为当时学校的组织活动,“运动会”尤为受到重视。)当然丁母竭尽全力做了运动会活动。还在秋天,体育教师的丁母带学生郊游,为自然之美很受感动。所以她在文章里颇为自得地写道:“我的身体非常进步……不畏寒冷,强健。”
次年,丁母出任当地女校(常德女子小学)的管理兼美术科。不料在学校里,因“急进派”而产生的内部纠纷激化,学校发生分裂。丁母受一部分学生恳求留任授课,并增设缝纫专科,开始尝试实践,以期帮助学生实现“家庭改良”和“独立谋生”。“此吾一生最满意之时期”,丁母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可以说她此时已找到了自己的天职了吧。三年后,丁母一度辞去常德女子小学职务,此后在地方的小学等数校继续任教。
丁母在40岁那年的春天,一个友人要丁母进入地方小学任教说:“(这校)校款困难,薪金不多,地址亦仄,小学生少,不能发达,非你去振作不行。”丁母接受了友人的建议,在这里任教,因为她自己是“生性做人群不争做之事”。丁母送儿女到寄宿校,开始母子分居生活。新校的校舍坐落在古庙中,校长是位年高有德之人。由于学生人数太少,丁母增设缝纫班,并为废除缠足到学生家中访问劝告,并热心地对学生进行指导。
次年,因军界纷争,上课时忽听枪声四起,医院与学校挤满了前来避难的人。看丁母衷心关心照顾学生,有人问及丁母是否挂念在别处的自己子女的平安,丁母回答说:“我既照应人子,想吾子亦必有人照应。”所幸丁母一双儿女最终的确平安无事。
“俭德会”与“会校”
丁母42岁那年,年仅12岁的儿子染急病身亡,先丁母而去。丁母的悲痛非笔墨所能尽叙,她恨不得即刻与儿子相依于地下。丁母虽然希望实现女性自立,怀着满腔心血教育女学生,但在其内心深处,“男儿是后继之人”的想法仍然没有消失,不由地希望儿子将会复兴这个家庭。想必这个希望一直以来苦苦支撑着她。此时的丁母突然陷入了绝望,因此她开始信奉佛教以求安慰。佛教信仰在一个时期内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坐禅,对她而言最能抚慰精神上的伤痛。
是年,丁母成立了一个比较大的组织——名为“妇女俭德会”的“女界团体”(根据《回忆》,该会宗旨包括量力乐捐,不着华服,不得撑伞坐车轿等。可以想见,这应该是一种女性慈善团体)。成员已知的有丁母和一位唤作敏的女性亲戚,除此之外,俭德会的具体人员构成及其背景均不得而知。成立大会有数千人参加,丁母被推荐为临时主席,因此可推定丁母为该组织的中心成员。
作为俭德会活动的一部分,创建学校是其中重要的事情。(丁母有时在文中把它写作“平民女校”,不过这并非正式校名。“后记”①中提及“常德公立育德女校”,但并不能确定是丁母她们所建的女校。下文按丁母惯用说法,称之为“会校”)。这所集女界之力建成的学校,一路上困难重重。但是,丁母为了学校的持续与发展竭尽所能。事实上,建校翌年,会校内部就产生纷争。因丁母在俭德会大会中被推选为该校负责人之一,她便召开了紧急会议。然而与会者寥寥数人,这令她束手无策。丁母此时还在别的学校兼任职务,并顺利涨薪。然而,丁母却向这所待遇优越的学校提出辞呈,要竭尽全力将安置在古庙的贫穷“会校”重建。她说“此会(校)乃我女界之团结处,我同志煞费苦心,成之不易”,“我向来是不畏难与环境奋斗的”。
丁母以古庙为家,一人独守,为会校的重建作努力。之后军阀争斗,时有枪声骚乱,不过在数日内事态平息,会校也平安无事。在丁母的努力下,会校成功重建。由于学生人数的增加,会校也增设了教室和座位,学生们都非常踊跃。秋天时,会校还组织了郊游。一直坚守会校的丁母此时已年届47,而一场意料之外的灾难随即袭来。会校附近发生火灾,火势蔓延到学校,加之民众涌入会校避难,导致学校建筑遭到极大破坏。翌日,俭德会召开紧急大会,然而会员到者寥寥,众人都态度冷淡。不久,会校再度开课,但贷款也累积愈多。
丁母48岁那年,俭德会召开“改组大会”,在丁母的财务决算报告之后进行了选举。这一次,丁母没有被选举上(负责人)。其中缘由,回忆录中并没有明确交代,但可能丁母当时已决定回故乡临澧出任校长(后述)。
参加地方自治
丁母45岁时,湖南筹备地方自治的运动非常活跃,这也影响了丁母。(据“后记”2《年谱》记载的丁母履历,担任“常德筹备地方自治会职员”大约在这一时期)。地方筹备自治,各界派有代表。丁母作为女界代表之一,初次与政治产生了关联。(令人遗憾的是《回忆》并未写及活动议题等详情)。然而,代表们均不按时与会,当严谨认真的丁母准时出席会议时,会场经常空无一人。这种旷时废事的行为让丁母烦躁不已。而与会者中,还有人分党结派,自私自利,其中甚至还隐藏着黑幕。“纵堆金积玉,我不愿向此讨生活也”,因此丁母刚刚涉足政治界便抽身而退了。
创建城东“工读女校”
建成俭德会会校的同时(丁母43岁),丁母为向城东落后贫困区域的女性提供教育,自己筹建了一所学校。她挨家挨户地访问附近的家庭,召集齐了20左右的学生,把学校办了起来。此后学校逐渐壮大。2年后,“艺科”一班学生毕业,她们将一座破庙收拾得干净整齐,在那里进行作品展示,获得了来宾的交口称赞。
然而,在丁母48岁那年,“工读女校”内部也发生了纠纷。经调查,原来是一干嫉妒丁母的人蓄意引起的纷争。丁母认为如果外部有人出手干涉,事情将变得复杂,因此主动放手。数年来倾注无数心血的学校就这样付之一炬。
出任故乡县立女校校长
丁母48岁那年,受故乡临澧新办的县立女校之邀请,出任校长一职。当时丁母已身兼两校职务,对于县立女校的邀请,本想拒绝。然而,想到这是自己于归之地,而且偏僻地方的女性更需要支援,所以虽然知道其中困难重重,但丁母仍然带着三位新上任的教师不辞路途遥远,前去女校赴任。可知丁母积极的姿态,在经历了多次挫折之后,也丝毫未曾改变。
抵达任所时,发现学校周围有田亩池塘,风景自然。丁母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里,下定决心要在此做出一番努力。考虑到女校学生的发展,丁母认为兴办实业至关重要。丁母申请在校内建筑工厂以帮助女子就业,获得官方批准。之后,学校领到一部分工厂建设资金,购买了建厂所需资材。事情到此为止一切顺利。
然而结果却又令人悲伤。简单来说,是年秋天,军阀入侵女校所在一带,部队开进学校驻扎。学校在与军队的“同居”状态下坚持开课,直到完成毕业仪式。然而,翌年,三名新任教师怯于士兵匪贼,辞职而去。辛苦备齐的工厂建设原料,也被没收,转用于军需。丁母也最终筋疲力尽,不得已而辞职。
活动的尾声
丁母的教育活动持续到次年(50岁),但是她追求理想的奋斗行动,在这时已接近尾声。丁母曾热切地希望,能够在偏远的乡下兴办女性学校,为纯朴善良的女童们提供精神与经济上的进步性帮助。但是,在军阀混战的黑暗时代,这个美好的梦想被撕得粉碎。
丁母寄予女性的热情、挑战新事业的勇气、为改善现实而投身实践的行动力,都是非常了不起。如果身处和平稳定的时代,丁母的力量也许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为女性的发展起到作用。可惜在那个时代,“启蒙”在武力面前惨遭败北。
丁玲在《我母亲的生平》一文中有提及。“我母亲从事教育活动,一直持续到1927年上半年马日事变后(指1927年5月21日,湖南的反革命军阀何键等在长沙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及一切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及一切革命的工农群众)才不得不终止下来”。
令人遗憾的是,《丁母回忆录》缺少丁母51岁那一年的整个记叙(原委不明)。根据50岁年的记录,丁母当时尚兼两校教职。文中对战乱的情形有所描写,年末时“北伐的军士来得很多”,到处充斥不安的气氛,最终枪声响起,引起了巷战、火灾、死亡等。
在52岁当年的新年记述中,有关于街道激变和民众被枪杀的记录。描写过于感情激烈,无法从中读取客观事实。但可推知,此时丁母已经结束了教育相关的工作。
之后,丁母在53岁时受女儿丁玲之邀去上海。丁母坐汽船赴沪,受到女儿热情款待。丁母游览了杭州西湖等名胜。此后,《回忆》里再不能看到关于丁母社会性活动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