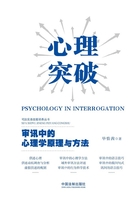
三、有心理强迫属性的审讯策略在审讯中的适用之界限
由于审讯行为本身具有强迫属性,心理强迫由于不涉及侵犯人权的身体伤害与虐待,因而在审讯中应当是一个中性概念。但“度”的把握至关重要,否则亦涉及非法。《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不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其“强迫”既包括了通过刑讯的身体强迫,也包括了威胁、引诱、欺骗方式等施加的心理强迫,然而,在审讯中,侦查人员常常要运用说服教育、情感感化以及使用证据等常规的审讯方法,在运用这些方法时,也会从策略的角度考虑各种方法的全面运用,因此,引而不发、避实击虚等审讯策略就常常被巧妙地使用。这些策略和方法,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或多或少都有对犯罪嫌疑人的认知、情绪情感以及意志进行引导和影响的功能,因此也具有心理强迫的特征[20]。
威胁、引诱、欺骗的取证手段并不像那些直接作用于人身体的强制性物理手段一样,它是通过言语、环境、心理等向犯罪嫌疑人施加压力,对于威胁、引诱、欺骗获得的供述应属裁量排除。
威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不会影响到犯罪嫌疑人的意志自由的,如办案人员加重语气、态度严肃,包括审讯中运用的“白脸和红脸”的审讯策略,只要“白脸”的扮演者没有使用暴力,没有以暴力相威胁,只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贬低”,表现出来不耐烦,对被审讯者造成一定的压力,那么这些审讯方法都是适当的;另一种为法律所禁止的方法。比如说“再不说就把你女儿工作搞没了!”等,包括以剥夺犯罪嫌疑人生命、自由、财产,损害其名誉、信用等这些不利结果相威胁的方法,都是不适当的,应属非法取证。
引诱包括诱供和引供,“诱供是指侦查人员给予犯罪嫌疑人某种利益或好处为条件,诱使其供认,引供则是指侦查人员通过自身的假设或推想来引导犯罪嫌疑人进行供述”[21]。引诱也包括很多内容,比如围绕“坦白从宽”所进行的规劝和政策攻心,对犯罪嫌疑人表示关心、为犯罪嫌疑人积极安排和家人见面,等等,这些行为都是可以理解和被人们所接受的。过度的或者是极有可能影响犯罪嫌疑人供述自愿的引诱,主要是指办案人员以法律禁止,或在其权力范围之外的利益相引诱。比如“如果你现在交代,只判你三年,如果不老实,最后要判五年以上”或“你若交代可以不判你死刑”等,事实上,作为侦查人员,他并没有定罪量刑的权力。此种情况下,即使是无罪的犯罪嫌疑人,也有可能为了避免从重处罚而承认自己有罪。
欺骗,即通过虚构的情节使得别人得出虚假认识的行为。[22]有学者指出:“侦查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对抗性’,又可以称为‘博弈性’。在侦查中要擅长运用策略,则难免会采用一些欺骗手段。”[23]实践中,办案人员常把引诱和欺骗作为审讯策略技巧来使用,很多时候,引诱和欺骗与常用的审讯策略技巧并不容易区分。
当办案人员告知犯罪嫌疑人:“你现在不交代可别悔。”这是否属于威胁?当办案人员告诉犯罪嫌疑人只要如实交代,检举揭发其他人的犯罪行为,就可能得到从轻处理是否属于引诱?通常,如若犯罪嫌疑人的自由意志没有被剥夺,即为合法的,所获得的口供可作为证据使用。
在审讯中,适度地欺骗、引诱被认为是审讯的策略或谋略。审讯策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欺骗的成分。如办案人员用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告诉嫌疑人:“别人已经交代,你扛着也没有用,只会对你自己不利。”费雷德·英博教授指出了判断取证合法性的标准,办案人员在取证中,如果对特定哄骗方式的合法性产生疑问,则可以自问“该方式是否会导致无罪人员承认罪行?”当得出否定答案时,则可以继续取证;当得出肯定答案时,则需要停止。这种标准是可以被接受和理解的检验标准。[24]超过限度的欺骗主要是指办案人员以超出自身权力范围不可能实现的允诺或者以虚假的证据和事实欺骗犯罪嫌疑人,从而使犯罪嫌疑人违背意愿,做出虚假供述。比如说:“快讲吧,讲了就没事情了,就放你回家。”2012年9月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被称为新刑事诉讼法第一案的“郭宗奎等贩卖毒品案”中,本案的辩护律师指出,当郭犯于2011年8月21日在四川被逮捕之后,北京市公安局的两名工作人员通过威胁亲人安全、摔板凳及拍桌子等手段迫使其认罪。并且,相关工作人员在押送郭犯的路程当中,当面讨论相关案情,对其诱供,告知其当事人在认罪的情形下不会判很久。郭犯的辩护律师要求法院启动排除程序,要求排除公安侦查人员采用诱供和逼供而得到的相关供述。另外,郭宗奎向法庭具体叙述了侦查人员威胁的内容,即“你要是不承认就别想再见到你女儿”。该案主审法官在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其之所以接受辩方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主张,非常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被告提出的受到侦查人员威胁的内容非常具体,而其之所以未接受出庭作证人员有关未对被告人进行威胁的说明,理由恰恰是:“主要为公安和检察官证人没有阐述审讯时的具体情形,没有具体说明没有对于郭犯实施言语威胁。相反,郭宗奎及其辩护律师所给出的所受到的言语威胁则十分详尽,而侦查人员与公诉人没有给出具体内容,因此法庭则怀疑侦查人员进行了威胁。”[25]虽然从审讯的目标上来看,犯罪嫌疑人易被欺骗,则侦查人员就易获得供述,但从司法行为的最终结果看,这种心理强迫状态下获得的供述,有错误的可能性,可能导致刑事错案的发生;另外,犯罪嫌疑人一旦认识到被欺骗,则有翻供的可能性,同时滋生对公安司法机关的怨恨情绪,损害了刑事司法的社会效益。因此,除了合法的审讯策略与方法外,欺骗、引诱等心理强迫的方法在审讯中应当被禁止。
在审讯中具体运用审讯策略时需要注意策略与欺骗、引诱的界限,防止基于策略与方法的过度运用而导致的错案以及与司法诚信背道而驰。欺骗、引诱等心理强迫的方法,在审讯中会影响到犯罪嫌疑人意志的选择性,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形成有关案件证据、法律处置等内容的一种确定性的认识,在这种确定性认识的影响下,犯罪嫌疑人难以做出依据自己的选择性判断的供述决策,因而形成供述意志的非任意性结果。有关研究表明,受监禁者意思能力瑕疵的概率远高于正常人,且此概率与监禁期成正比。该研究特别针对心理临崩溃症状、思维过程混淆、心理健康全面恶化这三类心理问题,因为此三类最可能直接影响意思表示正常与否。通过对特定数量人群的抽样调查,美国学者得出以下数据:自由状态下,正常成年人罹受心理临崩溃症状的比例为7.7%,思维过程混淆的比例为10.8%,未出现心理健康全面恶化的个案;普通保护性监禁的情况下,成年人出现上述三种心理问题的比例分别为48%、65%和52%。[26]因此,除了合法的审讯策略与方法外,欺骗、引诱等心理强迫的方法在审讯中应当被禁止。
根据最高法院相关精神,由于使用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收集的证据极有可能是虚假的,因此,如果法庭通过审查审讯记录等证据材料能够认定侦查人员采用引诱、欺骗方法获取被告人供述,且该供述不能与在案证据相互印证,也可以从证明力的角度,因该供述具有虚假性而依法排除。
[1] 详细分类前文已述。
[2] 表20、21由(日)浜田寿美男教授提供。
[3] 吴纪奎:《心理强制时代的审讯规制》,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3期。
[4] 参见Richard A.Leo&Welsh S.White,/Adapting to Miranda:Modern Interrogators.Strategies for Dealing-Withthe Ob-stacles Posed by Miranda0,84Minnesota Law Review,1999,pp.431~447。以及Richard A.Leo,/The Impact Of M-iranda Revisited0,86Journal of Criminal Law & Criminology,1996,pp.660~666。
[5] [英]Gisli H.Gudjonsson(古德琼森):《审讯和供述心理学手册》,乐国安、李安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169页。
[6] [美]Elliot Arronson等:《社会心理学》,侯玉波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1页。
[7] Gudjonsson,G.H.The application of interrogative suggestibility to police interviewing.In J.F.Schumaker(Ed.),Human suggestibility:Advances in theory,research,andapplication(pp.279~288).New York:Routledge,1991.
[8] 赵桂芬、毕惜茜:《犯罪嫌疑人供述障碍的心理学研究》,王怀旭主编:《侦查讯问研究与应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161页。
[9] Schachter,S.& Singer,J.E.,Cognitive,social and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emotional state.Psychological Review,1962,69,p.379~399.
[10] [日]片成男、[日]高木光太郎:《陈述的心理学分析方法——日本足利案件的文体分析为例》,载《全国侦查中的心理学应用研讨会论文汇编》,2016年11月。
[11] 何胜利:《口供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2] 范红亚:《浅谈口供的真实性》,载《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6期。
[1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于2012年成立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行为科学侦查应用实验室”,包含语音分析、眼动分析、肢体行为分析、生理信号采集分析等。
[14] “运用证据识别供述”已经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赵桂芬教授曾发文介绍并分析此种识别供述的方法,本部分将赵桂芬教授的研究进行介绍。其成果发表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15] 林喜芬、秦裕林、葛岩:《无辜者何以被怀疑——警察辨别真伪陈述能力的认识—行为研究述评》,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33—44页。
[16] GRANHAG P.A.,STROMWALL L.A.,WILLEN R.M.,et al.Eliciting cues to deception by tactical disclosure of evidence:The first test of the Evidence Framing Matrix[J].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2013,18(2):341~355.
[17] TEKIN M.S.,GRANHAG P.A.,STROMWALL L.A.,et al.How to make perpetrators in denial disclos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crimes[J].Psychology,Crime & Law,2016,22(6):1~35.
[18] PEACE是由一套侦查访谈中培训模式的几个环节的首字母组成,具体包括计划和准备(Planning & Preparation),建立关系和解释谈话目的(Engaging with the interviewee & Explaining the interview process),获得陈述(Account),结束访谈(Closure of the interview),评估(Evaluation)。参见CLARKE C.,MILNE R.,BULL R.Interviewing Suspects of Crime:The Impact of PEACE Training,Supervision and the Presence of a Legal Advisor[J].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Psychology and Offender Profiling,2011,8(2):149~162。
[19] 赵桂芬:《国外侦查讯问中识别谎言方法的新发展及启示》,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20] 赵桂芬:《论审讯中的心理强迫》,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60页。
[21] 毕惜茜主编:《审讯理论与实务探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2] 安文霞:《“威胁、欺骗、引诱”审讯方法的另类思考》,载《政法学刊》2012年第6期,第54页。
[23] 龙宗智、何家弘:《“兵不厌诈”与“司法诚信”》,《证据学论坛》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第167页。
[24] 弗雷德·英博:《审讯与供述》,何家弘等译,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页。
[25] 北京青年报:“证词涉嫌逼供所得,法庭弃用非法证据”,载http:∥news.sina.com.cn /c /2012- 09-14 /000025170753.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4月3日。
[26] 陈诚:《受监禁者行为能力瑕疵实证——基于心理学、司法制度及司法实践的考察》,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84—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