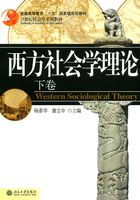
第二节 理性行动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
与他的侧重宏观—微观联系的主旨相适应,科尔曼的理论概念主要在两个分析层次上展开:一个是基本行动层次,另一个是系统行动层次。基本行动是指两个行动者相互依赖的行动,与这一层次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是:行动者、资源、行动者的利益、简单社会关系(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等)。系统行动包括三方或更多的行动者,与此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有:复杂关系(如权威结构、信任结构)、社会规范和社会资本、法人行动。
一、基本行动的要素
1.行动者、资源和利益
科尔曼对社会行动者的定义借鉴了经济学的“具有目的性的理性人”的观点。他认为,行动者都有一定的利益偏好,并且都试图控制能满足自己利益的资源。“资源”的种类很多,如财富、物品、事件、信息、技能、特长、感情等等。行动者与资源之间是控制关系与利益关系。“行动者仅仅通过两种关系与资源(间接地与其他人)建立联系,即控制资源和获利于资源。行动者只有一个行动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利益。”
行动者的利益是由一定的需要和偏好构成的,它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需要和偏好。科尔曼对利益并没有下精确的定义,但他区分了两种自我的利益:(1)客体自我,它涉及人的感受和满足程度,并由此形成了人的行为动机。但是对客体自我的利益很难加以观测。(2)行动自我,它服务于客体自我,努力使之感到满意,就如同人手的行动抓到了一只苹果,使自我感到满意一样。行动自我的利益是可以观测的,它表现为获取对于事件控制所必需的资源数量。两种自我的关系可比喻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 。
。
在大多数情况下,行动者并不能控制能满足自己利益的所有资源,许多资源是由其他人控制着;同样,行动者也控制着其他人所需要的某些资源。这样,最基本的行动是两个行动者交换资源,以此来满足双方的利益,这也是人际互动或行动者相互依赖的起因。基本行动是任何行动系统的基础,两人的社会交换也是一些社会理论(如霍曼斯、布劳的“交换理论”)的基础,科尔曼正是以此为基点来扩展他的理性行动理论。
2.社会最优状态
通过对行动者和基本行动的定义,科尔曼参照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引入了“社会均衡”和“社会最优状态”的概念。“社会均衡”是在多次交换过程中逐渐实现的。按经济学的理论来说,行动者之间的交换是使双方都获利而又不受损失,这些利益在交换之前是无法得到的;如果这些交换稳定在某种状态而不再改变交换形式或交换比率,那么社会就达到了某种均衡状态。由于不同的交换率和每个人的获利比率不同,所以社会均衡点可以有多个。“社会均衡”不是平均状态或理想状态,而是一种相对状态,即相对于不稳定、不均衡的交换而言。一般来说,处于均衡状态的交换比起交换之前的资源分配所达到的利益满足程度要高。“社会最优状态”是在一定系统中最佳的社会均衡状态,它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相联系。古典经济学假设,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会自动地(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牵引)导向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或社会最优状态。在社会系统中,最优状态有许多种,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行动系统(或区域),每一系统都有自己的最优状态;在有些系统中,还存在着多个最优点(类似于经济学的“帕雷托最优”)。科尔曼指出,引入这两个概念,一是为了对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状态进行衡量和评价,二是为了像经济学那样构造规范性的社会学理论 。
。
3.行动的权利
社会交换必须以一定的社会秩序为前提,因为行动者对资源的控制并非是自然而然的或毫无疑义的。这就需要建立行动的权利结构。权利可分为“自由(处置)权”和“要求权”,权利结构规定每个行动者对何种资源有自由处置权或利用这些资源采取行动的权利。例如,规定奴隶主是否有用他的奴隶交换其他物品的权利,规定吸烟者是否有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权利。通过对吸烟权的讨论,科尔曼指出,“权利既依赖权力,又依赖他人的承认”。权利结构是由行动所涉及的所有人共同决定的。行动者可以依靠强力或影响力强制其他人承认他的要求,也可以依靠共识,形成规范,使“有关他人”承认他的权利。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涉及社会共识和权力分配。“社会的认可是权利存在、消失以及转让的前提条件。权利的实施必须以权力予以保证。”
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行动者之间除直接的交换关系、人际(情感、互助)关系外,还存在着与系统行动有关的权威关系和信任关系,这些关系界于微观与宏观之间,它们可以说明众多行动者的基本行动是如何转变为系统行动的。
1.权威关系
科尔曼对权威关系的定义是:如果行动者甲有权控制乙的某些行动,则行动者甲和乙之间存在着权威关系。也就是说,行动者乙将自己对某些资源或行动的控制权转让给行动者甲,从而建立了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间的关系。权威关系可分为两种类型:(1)共同的权威关系。即被支配者转让控制权的前提是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支配者行使权威能使被支配者获益。但支配者并不直接用自己的资源换取控制权,而是通过承诺使被支配者预期到未来的利益而转让控制权。如工会、政党领导人的权威。(2)分离的权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的利益并不一致。支配者行使权威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被支配者服从权威是为了直接获得某些补偿。这种关系类似于市场交换关系。不同的是,被支配者付出的不是物品,而是对自己的某些资源(如能力、时间)和行动的控制权。如企业领导人、行政长官与雇员、下级之间的权威关系 。
。
在实践中,这两种权威关系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共同的权威关系中,主要的问题是支配者超范围地行使权威,使被支配者失去过多的控制权而受损,这就涉及如何监督支配者,使其在必要的范围内为实现一致利益而行使权威。另一问题是由于被支配者未直接获得失去控制权的补偿或他对预期利益的估价较小而不服从权威。因此,共同的权威关系的维持与加强既取决于双方有较多的、一致的长远利益,也取决于双方对权威范围和一致利益的共识。在分离的权威关系中,主要问题是被支配者的消极行动(如怠工)会损害支配者的利益。要有效地监督被支配者的行动就需要建立监控系统和赏罚制度。另一问题也是支配者超范围地行使对被支配者的控制权,例如雇主对雇员的性骚扰 。
。
2.信任关系
最简单的信任关系包括两个行动者:委托人与受托人,他们的行动目的都是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信任关系是指委托人将自己的资源委托给受托人使用,以便得到比不存在委托关系时更大的利益。委托人在建立信任关系时要考虑三种因素:受托人确实可信的概率(P)、如果受托人不可靠所造成的损失(L)、受托人确实可信所得到的收益(G)。委托人的决定类似于经济学理论中风险条件下的决策模型。对受托人而言,由于他在接受信任时已经获得了利益(使用他人的资源),所以他在以后面临的选择是:违背诺言还是讲信用。对他的选择有影响的因素,一是他本人的道德观念,二是外在的社会结构。科尔曼指出:“为了保护委托人的利益,还应该创造某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受托人只有恪守诺言才能获得好处” 。这种社会结构的形式主要有较持久的互赖关系和内部联系密切的社会组织。经验研究表明,在两人的短暂联系中,受托人违约的概率更大。但在持久的互赖关系中,受托人一次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远远小于他失去信任所造成的损失。同样,在联系密切、信息交流广泛的社会组织中,受托人如果违约,他也将失去其他组织成员的信任。
。这种社会结构的形式主要有较持久的互赖关系和内部联系密切的社会组织。经验研究表明,在两人的短暂联系中,受托人违约的概率更大。但在持久的互赖关系中,受托人一次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远远小于他失去信任所造成的损失。同样,在联系密切、信息交流广泛的社会组织中,受托人如果违约,他也将失去其他组织成员的信任。
3.复杂关系:权威系统与信任系统
由两个行动者的简单关系发展到多个行动者的复杂关系标志着由微观互动到宏观结构的转变,因为复杂关系不仅涉及超出两个人面对面互动的间接关系,而且还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如权威结构、市场结构等)。不仅如此,科尔曼认为,由复杂关系形成的社会结构还表明了系统行动的三个组成部分:微观互动、微观到宏观(结构)的转变、宏观结构对微观互动的影响 。
。
以权威系统为例,任何社会都会从简单权威关系发展出各种权威结构,这一方面是社会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只有通过权威结构,才能提供行动者所需要的各种公共产品(如法律、安全保障等)。与简单的权威关系相比,复杂的权威结构是由三种角色构成的:支配者(也称权威委托人)、代理人、被支配者。支配者将自己掌握的某些权利委托给代理人,由他们具体行使权威,如国家领导人授予各级行政官员一定的职权,企业主给各级经理一定的管理权,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类似于分离的权威关系,因为两者既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也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因此,如何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监控和激励是现代组织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在马克斯·韦伯的科层组织理论中是被忽视的。
委托人、代理人、被支配者这三种角色的复杂关系和微观互动形成了社会的权威系统(如科层组织、等级制度、法规体系)和系统行动(如行政管理、收入分配),这是微观到宏观的转变。宏观结构和系统行动的结果又对行动者有反馈作用,行动者根据这些结果作出判断(如目标是否实现、分配是否公正、权利和利益是否受损等),并依据这些认识调整自己的行动或改变相互关系,这是宏观到微观的转变。
社会的信任系统也是由简单的信任关系发展起来的。在市场、金融、教育、文化、科技、政治、社会生活等等领域中都存在着信任结构,即由许多复杂的信任关系联结起来的网络。这种信任结构是由三种角色构成的:委托人、中介人、受托人,他们组成了一条信任链,委托人信任中介人,中介人信任受托人。例如,储户—银行—借贷人、用人单位—职业介绍所—求职者、选民—人民代表—候选官员、歌星—经纪人—晚会组织者。中介人需要担保受托人的履约能力。中介人分为三种类型:(1)顾问(或推荐人),他提供受托人的信息和他本人的判断,但不承担责任,如职业介绍所。(2)保证人,他需要承担受托人违约的责任,赔偿委托人的损失,如银行。(3)承办人,他具体经手将委托人的资源转给受托人,如歌星经纪人。除了单向的信任链外,还存在着相互信任的结构,即相互委托自己的资源,这种结构可增强互赖关系,减少违约的可能性 。
。
三、社会规范与社会资本
以往的许多社会理论(特别是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都假定:社会规范是既定的,个人通过社会化将其内化并依据规范行动。而理性行动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个人的利益偏好是既定的,行动者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动。科尔曼认为,社会规范是在微观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宏观建构,它伴随着各种赏罚措施又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因此规范是与利益考虑结合在一起的。理性行动理论要研究规范是怎样产生的,它在众多行动者的互动中是怎样维持的,即规范的微观基础问题 。
。
1.社会规范的产生及类型
社会规范是通过社会共识形成的、非正式的有关行动权利的规定,如“不能在公共餐馆吸烟”、“参加晚会要穿礼服”等等。规范不同于法规,它不具有正式性和法律强制性,但有些规范通过立法可转变为法规。各种规范都是针对某种(或某类)行动制订的,这种行动称为焦点行动(如吸烟、穿着打扮)。规范的产生是由于焦点行动具有外在性,即行动的结果对其他人有影响,例如在公共场所吸烟会影响其他人的健康,损害他人的利益。有些行动的外在影响是使其他人获益,如助人为乐的行动。因此,有些规范是鼓励这些焦点行动。科尔曼认为,“利益为规范提供了基础,即接受外在影响的人们产生了对规范的需求” 。受焦点行动的外在性影响的其他人称为“规范的受益者”,受规范所限制或鼓励的行动者称为“目标行动者”。
。受焦点行动的外在性影响的其他人称为“规范的受益者”,受规范所限制或鼓励的行动者称为“目标行动者”。
规范可分为几种类型:(1)共同性规范,即规范的受益者和目标行动者都能从规范的实施中获益,如“要礼貌待人”。(2)分离性规范,是对目标行动者的限制,使他的利益受损,但使“有关他人”获益,如禁烟的规范。(3)惯例性规范,是对长期形成的习惯和行为方式的规定,如在许多国家,驾车“要靠右行驶”(而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惯例是“靠左行驶”)。规范还可分为指令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前者不限制某种行动而是提倡某种行动(如“要尊敬老人”),后者是限制某种行动(如“不能随地吐痰”)。
2.有效规范的实现
规范的制订并不能保证它的实现,它的实现必须有其他手段来保证。如果行动者不服从规范,就需要对他实行惩罚,只有这样规范才能行之有效。有效的惩罚措施依赖于“有关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结构可以从两个方面保证惩罚的有效性:第一,受影响的其他人采取联合行动对行动者施加压力,如社会舆论。第二,“有关他人”之间建立利益结构,共同承担实施惩罚的费用(如游说行政和立法部门)。
规范是一种公共物品。如果说规范的建立是一级公共物品,那么规范的实施则是二级公共物品。规范的实施涉及惩罚问题,实施惩罚要付出一定代价,如果有关他人都不愿意付出代价,那么规范就形同虚设。例如,见义勇为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补偿或奖励,那么就没有人去惩罚违反规范的行动者。科尔曼认为,奖励不足就会产生坐享其成(或“搭便车”)的现象,即大家都等待其他人采取行动而自己从中受益;奖励充分不仅是实施有效规范的必要条件,而且还会产生热情奉献的现象,即热心公益事业或为集体利益冒风险。有效的奖励措施也依赖于有关他人的社会关系结构 。
。
但规范的实现并不都依靠外在的赏罚措施,例如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许多人都自觉地遵守规范。这就涉及“规范的内化”问题,即个人建立了内在的赏罚系统,它规定哪些行动会受到自我谴责,哪些行动会得到奖励(或自我满足)。“规范的内化”(或社会化)是怎样实现的?科尔曼承认,由于理性行动理论以个人利益是既定的为前提,因此它无法在微观层次上说明个人利益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这涉及个人心理和意识的层次),这是理性行动理论的缺陷 。但在宏观层次上,理性行动理论可说明在什么条件下,行动者试图使他人内化规范(如父母对子女)。内化或社会化是通过思想教育和文化熏陶使个人与社会(他人、父母、团体、企业、社区、国家等)实现认同,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这相当于塑造或改变个人的利益结构。这种内化工作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因此只有当外在惩罚系统失效或代价更高时,社会行动者才会投资于内在惩罚系统。
。但在宏观层次上,理性行动理论可说明在什么条件下,行动者试图使他人内化规范(如父母对子女)。内化或社会化是通过思想教育和文化熏陶使个人与社会(他人、父母、团体、企业、社区、国家等)实现认同,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这相当于塑造或改变个人的利益结构。这种内化工作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因此只有当外在惩罚系统失效或代价更高时,社会行动者才会投资于内在惩罚系统。
3.社会资本
在复杂的行动系统中,人们建立了各种社会关系,并形成了各种人际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为个人提供了新的资源——即社会资本。原始性社会资本是由家庭、村社提供的,它使个人在遇到困难或需要帮助时可以得到必要的社会支持,包括物质支持和感情支持。社会资本是一种表现为相互关心、相互信赖关系的无形资本或公共物品,这种资本很难通过市场交换来提供。创造社会资本的条件是,需要在较稳定、封闭的社会网络中通过较长期的互动形成道德观、文化观的共识。与其他形式的资本(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不同,社会资本的特征是:(1)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由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2)社会资本只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它具有不可转让性。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是相互信任关系(可相互提供资源),其他的形式还有:共享的信息网络、有效的社会规范、权威关系以及合作性的社会组织(可提供公共物品) 。
。
四、基本的分析框架
在科尔曼看来,任何行动系统都是某种社会交换系统,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是通过人们的交往和交换行动形成的,它反过来又对人们的行动有制约作用。因此,对人的行动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偏好,另一个是结构制约。结构可分为三种类型:市场结构、权威结构、信任结构。在不同的结构中,对行动的制约机制是不同的,经济机制在市场结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在权威结构和信任结构中,权力(或实力)、社会规范和社会资本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三种结构的共同特征是,它们反映了行动者的资源和权利的分布状态,行动者据此制订了交往或交换的法规(规范)和制度;同时,行动者也可以改变资源和权利的分布状态,并改变现有的法规和制度。
理性行动理论的分析框架如图1-2所示,这一框架可同时用于对基本行动和系统行动进行分析和预测。科尔曼认为,任何行动系统都包含四个主要概念。其中,“个人利益”指个人需求及其满足程度。“控制分布”指每个行动者所控制的资源和权利及其分布。这两个概念说明行动者与资源的关系,它们是微观水平的概念。“资源价值”取决于有实力的行动者在相应资源中具有的利益,“行动者的实力”存在于他控制的有价值的资源之中。这两个概念是宏观水平的概念,它们说明行动者和资源在整体行动系统中的特征。“事件的结果”指交换行动(或互动)所形成的社会安排(如某种社会关系或制度等等) 。
。

图1-2 理性行动理论的分析框架
科尔曼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例如,在男女恋爱中,双方是交换他们的感情资源,行动者对于对方的感情需求越高,则对方感情的价值就越高。反之,获利(需求)较少的一方具有较强的实力,由于他(或她)掌握着较高价值的感情,因此在此种交换中起主要控制作用,并能使事件的结果按自己的意愿发展(如建立恋人关系或朋友关系或一般关系)。又如,在分析利益群体的冲突和争议时,根据不同群体与所争议问题的相关利益以及它们对资源的分别控制,就可以预测争论的结局。总之,在这一因果理论框架中,如果已知利益和资源控制在事件中的分布,就可以计算出每个行动者的实力和每一事件的价值,进而可推论出在均衡状态下,每个行动者对这一事件的控制程度以及事件的结果。同样,如果已知交换前和交换后资源控制的均衡分布,那么就可以由图1-2反箭头方向推论出每个行动者的实力和他所控制的资源的价值,以及行动者在每一种资源中的利益。在第五编(数学分析)中,科尔曼首先建立了对简单行动进行这两种因果分析的数学模型和计算公式(第25、26章)。
在上述基本行动分析模型的基础上,科尔曼还发展了对各种复杂的系统行动(包括权威系统、信任系统和法人行动)进行分析的数学模型(第27—34章)。在他看来,这些模型是对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模型的扩展,因为社会系统行动并不局限于经济行动,社会交换虽然包含经济交换,但它并不等同于经济交换。这种不同表现在几个方面:(1)许多社会交换不是在相互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进行的,而是在各种信任结构和权威结构中进行的,因此交换的制度与结构背景不同。(2)在许多社会交换中,所涉及的资源不是私人控制的物品,而是不可分割或不可转让的公共物品,因此交换对此类资源的控制权不同于纯粹的经济交换。(3)在理想的社会交换系统中,由于社会规范和社会资本的作用,不存在坐享其成的问题,也就是说,系统中的交易成本为零。通过上述界定,他建立了一个与经济学理想竞争市场模型相对应的“理想社会系统”模型 。
。
理想的社会行动系统的关键是通过共识达到交换的均衡,即由共识建立的法规(或社会规范与社会资本)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使交换行动得以稳定进行。共识是在社会交往中建立的。这种社会交往系统称为行动的外部系统,但共识又连接着行动者的内部系统,即行动者将法规或社会规范加以内化。“每一行动者均有一与外部行动系统部分一致的内部行动系统。行动者的行动基本上以利益为起源,但同时也源于上述内部系统。一种行动之所以出现,是依据赞同不同事件后果的利益,对于相应事件的价值所作的判断。形成行动内在系统的基础是行动者建立的法规。在这一法规中,行动者观察到各种行动者拥有的权利、资源和利益。”
通过上述分析,科尔曼揭示了由个人动机到社会交换、由基本行动到系统行动的内在逻辑关系,指出了由微观到宏观、宏观到微观转变的途径和机制,提供了在个人理性选择基础上分析各种形式的社会行动的理想模型。他指出,在不同的交换行动中,“行动者自身行动的控制权或者由行动者本人掌握,或者由其他人掌握(行动者把控制权转让给这些人)。其结果,行动者有时依据自身利益行动,有时根据特定的他人利益行事,有时又按照规范采取行动。合理性不仅存在于依据本人利益采取的行动,而且存在于建立内在法规的行动中。因为根据内部行动系统采取的行动能使行动者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