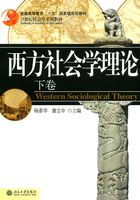
第六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变迁理论
帕森斯早期的著作很少涉及社会变迁问题,这使得人们批评他的理论不能描述和解释社会变迁过程。部分地作为对这些批评的一种反应,帕森斯晚期与其支持者们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对社会变迁过程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被称为“分化理论”的功能主义社会变迁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点是:(1)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式是社会分化,社会变迁的基本趋势是不断地从功能重叠的简单结构向功能特化的复杂结构演进;(2)提出推动社会分化的基本动力是社会的功能需求以及由此导致的结构性压力,每个社会都有一定的功能需求,当这些功能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满足时,就会对社会结构产生一种压力,迫使社会创造出一种更为有效、更为分化的结构安排;(3)社会分化的结果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的效率和效力;(4)社会分化过程包括分化、适应性增长、包容和价值概括化几个基本环节 。
。
然而,这个最初的分化理论又引起了人们对它的新的批评。人们指责它:(1)关于社会分化是社会变迁基本形式的说法过于空洞抽象,缺乏对变迁过程的历史与经验的专门分析;(2)对社会变迁动力的解释过于简单,未能对卷入社会变迁的具体社会群体的作用进行考察,也忽视了权力与冲突对变迁的影响;(3)认定分化必然导致系统效率与效力的提高,这点值得质疑;(4)对现代社会的状况过于乐观,与整个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一样内在地具有保守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当代的新功能主义者们承认了上述批评的合理性,并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试图在坚持分化理论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分化理论。按照柯罗米的归纳,他们的努力主要指向四个方面:
一、扩展原初分化理论模型的经验范围
虽然几乎所有的新功能主义者依然坚持分化是社会变迁的基本趋势,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自己的研究明确地提出,在经验世界中有许多社会变迁过程与分化的“大趋势”并不一致甚至完全背离。例如,鲍姆和莱切尼尔等人强调指出,除了分化以外,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还存在着“逆分化”(dedifferentiation)现象,即拒斥社会的复杂性而促使社会组织朝着较低分化水平的方向变迁,如“原教旨主义”运动等。在现代社会,“逆分化”现象多数是作为一种对现代化不满的结果而出现的 。钱帕基(D.Champagne)等人则提出了“不平等的分化”(unequal differentiation)的概念,用来表示不同的功能领域在分化的速度与程度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种现象。钱帕基以他对Tlingit社会的经济研究来说明这个概念。他指出在Tlingit社会中,由于西方入侵的影响,经济与政治领域同传统的亲属结构之间产生了较高程度的分离,而团结与文化系统却仍然与传统主义混淆在一起
。钱帕基(D.Champagne)等人则提出了“不平等的分化”(unequal differentiation)的概念,用来表示不同的功能领域在分化的速度与程度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种现象。钱帕基以他对Tlingit社会的经济研究来说明这个概念。他指出在Tlingit社会中,由于西方入侵的影响,经济与政治领域同传统的亲属结构之间产生了较高程度的分离,而团结与文化系统却仍然与传统主义混淆在一起 。与此相应,柯罗米等人又提出了“不平衡的分化”(uneven differentiation)这个概念来与钱帕基的概念相补充。“不平等的分化”指的是不同领域或制度之间在分化速度与程度上的差异,“不平衡的分化”则指的是某一制度部门或角色结构在不同地域之间分化速度与程度上存在的差异
。与此相应,柯罗米等人又提出了“不平衡的分化”(uneven differentiation)这个概念来与钱帕基的概念相补充。“不平等的分化”指的是不同领域或制度之间在分化速度与程度上的差异,“不平衡的分化”则指的是某一制度部门或角色结构在不同地域之间分化速度与程度上存在的差异 。柯罗米研究了大众政党制度初起时在美国不同地区之间发展速度与程度上的差异,亚历山大、罗德斯等人则分别研究了更为分化的新闻媒介制度,高等教育制度在不同国家之间发展速度与程度上的差异,等等
。柯罗米研究了大众政党制度初起时在美国不同地区之间发展速度与程度上的差异,亚历山大、罗德斯等人则分别研究了更为分化的新闻媒介制度,高等教育制度在不同国家之间发展速度与程度上的差异,等等 。此外,斯梅尔塞则提出了“受挫的分化”(blunted dicerentiation)这一概念,用来揭示某种分化过程受到阻碍这种现象。他举例说,在英国,允许工人子女进正规的初级学校这一制度当初就曾因资本家和工人家长从维持“家庭经济”角度出发极力反对而受到严重挫折,等等
。此外,斯梅尔塞则提出了“受挫的分化”(blunted dicerentiation)这一概念,用来揭示某种分化过程受到阻碍这种现象。他举例说,在英国,允许工人子女进正规的初级学校这一制度当初就曾因资本家和工人家长从维持“家庭经济”角度出发极力反对而受到严重挫折,等等 。上述所有这些研究都对传统分化理论对分化的描述作出了重要补充。
。上述所有这些研究都对传统分化理论对分化的描述作出了重要补充。
二、超越对分化的纯系统论或进化论的解释
许多新功能主义者都指出,分化不能被理解为对结构性压力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一种反应,也不能被理解为系统内在固有的趋于更高效率的一种冲动,单纯的结构性压力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千篇一律地产生出高水平的社会分化 。社会变迁过程是由具体的社会群体来完成的,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具体群体的动员,群体关系格局以及群体内外冲突等因素的影响。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系》等著作中,对具体社会群体的动员、群体联盟的形式、群体对相关资源的控制以及群体冲突给予了相当的注意,将它们视为影响制度变迁过程的重要因素。艾森斯塔德还提出了“制度提倡者”(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的概念
。社会变迁过程是由具体的社会群体来完成的,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具体群体的动员,群体关系格局以及群体内外冲突等因素的影响。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系》等著作中,对具体社会群体的动员、群体联盟的形式、群体对相关资源的控制以及群体冲突给予了相当的注意,将它们视为影响制度变迁过程的重要因素。艾森斯塔德还提出了“制度提倡者”(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的概念 ,认为结构变迁的发生以及它采取的特殊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制度提倡者的活动所型塑。他进一步指出,这些制度提倡者并非“系统适应性”的无私的代理人。相反,他们对新结构的倡导部分地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驱使。然而他们也不能简单地将自己的意愿施加于较大社区之上。他们的特殊利益尤其为他们同盟者的利益、为他们所求以使其制度性要求合法化的文化形式、为作为其活动条件的周围社会环境、为他们对手的冲突性的利益所限制。对制度分化的一种充分解释必须考察这些因素。在较晚近的一篇文章中,艾森斯塔德又提出要重视精英群体对结构变迁的影响
,认为结构变迁的发生以及它采取的特殊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制度提倡者的活动所型塑。他进一步指出,这些制度提倡者并非“系统适应性”的无私的代理人。相反,他们对新结构的倡导部分地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驱使。然而他们也不能简单地将自己的意愿施加于较大社区之上。他们的特殊利益尤其为他们同盟者的利益、为他们所求以使其制度性要求合法化的文化形式、为作为其活动条件的周围社会环境、为他们对手的冲突性的利益所限制。对制度分化的一种充分解释必须考察这些因素。在较晚近的一篇文章中,艾森斯塔德又提出要重视精英群体对结构变迁的影响 。他认为精英活动是制度化的一个相对自主的方面,精英的活动与眼光以及精英之间的冲突对结构分化的形式与方向等有直接的影响。艾森斯塔德提出的这些概念与思想被斯梅尔塞、柯罗米、罗德斯等人进一步加以拓展。他们不仅以许多不同的案例研究验证了上述思想,而且还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新概念、新思想来补充它。如柯罗米在“制度提倡者”概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制度追随者”、“制度保守者”、“制度迁就者”等概念,认为结构分化直接受到这些群体之间相对力量及冲突的形式与过程的影响,等等
。他认为精英活动是制度化的一个相对自主的方面,精英的活动与眼光以及精英之间的冲突对结构分化的形式与方向等有直接的影响。艾森斯塔德提出的这些概念与思想被斯梅尔塞、柯罗米、罗德斯等人进一步加以拓展。他们不仅以许多不同的案例研究验证了上述思想,而且还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新概念、新思想来补充它。如柯罗米在“制度提倡者”概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制度追随者”、“制度保守者”、“制度迁就者”等概念,认为结构分化直接受到这些群体之间相对力量及冲突的形式与过程的影响,等等 。新功能主义者们试图以这种突出利益冲突在结构变迁过程中之作用的“利益模式”(interest model)来补充过去那种单纯强调结构压力导致变迁的“压力—分化”(strain-produces-differerfiation)模式,或“问题—解决”模式(problem-solving model)
。新功能主义者们试图以这种突出利益冲突在结构变迁过程中之作用的“利益模式”(interest model)来补充过去那种单纯强调结构压力导致变迁的“压力—分化”(strain-produces-differerfiation)模式,或“问题—解决”模式(problem-solving model) ,把个人与群体的能动作用、利益与冲突等因素导入分化理论,使分化理论更具现实解释力。
,把个人与群体的能动作用、利益与冲突等因素导入分化理论,使分化理论更具现实解释力。
三、增加社会分化结果的可能性范围
效率的增长与整合能力的提高是传统分化理论认定的两个主要社会进化结果。新功能主义者们则普遍认为,效率的增长与整合程度的提高只是理论上与经验上的可能性而非分化过程的必然产物,他们拒斥分化会自动增加系统效率与整合程度的观点,指出社会分化的结果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亚历山大提出功能性的分化和相对自主的亚系统及精英的出现会促使现代社会冲突数量的增加,但同时也会缩小冲突的范围
。亚历山大提出功能性的分化和相对自主的亚系统及精英的出现会促使现代社会冲突数量的增加,但同时也会缩小冲突的范围 。斯梅尔塞等人指出分化出来的制度为各群体提供了重新组合的新的利益基础
。斯梅尔塞等人指出分化出来的制度为各群体提供了重新组合的新的利益基础 。罗德斯则指出分化结构中那些保守团体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将一种僵化的、固定不变的因素导入了社会系统,从而削弱了系统对变化了的环境的适应性
。罗德斯则指出分化结构中那些保守团体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将一种僵化的、固定不变的因素导入了社会系统,从而削弱了系统对变化了的环境的适应性 。苏里(D.Sciulli)认为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存在着趋向专制权力和官僚权威主义的危险,但也存在着以程序规范为前提的“社团结构”来有效控制这种趋势的可能性
。苏里(D.Sciulli)认为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存在着趋向专制权力和官僚权威主义的危险,但也存在着以程序规范为前提的“社团结构”来有效控制这种趋势的可能性 。芒奇则对“整合”的概念进行了补充,指出各个分化的亚系统之间除了以帕森斯曾经提出的“相互渗透”的形式发生相互关系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不同的关系形式,如相互调节、相互孤立、单方面的控制等等
。芒奇则对“整合”的概念进行了补充,指出各个分化的亚系统之间除了以帕森斯曾经提出的“相互渗透”的形式发生相互关系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不同的关系形式,如相互调节、相互孤立、单方面的控制等等 。所有这些对分化之后果的重新探讨都对传统的分化理论形成了这样或那样的补充或修正,提高了分化理论在预见分化结果方面的灵活性。
。所有这些对分化之后果的重新探讨都对传统的分化理论形成了这样或那样的补充或修正,提高了分化理论在预见分化结果方面的灵活性。
四、改变原初理论“价值无涉”的形象
针对功能主义的反对者关于功能主义及其分化理论内在地具有保守性这种诘难,许多新功能主义者都试图刷新功能主义及分化理论的意识形态形象。例如,亚历山大承认社会科学中的每一种理论视角都包含着一个意识形态的部分,它自动地来源于该理论视角的预设、理论模式和经验命题 ;他和博里库德(F.Bourricaud)等人认为功能主义的意识形态承诺不是社会稳定和系统均衡,而是个体自主性,任何威胁到个体自由的制度安排都应该受到批判或攻击
;他和博里库德(F.Bourricaud)等人认为功能主义的意识形态承诺不是社会稳定和系统均衡,而是个体自主性,任何威胁到个体自由的制度安排都应该受到批判或攻击 。苏里和古尔德(M.Gould)对现代社会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批判态度。苏里认为现代社会一方面受到政治与经济寡头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受到被绥靖的消极公民的威胁,提出要用自治性的社区或社团来重构现代社会
。苏里和古尔德(M.Gould)对现代社会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批判态度。苏里认为现代社会一方面受到政治与经济寡头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受到被绥靖的消极公民的威胁,提出要用自治性的社区或社团来重构现代社会 ;古尔德则强调现代社会产生的压力只有通过财产关系的转变才可能被缓解,等等
;古尔德则强调现代社会产生的压力只有通过财产关系的转变才可能被缓解,等等 。这些用新的批判性眼光重新审视社会进化的现代阶段的种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都促使功能主义向左转”
。这些用新的批判性眼光重新审视社会进化的现代阶段的种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都促使功能主义向左转” ,使功能主义呈现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色彩。
,使功能主义呈现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色彩。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努力,新功能主义者们的确使功能主义的社会变迁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使之对社会变迁的形式、过程、动力、结果等都能做出更好的描述和解释,从而增加了它的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