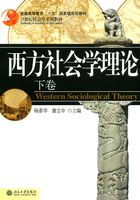
第五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过程理论
包括帕森斯在内,所有的传统功能主义社会学家们都侧重于把社会运行过程当作一个合意的、协调的、均衡的过程来加以考察。自然,帕森斯在这方面所做的分析也是最为精致的。按照这种分析,整个社会过程在理想状态下可以描述为构成社会系统的全体成员在某种共同认可的社会意识、社会规范以及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下,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致力于满足各种社会功能需要的过程。这种描述所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无数孤立的个体行动是如何构造出这种合意的、协调的、均衡的总体过程的?帕森斯归纳出两个基本的社会机制来回答这个问题。一是个人的“社会化”。在“社会化”过程中,社会努力将它对个人在能力、规范、价值等方面的期待与要求灌输到个人的人格结构中去,个人则将社会对它的种种要求努力内化到自己的人格结构中来。正是通过“社会化”过程,个人才转变成为一个与社会期待相符合的“社会角色”。社会化了的集体成员,将共同按照社会的需要来进行分工合作、创设规章制度、协调各自的行动,使社会合作得以顺利进行。但“社会化”过程并不是完全的、充分的。个人的需求、意志、能力不可能充分地与社会的期待相吻合,任何时候总有部分“差异行为”出现,因此必须有另一方面的机制来处理这类行为,以确保社会合作的成功。这就是社会控制机制。通过社会控制机制,差异行为或是得到部分的预防,或是在出现后得到部分地减弱和各式各样的矫正,差异行为者的“正常”行为功能得到恢复,社会合作的正常秩序便得以维持。传统功能主义对社会过程的这种描述,凸显了社会过程的整体性质、合意性质和规范性质,忽视或掩饰了社会过程中个体行动的能动性质、利益性质以及社会过程的冲突性。这种社会过程观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符号互动论、冲突论、交换论等其他社会学理论流派的批评。为了弥补帕森斯主义社会过程观的缺陷,新功能主义者们吸取了符号互动论、交换论与冲突论者的批评意见,对帕森斯的社会过程观进行了新的阐释。
例如,亚历山大在区分行动与行动环境的基础上,指出社会运行不单纯是行动者(社会成员)被动地服从社会安排,机械地履行社会角色的过程。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人格系统只是作为行动的外部环境进入到个体行动过程当中去,它并不对个体行动形成一种唯一性的约束,而是为个体行动划定一个可能的行动空间。行动者作为行动的主体,随时随地都在对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行解释和谋划,制定出自己的行动策略,作出自己的行动选择。因此,在社会的结构性约束与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环境只是为行动者的行动限定了一个变化和选择的范围,而行动者所作出的行动选择反过来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因此,社会过程是行动者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相互构造的过程。不过,就亚历山大而言,在行动者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他更强调的是社会环境对行动的约束作用,认为这种约束是微观的个体行动秩序形成的基础,宏观社会环境正是通过其对个体行动所施加的一定的约束,确保了整个宏观社会过程的有序运行 。
。
芒奇也从行动与结构相互作用的角度,对社会过程作了新的阐释。与亚历山大相比,他的分析显得更为精细。以他对行动领域的四种基本类型的分类模型为基础,芒奇提出了微观互动的四种基本类型:市场交换、政治决策、社区互动和理性讨论。这四种微观的互动过程构成整个社会过程的基础。芒奇指出,这些微观互动过程具有两方面的性质:一方面它们必须以一定的前提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而这些前提无论从时间上和空间上看都是处于它们的互动情景之外的,是在它们之前和在它们之外的人们互动的产物,“就这些前提与结果超越了互动情境而言,它们具有给定的和宏观结构的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微观的行动与互动必须以宏观的社会结构作为自己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者的约束。另一方面,每一次微观互动的结果也对未来进一步的互动过程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对未来将要进行的互动过程而言,现在正在进行的互动过程的结果也是外在的、既定的,因而也是它们借以发生和受其约束的宏观结构前提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微观的行动与互动也影响着或改变着它们借以发生和受其约束的宏观结构前提。可见,微观互动与作为其前提的宏观结构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对正在进行互动的行动实体来说宏观结构是给定的、在互动情境中不可改变的,因为它们是在这个互动情境之外的时间中与空间中创造出来的。与此同时。由于互动对宏观结构所施加的影响,它们又是可以被正在进行互动的行动实体所改变的;但这种变化仅仅只是对未来的互动而不是对当前考虑之中的互动情境有效”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微观的行动与互动必须以宏观的社会结构作为自己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者的约束。另一方面,每一次微观互动的结果也对未来进一步的互动过程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对未来将要进行的互动过程而言,现在正在进行的互动过程的结果也是外在的、既定的,因而也是它们借以发生和受其约束的宏观结构前提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微观的行动与互动也影响着或改变着它们借以发生和受其约束的宏观结构前提。可见,微观互动与作为其前提的宏观结构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对正在进行互动的行动实体来说宏观结构是给定的、在互动情境中不可改变的,因为它们是在这个互动情境之外的时间中与空间中创造出来的。与此同时。由于互动对宏观结构所施加的影响,它们又是可以被正在进行互动的行动实体所改变的;但这种变化仅仅只是对未来的互动而不是对当前考虑之中的互动情境有效” 。芒奇还对上述各种互动类型和其宏观结构性前提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具体的说明。他指出,每种互动类型都有一些与它们各自本身的特征相联系的前提与结果,同时也都有一些与其他互动类型的特征相联系的前提与结果。例如,在市场交换中,自我和他人从一个既定的货币收入、商品和劳务方面的分配格局出发,这个分配格局是先前许多其他交换者交换活动的结果;与此同时,这一次交换的结果又会影响到货币收入、商品和劳务在未来的分配格局。此外,交换也要以结构性的规范作为自己的一种前提,这种结构性规范不是由参与这次交换的交换者创造,而是由一大批在时间和空间上处于这次交换情境之外的交换参与者组成的交换者共同体所创造的。与此同时,就结构性规范会被交换者根据他们在交换中获得的实际经验而加以改变而言,交换也影响着结构性规范的变化。成文的契约法是交换的政治性前提,它也会根据交换者的经历被加以改变。普遍的价值观则是交换的文化前提,它们为契约形式的合法化设立了一个框架,而交换也对普遍价值观不断产生动态的影响,因为它不断地使这些价值观面临一些新的必须“文化地”加以回答的问题。同样,政治决策也是一方面以先前政治决策活动中所形成的一些成文法,以在时空上处于这次政治决策情境之外的许多行动者组成的社区创造的规范性规则,以普遍性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前提,另一方面又对这些成文法、规范性规则和普遍价值观产生深远的影响。社区互动和理性讨论也都是如此。芒奇还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微观互动与宏观结构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交错的,因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也是异常复杂的,远不是上面所说的那么简单。通过这些分析,芒奇表明了社会过程并不单纯只是行动者被动地履行宏观结构性安排的过程,而是行动者的微观互动与宏观结构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创造的过程。
。芒奇还对上述各种互动类型和其宏观结构性前提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具体的说明。他指出,每种互动类型都有一些与它们各自本身的特征相联系的前提与结果,同时也都有一些与其他互动类型的特征相联系的前提与结果。例如,在市场交换中,自我和他人从一个既定的货币收入、商品和劳务方面的分配格局出发,这个分配格局是先前许多其他交换者交换活动的结果;与此同时,这一次交换的结果又会影响到货币收入、商品和劳务在未来的分配格局。此外,交换也要以结构性的规范作为自己的一种前提,这种结构性规范不是由参与这次交换的交换者创造,而是由一大批在时间和空间上处于这次交换情境之外的交换参与者组成的交换者共同体所创造的。与此同时,就结构性规范会被交换者根据他们在交换中获得的实际经验而加以改变而言,交换也影响着结构性规范的变化。成文的契约法是交换的政治性前提,它也会根据交换者的经历被加以改变。普遍的价值观则是交换的文化前提,它们为契约形式的合法化设立了一个框架,而交换也对普遍价值观不断产生动态的影响,因为它不断地使这些价值观面临一些新的必须“文化地”加以回答的问题。同样,政治决策也是一方面以先前政治决策活动中所形成的一些成文法,以在时空上处于这次政治决策情境之外的许多行动者组成的社区创造的规范性规则,以普遍性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前提,另一方面又对这些成文法、规范性规则和普遍价值观产生深远的影响。社区互动和理性讨论也都是如此。芒奇还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微观互动与宏观结构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交错的,因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也是异常复杂的,远不是上面所说的那么简单。通过这些分析,芒奇表明了社会过程并不单纯只是行动者被动地履行宏观结构性安排的过程,而是行动者的微观互动与宏观结构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创造的过程。
与其对帕森斯结构理论的修正相适应,艾森斯塔德也把冲突论的有关思想引进功能主义的社会过程观,用冲突论的有关思想来对帕森斯的社会过程观进行修正。与帕森斯对社会过程的描述不同,艾森斯塔德把社会过程描述成为一个充满利益冲突的过程。在早期的两篇文章《制度化与社会变迁》和《社会变迁、分化与进化》中,艾森斯塔德认为,在一定的背景条件上(如人口增长、资源稀缺等),社会必然产生冲突与失序。社会通过发展出一些更为特殊的结构来回应这些冲突,由此产生了社会分化,整个社会系统也由此分化为—些相互联系的子系统。然而社会对冲突与失序的这种回应并没有也不可能终结社会冲突与失序。因为结构分化既是功能性的,又是利益性的,社会的不同功能部分同时也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在承担社会功能的同时也在追逐着自身的利益,在资源稀缺等背景条件未变的情况下,这种不同群体对各自利益的追逐必然会持续不断地产生群体间的冲突。艾森斯塔德进一步解释道,社会分化最先总是由一些在主要制度领域内占据“策略性角色”位置的人所倡导的。这些人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和发展他们各自领域的潜在可能性。“新的分化结构仅仅是通过按自己的利益来行动的那些群体确立起来的,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通过社会变迁而产生的制度反过来又会产生它自己的新问题” 。为了维持他们已确立的社会结构,那些倡导者集团将做出持续的努力从不同的群体与个体那里调动各种资源,来维护系统的各种价值、符号和规范的合法性。这些努力将对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地位产生明显的影响,引起他们之间权力平衡和他们对既定制度体系及其价值观的态度取向上的持续变化。由于分化是由特殊的群体来实施的,以及由于新的分化的制度的维持依赖于只能从其他群体那里获取的各种资源,社会的分化过程必然内在地引起群体冲突。“任何社会或集体中的大多数群体,在他们对任何此类制度的态度方面都倾向于显示出一定的自主性,并且,在他们向新的系统提供所需资源的意愿的程度和能力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或变化”
。为了维持他们已确立的社会结构,那些倡导者集团将做出持续的努力从不同的群体与个体那里调动各种资源,来维护系统的各种价值、符号和规范的合法性。这些努力将对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地位产生明显的影响,引起他们之间权力平衡和他们对既定制度体系及其价值观的态度取向上的持续变化。由于分化是由特殊的群体来实施的,以及由于新的分化的制度的维持依赖于只能从其他群体那里获取的各种资源,社会的分化过程必然内在地引起群体冲突。“任何社会或集体中的大多数群体,在他们对任何此类制度的态度方面都倾向于显示出一定的自主性,并且,在他们向新的系统提供所需资源的意愿的程度和能力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或变化” 。其中,最不愿意或最无能力满足系统资源需求的那个群体,将发展出对新的统治群体的要求更具对抗性的组织与意识形态,他们与统治群体间的冲突也将最为激烈。
。其中,最不愿意或最无能力满足系统资源需求的那个群体,将发展出对新的统治群体的要求更具对抗性的组织与意识形态,他们与统治群体间的冲突也将最为激烈。
在后来与他人合著的《社会学的形式》一书中,艾森斯塔德又提出社会冲突与失序是内在地植根于人类的先天本性之中的。他认为,人类的基因符码(genetic code)是开放的,它必须通过符号形式和技术性组织来被“强制性地加以结构化”(be arbitrarilystructured)。然而这种结构化的行动本身又产生了一种对于变迁和失序的开放性。因为符号形式与工具性技术进步的细节是无法完全确定的,它们只能在具体的互动中逐步显露;这种开放性反过来又产生了有关人类目标与活动的自由性与可变性、有关人格冲动的控制、有关贵重资源的稀缺性以及有关人类生命本身的持续性等方面的巨大的焦虑。这些焦虑一方面通过人类的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等各种文化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引起了有组织的努力和冲突,破坏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感。为了寻求和发展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感,社会发展出一些组织性的框架和机制来规范劳动分工,一些象征性符码来结构化社会情景。但是,在社会发展出来的意义性合约、符码和用来规范劳动分工的组织框架、机制之间并不存在着完美的适应。这些为促进信任而发展出来的结构之间的紧张反过来又会危及信任的维持。这种紧张产生了新的象征性符码。这些新的象征性符码将人们对劳动分工的不适应感转换成强调失序和组织性专权的批判性意识形态。由于这些批判性符码必须在每一场合具体地加以定义,不同传播群体之间的差别便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些差别反过来又加剧了上述紧张。在这种令人不满的情景下,各行动者群体便纷纷抢占接近关键性资源和位置的通道,颁布支持他们自己的立场与利益的规则。对每一群体之外的社会成员来说,这些规则常常显得是专横的、强制的和不公正的,群体冲突由此接踵而来。作为对这类冲突的反应,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中都产生了详细的、不仅用于控制符号互动也用于控制接近贵重资源机会的各种基础性规则。那些基础性规则构成了社会的“深层结构”,它们是通过不同类型的“事业家”或发明者之间有意或无意的联盟建立和维持起来的,那些联盟试图控制对社会结构的确定具有关键意义的符号和资源的流动。然而,艾森斯塔德指出,尽管这些基础性规则是用来处理社会秩序问题的,但“它并没有解决它们;它仅仅将它们转换到一个新的水平上。” 因此,社会冲突将始终存在。
因此,社会冲突将始终存在。
总而言之,社会运行并非是一个合意的、协调的、均衡的过程。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社会冲突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运行也不是行动者单纯被动地服从“社会安排”的过程,而是在既定的结构框架内自主地追逐自身利益与目标的过程。社会冲突与失序,正是导源于行动者之间对自身利益与目标的这种自主追求。艾森斯塔德通过将冲突论思想引入到功能主义框架中来,对功能主义社会过程观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