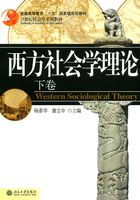
第七节 简要评论:新功能主义的成就与局限
以上我们从社会行动理论、社会结构理论、社会过程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四个方面对西方新功能主义社会学一些最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作了一个简略的介绍。新功能主义是一个较庞大的学术群体,按亚历山大的说法,它的应和者遍及欧美许多国家,仅亚历山大和柯罗米等人编撰的有关文献上有名可查者即达数十人。由于资料与精力所限,本文未能将他们一一涉及(甚至包括其中的名家如卢曼、阿切尔等)。本文仅对西方新功能主义社会学给出了一个“举例说明”似的描述,期望通过这种描述使读者能对西方新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获得一个虽非完备但却较为深入、具体的印象。
根据以上描述,我们应该承认,就将功能主义理论朝着一个新的、更具“多维性质”的综合性理论方向推进而言,新功能主义者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亚历山大等人对行动理论的重新阐述中,从罗西、芒奇和艾森斯塔德等人对结构理论的补充与修正中,从芒奇和艾森斯培德等人对社会过程的重新刻画中,以及从柯罗米、斯梅尔塞等人对分化理论所做的种种推进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到新功能主义的“新”意所在。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新功能主义者们的努力,功能主义社会学的理论空间确实被大大地拓展了。关于行动过程是一个以理解为基础的意义建构过程以及行动过程是一个策略性的理性选择过程的思想,关于社会结构不是一种完全外在于个体行动的既定存在而是一种不断被人们的行动所建构的未定存在以及社会结构是一种利益一冲突结构的思想,关于社会过程是人们能动地创造自己的生活世界以及社会过程是一个充满了群体冲突过程的思想,关于社会变迁并不必然导源于结构性的功能迫力而是导源于群体冲突以及社会变迁的结构并不一定是系统适应力与整合度的提高的思想等等,现在似乎已不再是符号互动论、社会现象学、本土方法学、社会交换论以及社会冲突论等“反”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专利了。它们与前面所述功能主义的那些传统思想(强调社会的系统性质、关注结构与行动之间的连接、关注社会整合、关于人格—文化—社会三分的假设、把分化看成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强调概念和理论的相对独立性等)似乎可以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功能主义社会学不再以一种只重宏观不重微观、只重合意不重冲突、只重客观不重主观的形象呈现于世,而是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态度将所有这些对立的要素都包容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当中。功能主义社会学的确获得了一种崭新的面目。
新功能主义思潮的出现也改变了人们对帕森斯理论的不良印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帕森斯思潮中,帕森斯也遭受了历史上许多伟大思想家曾经遭受过的那种待遇,被像一条“死狗”一样抛在一边。“今天谁还读帕森斯?”一位西方学者模仿帕森斯的语气如此地嘲讽帕森斯。对帕森斯的理论进行批评一度成为每个初入社会学界的学者表明自己“成熟”的必经仪式。然而,新功能主义者们的努力改变了帕森斯在人们当中的形象,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帕森斯理论的兴趣。莫泽利斯在考察了新功能主义的成就之后得出结论说:功能主义的复兴表明,“帕森斯学派的理论建构具有严密性和深刻性,社会学理论的当前任务应该不是对它进行全盘否定,而应该是对它的缺陷和问题进行全面调整” 。而按照亚历山大的描述,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新功能主义运动出现之前,很多当今世界比较有影响的思想家都相信,目前已经完全可以撇开帕森斯的观点来考察上述(社会学的各种)论题了。而到了现在,只有极少数人还坚持这一观点。‘帕森斯’已经从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力量,变成了一种被许多重要的社会理论家质疑其真正意义的对象,变成了一种当代知识生活中的‘经典’形象”。“帕森斯贡献的重要性现在已经得到人们的承认,尽管他的理论体系不再那么受到欢迎。……在当代生活中,作为一个理论形象,他的学术声誉不免会有升有降;但作为一个历史形象,在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的发展史上,他的地位在目前看来是确定无疑的,其著作和生平也已日益成为社会学史的重要资料”
。而按照亚历山大的描述,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新功能主义运动出现之前,很多当今世界比较有影响的思想家都相信,目前已经完全可以撇开帕森斯的观点来考察上述(社会学的各种)论题了。而到了现在,只有极少数人还坚持这一观点。‘帕森斯’已经从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力量,变成了一种被许多重要的社会理论家质疑其真正意义的对象,变成了一种当代知识生活中的‘经典’形象”。“帕森斯贡献的重要性现在已经得到人们的承认,尽管他的理论体系不再那么受到欢迎。……在当代生活中,作为一个理论形象,他的学术声誉不免会有升有降;但作为一个历史形象,在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的发展史上,他的地位在目前看来是确定无疑的,其著作和生平也已日益成为社会学史的重要资料” 。
。
由于以上原因,新功能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一度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和注意。连那些曾经激进反对帕森斯思想的人都承认新功能主义的出现是功能主义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成功回归”,是“对当代理论的重大冲击”。另一位学者则认为,“帕森斯学派的复兴是80年代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然而,90年代末期以来,新功能主义运动却似乎声浪渐息,有从人们的视野或注意焦点中逐渐远去的趋势,究其原因,恐怕有如下几点:
。然而,90年代末期以来,新功能主义运动却似乎声浪渐息,有从人们的视野或注意焦点中逐渐远去的趋势,究其原因,恐怕有如下几点:
首先,尽管新功能主义者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影响,但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目前已取得的成就与他们期望达到或者应该达到的境界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阅读新功能主义者们(尤其是亚历山大、柯罗米等骨干分子)的著作,在获得启发之余,也能感受到许多不足之处。如尽管他们大都承认结构与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在许多实质性的具体讨论中,他们仍更多地侧重于探讨如何重新解释结构对行动的约束作用,而对于人们如何通过行动来建构社会这一点仍然缺乏足够的说明;尽管引入了利益关系与群体冲突的概念,但它们仍然被认作是功能关系和系统运作过程的伴生物,而不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关系与过程,尽管承认分化理论的种种不足,但分化仍被视作是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式,等等。这些缺陷都不能不使新功能主义者们的理论视野受到很大的限制,阻碍他们更好地去吸取其他理论学派的思想精华,从而使人们对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始终抱有一种陈旧之感,对其理论创新的潜力产生怀疑。
其次,新功能主义运动始终未能产生一部代表性的作品。亚历山大和柯罗米是新功能主义运动最自觉、最主要的倡导者,但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柯罗米都未能拿出一部像样的著作来对新功能主义的理论主张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具体的讨论和阐发。亚历山大曾经写过一部四卷本的《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但按他自己的说法,那还是他产生“新功能主义”的理论构想之前的著作,虽然可以看作是新功能主义理论运动的前兆,但其基本内容、研究思路和理论主张却与后来的新功能主义构想并非完全一致,因而难以被视为新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代表作。在提出新功能主义的理论构想之后,亚历山大和柯罗米对新功能主义理论的论述多是通过一些零散的论文来展开的,篇幅的简短、论题的随机性都使得人们仅仅通过这些论文难以对新功能主义理论获得一种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细微的理解和把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新功能主义对人们吸引力的可持续性。
再次,是其内涵过于模糊、外延过于宽泛。按理,新功能主义应该是一种“新”的“功能主义”,它既应该超越传统的“功能主义”,使之具有“新”意,但又应该坚持“功能主义”的一些基本内核(譬如前述亚历山大所宣称的“功能主义”的那六个基本特征),使之仍然能够被称之为是“功能主义”。这既是人们在听到或看到“新功能主义”这个名词时在心里可能产生的期待,也是亚历山大在80年代中期提出“新功能主义”一词时对其含义所做的实际阐释。然而,与此相背的是,在许多场合,亚历山大等人又对“新功能主义”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作了过于宽泛的解说。按照亚历山大在许多场合的说法,似乎只要在论题或观点上直接或间接吸取了帕森斯功能主义理论成分的理论就都可以列入“新功能主义”的行列。因此,像卢曼、贝克、哈贝马斯乃至吉登斯这样一些在他人看来与“功能主义”传统大相径庭的理论家都被亚历山大一手拉进“新功能主义”的阵营。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乎是壮大了“新功能主义”的声势,但实际上却模糊了人们对新功能主义的理解。既然当今社会理论界的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家都可以在这样或那样的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新功能主义者,那“新功能主义”这个概念又还有什么用处呢?这也不能不说是“新功能主义”的口号对人们的吸引力逐渐削弱的原因之一。
其实,作为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历史最悠久的知识传统之一,无论“功能主义”有多少局限,都不失为一种具有持续存在价值的理论框架。它确实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其他理论框架所不能提供的理论视角,让我们看到从其他视角出发所看不到的一些世界景观,从而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提供了其他理论框架所不能提供的资源和参照系统。正如一些学者们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的不是完全、彻底地放弃这种传统,而是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空间的转换,随着我们的知识视野的扩大,而不断地对其进行调整、修正,推动其发展。在这一方面,“新功能主义”的确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构想。在坚持这种构想的基础上,努力克服上述缺陷,应当是新功能主义社会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学的未来发展只能有新功能主义这一条道路。说新功能主义应该是社会学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一条道路,这并不意味也不妨碍社会学还可以有千千万万条其他的发展道路。我们既不应该轻易地放弃一条曾经有过多年积累的社会学发展思路,也不应该简单地用其中的一条来取代其他的思路。因为,正如瑞泽尔早就指出过的那样,社会学本就是一门多范式的学科,多样性乃是社会科学的本来特色。
参考文献
Alexander, J.,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4Vo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1983.
Alexander, J.(ed.), Neo-Functionalism, Sage,1985.
Alexander, J., Giesen B., Munch R., Smelser N.(eds.), The Micro-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Alexander, J.,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Alexander, J.and Colomy P., “Newfunctionalism Today:Reconstructing a Theoretocal Tradition”, in Ritzer G.(ed.), 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 the New Synthes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Alexander, J.and Colomy P.(ed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Alexander, J., Neofunctionlism and After.Blackwell,1998.
Bourricaud, F., The Sociology of Talcott Pars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81.
Colomy, P.(ed.), Neofunctionalist Sociology, Elgar publishing,1990.
Eisenstadt, S.and Curelaru M., The Forms of Sociology: Paradigms and Crises, Wiley,1976.
Eisenstadt, S.,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9.
Eisenstade, S., “Social change, differentiation and 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Mouzelis, N., Socilogical Theory:What Went Wrong? Diagnoses and Remedies, Routledge,1995.
Munch, R.,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Action theoryII:The continuity of develop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7.
Ritzer, G.(ed.), 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the New Synthes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沈原、张旅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罗西:《对四个功能范式的辩证再解释》, 《国外社会学》1991年第3期。
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亚历山大:《论新功能主义》, 《国外社会学》1991年第3期,第3页。
亚历山大:《新功能主义及其后》,彭牧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