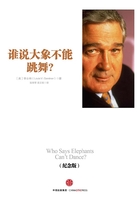
第五章
“热烈拥抱”计划
4月底,我们召开了一次“公司管理委员会”,与会者就是3月份参加宣布我当选CEO那次会议的原班人马——公司的50名最高层主管。
在会上,我告诉他们我在这3周中的体验和心得。一开始我就说,我看到了许多积极的因素在继续,特别是在研究、产品开发以及许多人所表现出来的积极能干的态度等方面。
然而,也存在着问题,比如:
·失去了客户的信任,另外,产品质量问题也引起了一些客户的极大不满,他们对此进行了指责。
·盲目地追求公司分立,经理们热衷于说“给我一个助理”。
·跨部门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市场部负责人和零售部负责人之间关系十分紧张。
·绩效评估系统混乱且存在着争议,这会给一线的零售带来严重问题。
·五花八门的联合没有任何意义。
我宣布了“热烈拥抱”计划。50名高级经理中的每个人都要在未来的3个月内,至少拜访公司5个最大客户中的一个。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倾听,要显示出我们对客户的关注并恰当地采取行动。他们的直接下属(大约有200名高级经理)也要做相同的事。在每一次的“热烈拥抱”式拜访活动中,我要求他们能够递交一份1~2页的报告,这些报告可以直接交给我,也可以交给那些可以直接解决客户问题的人。我希望这些拜访活动能够减少客户的成见,即在别人看来我们公司总是难以接触。我还清楚地指出,拜访活动也没有理由仅仅停留于公司5个最大的客户。显然,这是一次外界对我们公司信任度的大检阅。
“热烈拥抱”计划也是IBM公司文化改革的第一步,强调我们将从外至内建设自己的公司,并使公司的所有事情都以客户为导向。对我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它不仅带来了轰动效应,而且当人们意识到我的确是认真阅读了每一份报告时,他们的行动和反应速度相应也快多了。
撤销管理委员会
还是4月底那一天的下午,又召开了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IBM内部称其为“MC”会议)。要知道,在管理委员会谋得一职,是每一个IBM高级经理梦寐以求的事情,也是事业上的顶峰。当我加盟IBM公司时,该委员会有6名成员,其中就有埃克斯和库恩勒。管理委员会每周开1~2次会,通常是正规的全天会议,还有大量的会议提案。公司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在该委员会上提交讨论。
该委员会中有些成员是最近才任命的,但就在我来公司后的第一次管理委员会上,我告诉他们一个让他们感到十分沮丧的决定,那就是公司今后不再设管理委员会这一机构。因为我希望自己能够更有决策权,而不是由管理委员会来更多地行使公司决策权。尽管直到数月以后,管理委员会才正式撤销,但作为IBM数十年的主导性管理决策机制,它的使命早于1993年3月寿终正寝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管理委员会的兴起和消亡就是IBM公司整个刻板的等级制度兴起与消亡的写照。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奇怪的管理公司的方式——明显的中央集权式管理,这种管理方式最终会导致权责不分。管理委员会是IBM出了名的有争议体制的组成部分,在这一体制中,各个事业部的建议权会与具有同样权限的公司管理人员的建议权产生分歧和对抗。当我一想到技术产业的复杂性以及重要业务和产品决策所包含的风险性等因素,我就会理解这种体制,或许在创立之初它确实是一个精彩创新。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流逝,IBM的员工已经学会了如何开发新的管理机制以加快自己的议事日程。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真正有争议的机制已经明显地让位于事先安排好的共识性管理体制。公司的管理人员不是要提出有争议的建议,而是要使公司在最大范围内达成共识。于是,人们就期盼管理委员会能够提供一个包含众多可能性的、直截了当的建议。在通常情况下,管理委员会的使命就是一个形式上的盖戳批准行为。
我没有花太多的时间来仔细挖掘IBM的公司发展史,但我早就听说过行政助理制度就是这种官僚主义管理机制的产物。
会晤业内专家
上任后的最初几周,除了做其他事以外,我还安排了多次与电脑和电信行业各位领导之间面对面的会谈。其中有TCI公司的约翰·马龙、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英特尔公司的安迪·格鲁夫、NCR公司的查克·埃克斯雷以及莲花软件公司的吉姆·曼齐。这些会晤对我帮助很大,他们对IBM的看法或许还没有他们对行业的洞察力对我更有启发。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我的许多来访者都是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来的。
与安迪·格鲁夫的会晤算是其中最直接进入主题的一次了。格鲁夫以他可爱的直截了当的方式坦率地告诉我,IBM在微处理器行业没有前途,所以IBM应该停止用PowerPC芯片与英特尔公司竞争。只有停止这场竞争,两家公司之间的关系才不至于越来越紧张。我感谢格鲁夫的忠告,但对于他关于IBM应该怎样做的建议还是无法真正理解。于是,我只好把格鲁夫的忠告囫囵吞枣地放在了心里。
从内容来看,与比尔·盖茨的会晤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根本上说他只是给我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那就是:IBM应该坚持做自己的主机业务,而不是个人电脑业务。与盖茨会晤的一些偶然事件,则要比与他的交谈更有纪念意义。
我和盖茨是在5月26日上午8点见面的,地点是在纽约麦迪逊大街。很巧,我也打算在同一天稍后的时候在那里会晤莲花软件公司负责人吉姆·曼齐。所以,IBM的安全保卫人员糊涂了,他们不认识盖茨,所以称他为“曼齐先生”,并给了他一张曼齐的通行证。当盖茨到达第40层楼的时候,他对此感到不高兴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进行了一次有益的讨论(让我失望的是,我并没有在他身上看到著名的摇摆动作)。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晤之后所发生的事——我和盖茨以及我们的办公室人员都同意,在我们会晤之前和之后都不向外界公开。然而,媒体还是在盖茨离开IBM办公大楼两个小时之后知道了我们这次会晤的所有细节。到了晚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盖茨的通行证被IBM的安全保卫人员弄混了。盖茨显然不想说明在同一天我还要会晤曼齐,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弄混事件似乎更进一步证明了IBM——或许是郭士纳在技能上的缺乏。
快速失血的财务
4月底,我们公布了公司第一季度的经营业绩,但这并不是让人高兴的业绩:收入下降了7%,毛利润也从50%下降到39.5%,降幅超过10%,公司的税前亏损是4亿美元,而在上年同期IBM的税前利润接近10亿美元。
5月底,我看到了4月份的业绩,这些数据中没有一点夸张的成分。4月份,公司的利润又下滑了4亿美元,这样公司在前4个月中就一共亏损8亿美元。同期,IBM的主机业务销售量也下降了43%。其他一些大宗业务,包括软件业务、维修业务、融资业务以及大多与主机业务销售情况紧密相关的业务,也都因此而销售量大降。公司唯一增长的业务领域是服务,但其市场份额却相对较小,因而利润也不大。员工总数也略有下降:从年初的30.2万人下降到4月底的29.8万人。包括特定应用软件事业部和半导体事业部在内的好几个事业部都举步维艰。
几乎与这些糟糕的经营业绩一样糟糕的还有,尽管公司可以在财务总额上有所增加,但公司内部预算和财务管理制度还是漏洞百出。公司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两三个预算体系,因为IBM矩形组织结构中每一个部门(也就是各个地域的事业部和产品事业部)都坚持要有自己的预算,结果导致公司没有一个统一和固定的预算,财务分配当然也就不断地出现争议和变化,可想而知要想做出统一的决策是相当困难的。
如果听任主机业务以及众多与主机相关业务如此继续下滑,那么IBM的前景就十分危险了。我们正以最大的努力运用融资租赁的方式来支撑资产负债表的平衡,但是还必须采取其他一些方法来稳定公司的经营状况。
与媒体的早期接触
公司与媒体之间只有一个非常短暂的蜜月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情况一般都是这样。我们不可能整天在媒体的监督和报道之下对一家病入膏肓的公司动大手术,扭转乾坤,并且有太多的工作要去处理,不可能都将每天所取得的进步形成书面报道,再说这些进步也是花上数月和数年才能够取得,而不是数小时或数天就能够取得的。美联社的一名记者曾希望跟踪报道我在IBM第一天工作的全部经过,《今日美国》也说要为我每天的工作制定一个“每天进展表”。我对他们说:“不了,谢谢。我们需要大量安静的时间,仔细考虑我们下一步的任务。”这对于一个习惯于每日报道IBM问题的记者来说,是一个无情的拒绝。
我加盟IBM的第一天,就把我的公关经理戴维·卡里斯带了过来。卡里斯已经跟随我多年,20世纪80年代他回到美国运通公司。在我看来,他是美国最优秀的公关经理,也是IBM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职业公关人员,并从事着高级公关工作。几十年来,公关和销售一起被认为是公司的高级工作。
卡里斯加盟IBM的时候,公司的公关工作简直是一团糟。IBM也有一些天才的员工,但公关部门的员工大多初衷良好却缺乏培训。即便他们都是受过系统培训的职业公关人员,也无法在像1993年的IBM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公司中大展身手。特别是IBM的高级经理们也认为,公司唯一真正的问题就是每天来自媒体的轰炸。他们觉得,如果媒体对IBM的正面报道更多一点,那么公司就会转而赢利,而且方方面面也都会重新走向正轨。
尽管我最明显的优先性任务就是与IBM的客户和员工进行会晤和交谈,但我也不得不抽出一点时间来与媒体打交道,所以我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最初的几个月,在每个特定的日子里,都会有来自主要媒体超过65宗对我进行采访的请求。如果再加上来自地方性报纸以及电脑行业报纸的采访要求,那就有数百宗了。如果再加上来自全世界的采访要求,那简直不计其数。
我不知道自己在有限的时间里该如何处理这些事务,因为我已经答应接受《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财富》、《今日美国》以及《金融时报》的单独采访,但媒体的反应却告诉我——而且是不断地、大声地告诉我,这还远远不够。
我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但我知道自己的时间并不多。来自媒体、华尔街以及股东等各方面的压力在不断增大。我们已经做了不少事,我将不得不公开,而且是尽快公开我扭转IBM颓势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