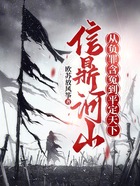
第1章 意外之祸
梁朝,昭鼎十七年。
秋风凛冽,黑云密布,雨滴淅淅沥沥地砸落在坞堡,将外墙上的血污洇成一道道暗红的溪流。似乎一场滂沱暴雨,随时都要到来。
彭信拖着疲乏的身躯走在城墙上,雨水顺着眉毛滑落脸颊,流过人的嘴唇。汗液混杂着血浆,让脸上的雨滴变得腥咸。但是已经饥渴疲惫的彭信心里却恨不得雨再下得大一些,湿润他已经干裂的嘴唇,温润他嘶喊沙哑的咽喉。
由于战事紧急,他已经快有两天未曾合眼了,现在的他只希望趁着敌人刚刚退去,赶紧收拾好战场残局,吃一口饭,美美地睡上一觉。
眼前,两个兵士正吃力地将敌方尸体推下城墙。有的人正在将倒下的旗帜扶起;有的人正在收拢地上散落的兵刃和器械;更惨一些的身受创伤,缩在门楼廊角避开雨水,默默地处理并不时发出呻吟。
“赶紧把火器搬回到仓库去,选干燥的地方阴干。弹丸和火药找中间的空地放,不要跟上次一样堆在潮湿可能反水的角落。给两口城防炮推到门楼下,盖上蓑衣,暴雨马上就要来了。”彭信向几个笨手笨脚搬东西的士兵下达指示,然后转向身旁的小校:
“趁着郧贼退去,让大家收拾完赶紧休息,吩咐拨些细粮犒劳一下大家,账房有异议你就说是我的命令。另外,角楼和门楼的哨兵不要下,挑些精神体力还好的士兵,让他们在楼内保持警戒。不要因为天气不好,就疏忽了侦查防卫。如果看到对面大营有任何动向,随时向我报告。”
校尉赶忙应允,匆匆走开去打理这些事务。彭信则继续在城上巡视,雨比刚才还大了些,不时有水滴顺着他的甲胄边缘流入衣袖。秋雨寒冷,让人不由自主地打颤。
他借着巡视活动着身体,绕了半圈,从北墙渐渐走到南墙。这个堡垒本就不大,驻扎了约五百余人,绕堡走完一周也花不了多少时间。这是阳津城北方前出据点几个中的一个。
水北为阳,渡口为津。城池在宏江以北,此处水阔浪平,可渡大船,故曰阳津。因泸河在阳津以北入宏江,涒河在南方又与宏江汇流,此地三面临水,乃是郩州治所,大梁的江北门户,兵家必争之地。
郧国此次南征,矛头直指阳津。要入阳津,必要拔除北面几个要塞。所以月余间,此堡累经数战。幸得大营援护,这座堡垒尚未被破。也许是担心天气不好,敌军没有在此死围,趁着暴雨未下,撤去了包围部队,全部回缩到北面的主营寨去了。
彭信正在南城墙上检查这一侧的损伤,忽见城下远处一匹马急速驶来。天阴有雨看不真切,只听得风鼓战袍马蹄嘀嗒。待到行得近处,才看清是一员信使着梁军装扮,手持令旗,疾行而来。到了城前却不下马,大声向城上喝到:“有武都统将令,速命彭信将军接收。”
城上看得真切,此人衣着旗信,皆是货真价实。然而平日传令官乃是熟人,自己早已认得,这个信使却看着眼生。彭信见他在城下喝问赶忙应答:
“末将正是彭信,未知武都统有何事令您至此。”
“信令是机密,十万火急,赶紧速开城门,需要当面说。”信使略显傲慢和不耐烦。
彭信却不恼怒,忙令人取下门栓,放开绞索,下到城口。
这信使下了马也不往里走,只是大剌剌地站在城门洞前,静待彭信亲自走过去。见彭信下城,便将令旗展开在胸口,颇有刻意展示的意味。
他待彭信走过来,探身凑到彭信耳侧,俯首低语:“武都统有机密军情,怕信使被劫,机密外泄,所以不能写作文字。现在命令彭将军赶紧备马,随我回大营,当面交代军令。”
“我当然知道军情机密,然而这边刚打退郧贼的进攻,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再来袭击,而且之前武都统就令我坚守此堡不得退却。此时让我离开,回营授命,将军没有书面命令吗?”
“正式命令当然是有的。”信使将手揣入怀中,摸出一个黄绿色竹筒,只有小指粗细,轻轻一磕,倒出一张纸卷,递到彭信身前。
彭信伸手接过,展开纸卷,上面仅有一行字:“命彭信速回大营复命,有军情面授”,只看字体,确实是武都统手笔。整行字的结尾处盖了一枚小章,却不是官印,而是将军的私印,印泥和墨迹都还未干。
彭信见了令旗和信件,扭头便对守卫的士兵说:“快去牵我的马来,再叫刘大和阿成也备两匹马,随我速速往大营。”
刚待转身,却被信使伸臂拦住:“武都统特别嘱咐了,要彭将军你一人前往,何况现在城外并不安定,经常发现郧军的小股部队,人多反而容易引起注意。将军这里并未部署骑兵,除了你的战马,剩下的也就几匹拉货驽马。真遇到敌情我们可以策马快跑,他们脚程慢倒是走不脱。而且军情紧急,我也被命令赶紧回去复命,还是将军只你一人速度骑马跟我同去吧。”
见信使说的在理,彭信也没有坚持。不一刻,已有士兵将他的马牵了过来,刚才城上听命的校尉听说彭信要离营,也跟着士兵一起过来。彭信便对其叮嘱一番,各种城防细节注意事项安排妥帖。待交代完毕,才放下心来,随着信使一起出城。
军队的大营是位于阳津外城北,距前线垒营五六里路的距离,要纵马抵达也不过一晌的功夫。整个坞堡群,大营与阳津城环环相扣,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防线。
彭信与信使二人骑马在道路上并肩而驰,一路却不见人烟,此季本应收割的田地一眼望去杂草丛生,已不知多久没有耕作过。策马疾驰一阵,才渐渐在远处看到营垒的轮廓和巡视的士兵。
信使先到了营门前进行禀报。营门拒马一侧的哨兵身着蓑衣,像拄拐一样支着长枪,全身缩成一团。他只拿眼角瞟了一眼信使,下巴朝门里一努,便又蜷起身来不动了,恨不得多说一句话身上的热气就会散掉。
随着信使进了大营内,彭信拐了几步便被带入了一个偏帐内。营帐不大,简单搭了个布帐用木头中间撑住,地上什么也没铺只是已经夯平的浮土,除去帐头摆了桌椅,就再无他物,似是进行候客或简单伏案点算的场所。虽然简陋,但好在干爽避雨。
“容我先行禀告武都统,彭将军在此稍坐。”信使只打个招呼,便自退了出去。
信使刚走没有一会,又有两个军士扮相的人转入帐内。一人托着脸盆毛巾,一人手抱一套便服。二人进帐,还未等彭信开口,便先声夺人道:
“今日除了武都统,谭知州也在营,带甲面见上官不合仪制,还请彭将军在此除甲更衣,再随我等前去大帐。”
却说武都统本名武忠赐,乃是御前都统制、郩州节度使,授统北方五州诸军事,以阳津为大营抵御郧国的进攻,所以大家都称之为武都统。谭知州本名谭邬,是郩州知州,虽品俸均在武都统之下,但朝廷以文抑武,文官地位总是高半分。今日不知为何,当地文官主官亲临大营。
“本朝立朝以来,也未闻武将拜见当地父母官需要除甲更衣的说法,何况现在在军营里,战事紧急,谭大人架子是不是太大了。”
“我们都只是奉命行事,听说今天不光谭大人在,还有京城使臣带圣旨前来,还请彭将军赶紧更衣,不要让小的难做。”军士只是举着脸盆,继续催促。
京城还有人来,战事难道要有大的变化?彭信闻之,心中一凛,不敢怠慢,忙在军士帮助下除去盔甲佩刀,又拿毛巾将脸反复擦洗。换上了二人带来的衣服,才随着二人前往大帐。
大帐前士兵冒雨而立。他们甲胄明亮,刀枪整齐,成两行鱼贯排列,没有半点倦意。彭信在引领下从兵士间走至大帐,随行的两人并未跟从,只以手示意彭信入内便退去。彭信便掀开门帘,独自径入。
大帐中央开阔,绕中庭摆了三张案几。谭知州着官服坐在上首正中。左侧坐的是武都统,身着皂甲,腰悬佩剑,身若磐岩,重髯面阔,虽然已两鬓花白,但身上却有无尽的英武之气。右侧坐的是个年过四旬的中年人,身披大氅,内着锦袍,却是个生面孔。他面白腮瘦,短眉翘鼻,双眼虽然不大,却乌黑发亮,不停地打量着彭信。
彭信迈入帐中,见几人已在座等候,准备向大人行礼。刚一欠身,便听身后门帘响动。猛觉背后一沉,双臂突然被大手钳住,向后拧去。瞬时两臂无比疼痛,仿佛肩肘要被掰断一般。紧接着,整个人身体向前倾倒而去,面门重重磕在大帐地板上,额头湿黏温热,牙根也一阵酸疼,血液的腥涩之感在口腔蔓延开来。还没尝试起身,就感觉到身后有人拿棍子插住自己的双腿,让人动弹不得。
此时,锦衣中年人缓缓站起,走到彭信身前,厉声说道:“彭家败类,竟敢勾结叛党,意图造反。今天你家父子兄弟均已伏诛,你可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