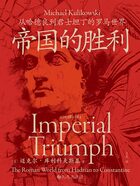
第1章
哈德良统治的早期
哈德良统治的开头并不顺利。人们相信,或者可能假装相信,哈德良登基要归功于图拉真的遗孀普罗提娜,而不是出于已故皇帝的意愿。的确,他受到普罗提娜的青睐,而且许多元老认为,相比普罗提娜的这个受保护人,他们自己更适合做图拉真的继承者。其他人选的名字四处流传,而当哈德良马上放弃了图拉真那令人瞩目的征服战争时,他显得更加糟糕。从后世的眼光看来,我们明白这些战争已经注定失败,就连图拉真也会不得不放弃。但图拉真已经去世,并被人铭记,而哈德良还活着,且不那么受人爱戴,因此成了被指责的对象。不过,最恶劣的还是谋杀。有人企图发动政变,或者政变的传言被当了真。无论如何,在哈德良从东方回到罗马前,有4名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现在拥有着帝国最高指挥权的高级元老被杀。哈德良总是宣称处决他们并非他的责任,但没有人相信他。与前任相比,他显得非常差劲:图拉真在其统治期间,即便在面对真正阴谋的时候,也仅仅流放了两名元老,没有处决他们中的任何一人。
哈德良过了一段时间才回到罗马,他入城时没有得到热烈的欢迎。平民骚动不安——谋杀4名前执政官元老是个丑闻。哈德良不得不分发大笔钱财来安抚他们。他还免除了个人借贷者和城市拖欠皇帝本人的小金库[fiscus,不同于国库,后者被称为“公共财库”(aerarium publicum),有时也被称为“萨图尔努斯财库”(aerarium Saturni),因为它坐落在萨图尔努斯神庙附近]的债务。他在图拉真广场上大张旗鼓地公开焚毁了税收记录,希望赢得一些民心。他还试图取悦元老院,但这并不容易。他发誓自己没有下令杀害那4名元老,并立下了那时已经成为传统的誓言,即自己将不会惩罚任何元老,除非得到了元老院本身的投票。但元老的怀疑无法扭转,哈德良从来都不受欢迎。
他把自己的养父封神,将图拉真的遗骨埋在其为纪念在多瑙河的胜利而竖立的石柱的基部。这根石柱高100英尺①,装饰着600英尺长的螺旋形饰带,描绘了皇帝发起的达契亚战争中的场景。石柱至今仍然矗立在以皇帝名字命名的广场上,是罗马帝国权力的象征性纪念物之一。哈德良的孝行实际上很不寻常,在某个层面上还是渎神的。图拉真广场坐落在罗马城的传统神圣边界,即所谓的城界(pomerium)内,那里禁止出现墓葬。即便是皇帝也被埋在位于城界之外的战神校场(Campus Martius)上的奥古斯都陵中。哈德良此举,就像他做的许多事一样,会触怒那些本就心怀不满的人,无论他的本意可能多好。
哈德良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稳固自己的皇位。他罢免了图拉真的两名近卫军长官(praetorian prefect,帝国政府的主要行政官员和近卫军的指挥官)之一,还接受了另一名长官的辞呈,这位上了年纪的前百夫长忠心耿耿,但似乎不愿意为哈德良效命(百夫长是罗马军团中非委任军官,通常在退伍时会获得骑士身份,让他们可以担任帝国行政体系中为骑士等级保留的各种职务,比如近卫军长官)。哈德良任命另一名前百夫长马尔基乌斯·图尔波(Marcius Turbo)来取代图拉真的近卫军长官。此人很早就在军中与哈德良相识,当时正忙于在达契亚和默西亚行省肃清多瑙河前线。第二名新的近卫军长官塞普提基乌斯·克拉鲁斯(Septicius Clarus)是骑士等级出身,我们对他的了解主要是小普林尼把自己的书信集题献给他。最后,哈德良还任命了新的司信官(ab epistulis)——负责起草皇帝的书信和回复的骑士等级官员——以《罗马十二帝王传》闻名的苏维托尼乌斯·特朗基鲁斯(Suetonius Tranquillus)。《罗马十二帝王传》是从尤利乌斯·恺撒(被错误地认为是第一位皇帝)到图密善的一系列皇帝的八卦传记,长久以来都是拉丁文学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其他任命显示了在弗拉维乌斯王朝时期就已经蒸蒸日上的殖民市精英现在如何成了政府的主导力量。哈德良的罗马城长官(该职务不同于近卫军长官,是负责罗马城本身的日常运行的)是来自西班牙的元老马尔库斯·阿尼乌斯·维鲁斯(Marcus Annius Verus)。此人的政治生涯可以追溯到韦斯巴芗时期,他后来成了罗马历史上最后几位3次担任执政官的平民之一,这项特权越来越多地成了皇帝及其继承者的专属。这位阿尼乌斯·维鲁斯的女儿阿尼娅·加莱里娅·福斯蒂娜(Annia Galeria Faustina)嫁给了一位来自纳尔波高卢的内毛苏斯[Nemausus,今尼姆(Nîmes)]的元老:这位名字拗口的元老叫作提图斯·奥勒留·弗尔乌斯·博伊翁尼乌斯·阿里乌斯·安敦尼(T. Aurelius Fulvus Boionius Arrius Antoninus),他后来将成为我们称之为安敦尼·庇护的皇帝(138—161年在位)。121年,当老阿尼乌斯·维鲁斯第二次担任执政官时,他的孙子,另一个马尔库斯·阿尼乌斯·维鲁斯出生了;这个马尔库斯·阿尼乌斯·维鲁斯日后将成为马可·奥勒留皇帝(161—180年在位)。这些相互交织的家族将主导公元2世纪的王朝政治。
和哈德良一样,阿尼乌斯·维鲁斯和阿里乌斯·安敦尼不同于图拉真这样的老一辈人。虽然他们有殖民市血统,在家族故乡仍然有亲戚和门客,但他们本身是意大利的孩子,在罗马长大,很少回到祖籍行省。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也与意大利精英关系密切:同样得到哈德良任命的哈特里乌斯·奈波斯(Haterius Nepos)属于骑士等级,祖上来自翁布里亚的自治市。他在114—117年,当亚美尼亚还是罗马行省时短暂担任过那里的总督;现在他迅速得到提拔,担任了一系列职务,最终成为埃及行省总督,这是一个专为骑士等级精心挑选的职位,总是由皇帝最信赖的人担任。哈德良的军团指挥官们既有图拉真时期的旧部也有新面孔:新皇帝对权力的掌控并不稳固,因此在对延续性的尊重和对自己的可靠支持者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了。
有时,这种对安全的追求会带来创新。一条新近发现的铭文表明,在犹太战争结束后,哈德良创设了一个非常军事辖区,将犹地亚和阿拉伯的罗马军团置于同一名军团指挥官的掌握下。此举旨在震慑犹太本土,防止它跟着犹太流亡者反叛,尽管就像我们很快会看到的,这种做法失败了。皇帝本人在罗马城度过了他统治的前三年,尽管他更喜欢东方,乃至更喜欢旅行本身:公元2世纪时,人们对皇帝的期待是他应该以元老中的元老自居,即便他不受欢迎,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到其他地方去。哈德良尽其所能地熬过了这段必需的与元老院的“会面时间”,此后他转向帝国的更广大疆域,尽可能地远离罗马。
121年,他前往高卢和日耳曼,留下图尔波和阿尼乌斯·维鲁斯照管人民和元老院。图拉真的遗孀普罗提娜也留了下来,过着退隐的生活。119年,图拉真的外甥女,同时也是哈德良岳母的马提蒂娅去世,和之前她的母亲马尔基亚娜一样被封神。她的女儿萨宾娜现在已经是奥古斯塔,与皇帝同行:她和哈德良都非常不喜欢对方,但他担心如果任由拥有像她这样权威的女性留在罗马,可能会成为阴谋的焦点。即便在旅途中和严格的监督下,萨宾娜仍然会引起丈夫的怀疑:122年年末,因为神秘地与皇后有了不明互动,近卫军长官塞普提基乌斯·克拉鲁斯和司信官苏维托尼乌斯等人突然被解职。也许的确有阴谋,或者萨宾娜有什么欠考虑的言行(哈德良只爱年轻男子),但事实上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萨宾娜仍然是皇帝同行者的一员,但没有人接替克拉鲁斯。这意味着从哈德良回到罗马伊始就任职的马尔基乌斯·图尔波直到他统治的最后都会是唯一的近卫军长官。
哈德良在旅途中度过了十年以上的时间,巡视了辽阔帝国的各个行省。121年或122年,他造访了上多瑙河的莱提亚(Raetia)和诺里库姆(Noricum)行省——今瑞士、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的一部分——还视察了后者的帝国矿场,为了纪念他来访而铸造的钱币显示了这一点。他给这两个行省带来荣耀,将几个诺里库姆的社区升格为自治市(municipia)——这是一种法律地位,按照罗马法拥有特别的权利——并为总督治所维鲁努姆[Virunum,今克拉根福特(Klagenfurt)附近]建造了一座新剧场,还把位于莱提亚的温德里库姆的奥古斯都市[Augusta Vindelicum,今奥格斯堡(Augsburg)]升格为自治市。从那里,他又把目光投向不列颠,并可能沿着莱茵河而下,一直来到下日耳曼尼亚(Germania Inferior,因为位于上日耳曼尼亚的下游而得名)的阿格里帕殖民市[Colonia Agrippinensis,今科隆(Cologne)]。哈德良似乎有意开发了下日耳曼尼亚的欠发达地区,包括今天弗兰德斯的一部分,而且通格罗鲁姆城[civitas Tungrorum,今通厄伦(Tongeren)]也是在那时被升格为自治市的。下日耳曼尼亚的总督普拉托里乌斯·奈波斯(Platorius Nepos)在122年随哈德良前往不列颠,并最终成为皇帝在那里的特使,这个行省将长期作为帝国的重要军事辖区之一。
图拉真死后第二年,不列颠发生了叛乱或边境骚乱,需要一位高级将领坐镇。122年,普拉托里乌斯·奈波斯带着一整个军团,即来自下日耳曼尼亚的卡斯特拉维泰拉[Castra Vetera,今克桑滕(Xanten),位于莱茵河与利珀河的交汇处附近]的“胜利者”第六军团,以及其他数千名来自西班牙的军团士兵,和皇帝的队伍一起前往不列颠。不列颠在很长时间里都将是帝国最棘手和收入最低的行省之一,122年皇帝来访的主要结果是修建哈德良长城的计划,这也许是罗马城之外最著名的罗马古迹了。皇帝在这个岛上度过了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于122—123年冬天回到大陆。
抵达高卢后,哈德良又动身前往他家族的故乡西班牙,现在那里获得了皇帝正式来访的荣耀。哈德良经由纳尔波高卢南岸前往那里,在图拉真的遗孀、他自己的养母普罗提娜的家乡内毛苏斯为她竖立了纪念碑。在阿普塔[Apta,今阿普特(Apt)],他为自己死在那里的心爱猎马波吕斯忒涅斯(Borysthenes)立碑,并亲自写了一首并不高明的诗装点其坟墓。哈德良从纳尔波高卢出发,沿着海边的道路前往广阔的近西班牙行省(Hispania Citerior)的首府塔拉科[Tarraco,今塔拉戈纳(Tarragona)],在那里过冬,一直待到123年年后很久。当年春天,他在弗拉维乌斯王朝建立的塔拉科广场和神庙举行了盛大的行省罗马公民大会(conventus)。随后,他又造访了行省的北部,包括“双子”第七军团驻扎的要塞(莱昂)和阿斯图里卡奥古斯都(Asturica Augusta,今阿斯托尔加[Astorga])等西北部的行政中心。我们不知道他是否造访了其他两个西班牙行省——贝提卡和卢西塔尼亚(Lusitania),但他有意回避了自己的祖籍地意大利卡。不过,他为该城投入了大笔资金:在他的统治期间,意大利卡几乎建立了全新的公共中心。同样是在西班牙期间,哈德良还在行省公民中征兵加入军团。他想要补充帕提亚前线的兵源,因为在124年,他计划向东进军。

地图8 小亚细亚
我们并不真正清楚哈德良东进的路线,但可以确定他亲自与帕提亚举行了和谈,在该国的王位争夺中向一方提供了象征性的支持,阻止了两大帝国发生真正的冲突。他在124年余下的时间里巡视了各个东方行省。我们知道他穿越了多山的卡帕多奇亚,一直来到黑海边的大港特拉佩佐斯[Trapezus,今特拉布宗(Trabzon)],下令对港口做了大规模修缮。他还去了比提尼亚与本都(Bithynia et Pontus)这个二合一行省东半部分的本都地区,然后回到比提尼亚,在尼科美底亚[Nicomedia,今伊兹米特(Izmit)]停留。尽管无法证实,但哈德良可能在这里遇到了安提诺乌斯,这个乡下少年是来自比提尼亚的克劳狄奥波利斯(Claudiopolis)城外的希腊人,后来成了他的挚爱和流传至今的浪漫传奇的主角。
从比提尼亚出发,皇帝的队伍来到了普罗庞提斯海(Propontis)的欧洲一侧,很可能造访了色雷斯行省的首府佩林托斯(Perinthus),然后回到亚细亚行省。库奇科斯(Cyzicus)是哈德良的第一站,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站,因为他授予那里大量的荣耀,重启了几百年前由帕加马国王阿塔鲁斯(Attalus)开展的神庙修建工程,并赐给该城“庙所”(neokoros)的地位,即作为行省的皇帝崇拜中心之一。成为庙所,拥有被封神的皇帝和皇族的神庙,这在亚细亚行省乃至小亚细亚半岛的更广大地区是令人垂涎的地位。随着罗马帝国的统治激发了当地的希腊城市在城市生活、情感和自豪感方面的复兴,帕加马、以弗所、士麦那和萨迪斯等古城都已经享有了这种地位。比库奇科斯获得更多荣耀的只有行省首府帕加马,以及哈德良的旅伴,智术师和哲学家波列蒙(Polemon)的家乡士麦那,因为哈德良两次授予它们庙所的地位,这是一项极高的特权。难怪他开始获得“爱希腊者”之名,罗马一些较为严苛的拉丁元老认为这并不完全体面。不过,哈德良的亚细亚之行鼓励了许多出身高贵、已经是罗马公民并拥有骑士等级财富的希腊人寻求加入元老院。
124年8月,哈德良在以弗所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经由罗得岛前往希腊本土。他年轻时到过雅典,但那已经是10年之前,当时他第一次对一切希腊事物表现出毫不掩饰的热情。现在,他作为罗马世界的统治者到来,首要目标是参加厄琉息斯秘仪。这是古代阿提卡重要的宗教仪式,在夏末或初秋进行,长久以来都让罗马的希腊文化崇拜者着迷。哈德良还与老熟人们重新见面,比如年轻的赫罗德斯·阿提库斯(Herodes Atticus)。赫罗德斯的父亲是雅典最富有的人之一克劳狄乌斯·阿提库斯(Claudius Atticus),他在10年前哈德良造访雅典期间曾经照顾过后者,而赫罗德斯本人将成为2世纪中期阿提卡的重要恩主。现在,哈德良特批他加入罗马元老院,身为“密友”财务官(quaestor inter amicos)。“特批”(adlectio,字面义是“读进名单”)是皇帝授予宠臣荣耀的方式,让他们不必担任积累资历的低级职务就能成为具有特定正式等级的元老。赫罗德斯现在享有和真正财务官同等的级别,他还是皇帝的“密友”(amici),这是一个虽然半官方,但罕见且令人垂涎的头衔。
宫廷驻扎在阿提卡期间,哈德良巡视了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的许多地方,修复和新建了一些建筑。他想象自己是在恢复希腊的古老荣耀,但更多是在当地的风貌中留下新的帝国印记。重新燃起对古典希腊文化的荣光的兴趣是2世纪的特点,哈德良爱希腊的热情只是这种范围大得多的现象的一个表现:正是在这个时期,博学的古物学家,来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的保萨尼亚斯(Pausanias)开始撰写篇幅宏大的《希腊游记》,它至今仍是该地区的地理和历史不可或缺的文献。而哈德良回到雅典时正好赶上125年的酒神节赛会,他扮演了赛会指挥(agonothetes)的角色。然后,他造访了德尔斐和科林斯,两地分别作为阿波罗的神谕所和尤利乌斯·恺撒在内战胜利后为老兵们建立的重要殖民市而闻名。接着,哈德良沿着科林斯湾向北航行,来到了尼科波利斯(Nicopolis),那里是为纪念奥古斯都最终击败他的对手马克·安东尼而建立的定居点。随后,他来到伊庇鲁斯的底拉西乌姆[Dyrrachium,今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Durrës)],从那里起航回到意大利的布伦迪西乌姆[Brundisium,今布林迪西(Brindisi)]。他离开罗马已经4年了。
哈德良在希腊和小亚细亚的逗留告诉我们许多罗马皇帝必须扮演的公共角色的情况。比如,在此期间,他接受了被选为雅典的执政官(archon),这一非常具体的爱希腊举动表达了对古老希腊传统(在许多个世纪以来都是空洞的记忆)的象征性认同。哈德良的队伍漫步穿行于他们的城市,仿佛在进行一次历史之旅,此举赢得了希腊精英们的爱戴。在亚该亚和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行省,哈德良重演和重写了希腊历史的不同版本。作为数不胜数的例子中的一个,他在伊利昂(特洛伊战争的战场,位于小亚细亚)重建了所谓的埃阿斯墓,还在阿卡迪亚的斯基洛斯(Scillus)吊唁了伟大的雅典将军色诺芬的墓。在另一次东方之行中,他修缮了位于弗里吉亚(Phrygia)北部内陆深处的梅里萨(Melissa)的阿尔喀比亚德墓。在阿卡迪亚的曼提内亚(Mantineia),他为忒拜人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竖立了纪念碑,此人在去世400年后仍然作为希腊人的解放者而受到铭记。在雅典,他开启的营建项目在当地人和帝国的资助下将持续整个世纪。哈德良对该城的重要个人贡献是下令完成了奥林匹亚宙斯的宏伟神庙: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了这项工程,但直到哈德良的时代仍未完工。在德尔斐,他的爱希腊举动更加激进:他废除了管理德尔斐神谕所的近邻同盟大会(Amphictyonic Council)被奥古斯都和尼禄皇帝强加的寡头统治。哈德良将其成员扩大,以达成他想象中的原始和最初的状态,即希腊世界还是由一系列独立的小城邦所组成时那样。这是对希腊古代历史的幻想,但迎合了他的听众。130年,当他第一次来到埃及时,伴随而来的是另一波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举动,首先是修复了培琉喜阿姆(Pelusium)的庞培墓,然后从那里沿着尼罗河继续行进。
哈德良的爱希腊举动标志着罗马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有趣的阶段。在他的统治期间,失望的对手和其他不喜欢他的人仍然可能嘲笑哈德良软弱,不像罗马人,而是个“希腊崽”(Graeculus)。他们的行为让人想起了一种非常古老的恐惧和嫉妒,可以追溯到共和时代。希腊文化毋庸赘言地要比罗马土生土长的传统古老和先进得多,对一切希腊事物摆出鄙视的姿态起到了自卫功能。比如,打猎是一种典型的希腊式消遣,罗马贵族曾经认为这有损他们的尊严。类似的还有浪漫或带有感情的同性恋:人们不会在意罗马男性是否偏爱与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但认为其中不该有浪漫成分,否则就令人尴尬。这两种文化在许多方面早就达成了一致,希腊人的艺术和文学品位在希腊语和拉丁语背景下往往都会占据主导,但在公元2世纪初,骑马打猎或者把对年轻男性的爱情色化仍然可能让一个人成为“希腊崽”:旧的刻板印象仍然蜇人。哈德良的漫长统治大大消减了这种毒性,并非因为拉丁元老们认同他本人或他的爱希腊热情,而是因为他对希腊贵族的青睐让他们更多地加入了罗马元老院的上层,跻身于元老院所象征的日益跨民族的精英行列中。
①1英尺约合30.48厘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