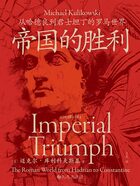
导言
在我们的故事开始前大约1000年,罗马最初是意大利中部台伯河畔的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子。多个世纪以来,它与邻居们基本上没有区别,但到了公元前4世纪,它开始咄咄逼人地向半岛的其他地方扩张。它的领导者是每年由公民群体选出的行政长官,投票经过了加权,以确保有钱有势者在投票结果中拥有决定性的话语权。这种制度在某些方面真正代表了公民群体的愿望,几乎每一年,公民军队都会在两位当选执政官的率领下出征,与敌人交战。征服活动在公元前3世纪加速,100年后,罗马已经成了地中海世界毋庸置疑的超级大国。不过,与此同时,共和政制开始崩溃,因为相互敌对的将领们试图让自己和亲信们垄断权力。几十年的内战摧毁了共和国,到了公元前1世纪末,共和政制这台运转不灵的机器被奥古斯都的一人统治所取代,他是罗马的第一位皇帝。
奥古斯都——他从公元前27年开始叫这个名字——原名屋大维,是第一个试图独自统治罗马的共和时代军阀尤利乌斯·恺撒的甥孙和养子。恺撒因为这种企图而被刺杀,但共和国没能恢复,公元前44年他遇刺后的战争甚至比之前的更加血腥。等到公元前31年战争结束时,罗马世界已经精疲力竭,它相距遥远的各个行省在三代人的时间里一直是战场。独裁因为替代了更多内乱而受到欢迎,难以驾驭、摇摇欲坠但具有代议性的共和政制永远消失了。奥古斯都比他自己那代人和大部分年轻一代都活得更长;当他去世时,很少有活着的人还记得他统治之前的世界。他把自己标榜为元首,是罗马国家的“第一人”,而不是“国王”或“皇帝”。这种礼貌的谎言安抚了元老们的感情,这些前行政长官群体长久以来都习惯于主宰这个国家。但奥古斯都对实权的完全掌握和他异乎寻常的长寿使其可以改变罗马的统治。
我们将奥古斯都的统治作为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分界线,统治罗马的一边是选出的行政长官,另一边是个人独裁者,但共和国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已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这个共和时代的罗马帝国由罗马人统治,维护意大利的利益,那是绝大部分罗马公民生活的地方;它也维护罗马城的利益,那是世界上到那时为止最大的都市圈。奥古斯都的革命逐渐改变了这点。共和时期对行省的统治(特别是在罗马征服后不久)经常反复无常,而且总是贪得无厌,但是它之后带来了新的基础设施和经济机会。在皇帝的统治下,行省生活变得稳定得多。统治着帝国的土著人口的酋长、市民和贵族可以保留他们在当地的权威,只有两个简单的条件:要保持和平,让罗马公民可以不受侵扰地行事;以及国库必须保持充盈。地方精英,从西欧的酋长到希腊市议会和东部行省的当地王朝,都热情地接受了这笔交易。这些人和他们的臣民学会了取悦罗马总督,许多人还学会了像罗马人一样生活。地方精英对罗马统治和由之而来的和平的热情是对罗马帝国成功的最重要解释。
奥古斯都和他的继承者们不仅对合作给予奖赏,他们还把许多行省人吸纳进了罗马公民的行列。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其他哪个古代国家像帝国时期的罗马这样慷慨地把自己的公民权授予别人。皇帝们没有把公民权局限于帝国的核心,而是将其广泛地授予他人:有时是他们认识的某些大人物;有时是他们垂青的城市;有时是帝国的整个地区。这意味着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都有人拥有着只有罗马公民才享有的法律权利。在帝国内部,无论前往何方,他们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在他们生活或置身之处,无论当地的司法制度如何,他们都享有财产和人身的权利。读者也许会想起使徒保罗的故事,在面临敌视他的犹太当局的审判威胁时,他亮出了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份,于是他的案子被转交给了罗马。罗马公民权的这种“国际性”也许是它最大的价值。
公元1世纪,帝国从由罗马和意大利开发的一系列臣属领地转变成拥有形形色色的文化的行省拼图,它们都服从于罗马皇帝,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行省罗马公民生活在那里。伊比利亚人和高卢人、摩尔人和叙利亚人、色雷斯人和希腊人——他们和其他许多民族可以越来越多地认为自己是罗马人,无论他们还可能是其他什么人。这种自我认同,对自己身为罗马人的意识,在本书涵盖的各个世纪里将变得更加深刻和强烈:行省的罗马人将逐渐在帝国的政治史上成为主角。罗马城中的罗马人也将保持他们的重要性,特别是被称为平民的那部分城市人群。当奥古斯都实行独裁时,平民放弃了他们形式上参与政治和选择领导人的权利,用以交换和平、繁荣和盛大表演: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将其讥讽为用来让人民保持安静的“面包和竞技”。这是平民可以接受的买卖,但对皇帝来说价格不低。教养城市人群不仅意味着金钱,还需要“面对面”。元首要是不兑现对平民的施舍或亲自表达关爱就很可能要面对街头骚乱。
为了让我们的叙述有意义,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帝国元老院、城市平民或行省的罗马公民,还有把所有这些人,以及皇帝和军队纳入帝国统治体制的方式,即它的未成文宪法。这方面被有意安排得含混不清,因为奥古斯都极其不愿意暴露自己统治的真相。元老院的成员曾经统治着共和国及其行省,他们接受了新元首的独裁,不仅因为这种独裁带来了和平,也因为他营造出了尊敬旧有共和原则的得体的表象。元老可以继续担任有着共和时代头衔的职务——财务官、营造官和执政官——尽管无法再通过自由竞争来获得它们,而且他们对帝国的行政仍然至关重要。随着那些经历过共和时代最后几十年的人全部去世,对共和国真实的记忆也随之消逝,精英公民能够接受掩盖一人统治现实的政治表演。他们也能接受世袭继承,这更加令人意外。
共和国的奠基神话是,据说在公元前6世纪,最后一个国王“高傲者”塔克文被推翻,元老院的统治建立了起来,两名当选的行政长官每次只任职一年。在共和时代的政治中,“国王”(rex)一词始终是巨大的侮辱;恺撒遇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相信,他事实上可能称王。不过,虽然奥古斯都在形容他的权力时用词非常谨慎,但他或他的臣民都不避讳世袭继承的现实,仿佛皇帝就是君主。奥古斯都把国家交给了他的养子提比略(公元14—37年在位),从而建立了我们所谓的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得名于他们出身的两个共和时期的氏族。后来这一家族又有3名成员成为提比略的继任者。当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男性在公元68年绝嗣后,帝国出现了短期的内战,直到胜利者弗拉维乌斯·韦斯巴芗(69—79年在位)建立了新的王朝,我们称之为弗拉维乌斯王朝。他的做法证明了帝国可以在没有其创始家族的情况下延续,皇帝也可以在罗马城之外由军队在行省拥立。身为元老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把这一发现称为“帝国的秘密”(arcanum imperii)。这意味着其他家族能够把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独裁延续下去,只要他们能在战场上赢得统治权。
向新王朝的转化使得皇帝权力的真正基础变得更加透明。韦斯巴芗首先在一场东方行省军团的政变中被拥立为皇帝,然后又得到了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的拥戴,让他的登基变得合法。更重要的是,元老院投票授予了韦斯巴芗一揽子曾经由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行使的具体专权。这些权力让元首与国家中的任何其他人都不一样,他以此为基础宣称自己有权行事。这些权力基于共和时代选出的行政长官们在任期内的职权,当它们集于一个人身上时,就使得皇帝拥有了其支配力。其中两种权力最为重要。第一种是代执政官的治权(imperium)。在共和时代,前执政官们会作为代执政官(“代表罗马的行政官行事”)统治行省。代执政官能够执行外交政策、对公民行使法律和司法权、要求公民和非公民服从,但只能在罗马城之外这样做,同样的权力在城内由任期一年的行政官行使。让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代执政官治权与众不同的是它的范围:元首的代执政官治权要高于任何行省总督的,这让他的任何决定在任何他选择采取行动的地方都有了约束力。皇帝的第二种关键权力同样植根于共和国历史。元首拥有永久的保民官权力(tribunicia potestas),这本是共和时代的保民官在罗马城中否决立法和在神圣城界内指挥公民的权力。与执政官的权威一样,共和时代的保民官权力由任期一年的在任保民官行使。然而,在皇帝的统治下,元首之外的任何人均不得拥有保民官权力,而元首是永久拥有的。
当元老院投票授予韦斯巴芗保民官权力时,它肯定了元首拥有某些东西是凭借他的地位,而非他本人,以及奥古斯都的权力可以由某个并非其家族成员的人所持有。但这并不是确定了一个人该如何真正成为皇帝的规则,而只是意味着无论谁成功被认可为皇帝(通过世袭、政变或军事胜利),他都必然能够行使这些权力。然而,模糊之处仍然存在,因为在奥古斯都恢复共和的表象下,人们不可能准确地界定是什么给了罗马皇帝统治权。多个世纪以来,军队、元老院和人民加起来才能让某个人成为皇帝,但它们之间的平衡从来不清晰,从不服从透明或正式的规则。王朝继承成了基准惯例,但从来不是原则:帝国是经常世袭继承的独裁政体,但从来不是世袭的君主制。
我们之前只是顺带提到的军队在皇帝废立中的角色也和元老院或罗马人民同样关键。帝制罗马的军队由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享有不同于公民和行省非公民人群的特权。士兵的忠心需要不断维护,因为归根到底,皇帝独裁统治能否成功就取决于这份忠心:在各种挑战面前保护元首的是军队的忠诚,特别是不列颠、日耳曼、巴尔干、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的行省大军。近卫军的忠诚甚至更为重要,他们是驻扎在罗马的皇帝私人军队,当统治者触怒他们时,他们总是致命的。不过,士兵的需要通常是可预计的,罗马平民的需要也同样如此。
精英——特别是元老——给皇帝造成的麻烦要大得多,因为必须逐一应付他们,而不是将其作为整体来打发。为了治理帝国,皇帝需要依靠元老和骑士组成的寡头集团,前者不仅富有,而且出身高贵,后者则仅仅是些非常富有的人。这个寡头集团中元老的部分能够自我巩固:掌握某些行政长官职务就能获得元老身份,这种身份能为家族的三代人所享有,即便某一代人没能通过担任公职来维持它。一个元老需要至少100万塞斯特斯的财产才能保有元老地位(一个普通市民每年靠大约1000塞斯特斯就能过得很好),而许多元老每年的收入事实上都要超过这个数字。鉴于这种排他性,元老家族天然倾向于组成一个不同于社会其他成员的阶层,即元老等级(ordo senatorius),但它从来不是封闭的,特别是因为它与金钱的关系。
拥有合格净资产的人可以选择寻求担任行政长官,他们会从财务官做起,让他们真正成为元老院的参与成员。这些人属于更大的罗马寡头集团中的第二个群体,也就是骑士等级(ordo equester),它的名字可以追溯到罗马最早期的历史,表示有足够的钱在骑兵服役的人。与需要担任具体的行政长官职务来确认自己地位的元老不同,骑士身份是达到某个最低财产要求(40万塞斯特斯)后自动获得的。人们是身为骑士,而非通过行动成为骑士的,无论他们是否寻求担任公职,都将保持骑士身份。等到下一章中我们的故事开始时,即在哈德良皇帝统治时期,元老和骑士阶层形成了一个国际统治精英集团,每当新的行省人群被授予了罗马公民权时,就会有新的血液注入这个集团中:富有的非公民突然变成了罗马骑士,如果愿意,他们有资格寻求在元老院占据一席之地。渐渐地,寡头集团中骑士的部分获得了主导地位,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公职,并通过它们管理帝国。但关键在于,统治精英集团吸收新成员的灵活性造就了一个基本上稳定的寡头政体,如果没有它,皇帝将完全无法统治。
这就是在下文中为什么我们不能仅限于讨论皇帝或皇帝家族,为什么我们不会回避介绍大量罗马人,以及他们冗长和经常无法记住的名字:这些将军和官僚、财政家和演说家缔造了帝国真实的样子,即便他们可能形象模糊,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仅仅是一长串他们担任的职务和掌握的指挥权。他们的动机常常完全不得而知,更别提他们的性格了。不过,像通俗史学家有时做的那样把他们排除出我们的故事,则会把问题简单化,以至欺骗读者和遮蔽过去的真相:如果不提这些寡头,以及他们复杂的名字和职业生涯,帝国历史就会变成一个只有皇帝及其家族才重要的幻想世界。当然,他们的确重要,但寡头集团也同样重要:独裁政治只有通过寡头和在他们首肯的情况下才能运作。
这是一种相互加强的关系,但我们只了解部分时期的情况,因为我们手上罗马帝国不同时期的史料在数量和质量上差异很大。读者们会很快意识到,我们对某些时期的叙述要远比对另一些时期详细:比如,公元2世纪中期和3世纪末几乎是一片空白;而2世纪末和3世纪初期则记录翔实。除了证据分布不均,还有另一个史料问题:我们现有的几乎所有的叙事性史料都出自元老或者认同自己属于元老阶层的作者之手。因此,他们习惯专注于皇帝个人的性格及其对元老院和罗马本身的生活的影响。卡里古拉和尼禄皇帝对元老们非常凶暴,对元老院也很不好,因此他们是暴君,尽管后者在更广大帝国的许多地方事实上很受欢迎。相反,作为好皇帝的典型,“公民元首”(civilis princeps)效仿奥古斯都,举止得体地扮演元老同侪中的第一人。因此,我们的精英史学传统往往会把每位皇帝归为这种或那种典型。好皇帝韦斯巴芗的小儿子图密善追随了卡里古拉和尼禄的丑恶榜样。韦斯巴芗和图拉真恰如其分地遵循了礼节,因此得到了深情的怀念。尽管我们的叙事性史料专注于帝国的特征,但我们也需要关注其他能够找到的证据,特别是大量石刻铭文,它们让我们得以了解除此之外不为人知的数以千计的个人是如何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生活和事业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几乎总是会发现,皇帝的性格以及寡头集团上层对其统治的感受与整个帝国命运的关系非常之小。
在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统治时期就已经是这样了,在我们的主要叙事开始的117年,即图拉真皇帝去世、他的远亲哈德良登基的那一年,情况更是如此。为了理解哈德良的统治(在许多方面决定了整个公元2世纪的王朝历史),我们需要简述图拉真时期的事件,以及当时在寡头统治集团中占据主导的那类人。皇帝中,韦斯巴芗和他的儿子们是最早的并非出身于罗马城的罗马人,他们来自意大利的自治市。他们是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里被授予罗马公民权的意大利人的后代,家族的一系是元老阶层,另一系是骑士阶层。这是新出现的情况。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祖先是共和国晚期的两个元老大族,这是他们对自身合法性和权力的意识的来源之一。但在这个王朝的统治下,来自罗马城的罗马公民和来自意大利的罗马公民的旧有区别远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后者在帝国政府中占据了越来越高的位置。
韦斯巴芗上台时,有人对他似乎热衷的乡下粗鄙行为嗤之以鼻,但没有人认为他的背景让他不适合统治。在他的弗拉维乌斯王朝统治时期,类似的地区差异消失的现象也出现在了意大利半岛之外。来自西班牙南部和东部,以及高卢南部的殖民市的精英(他们是被安置在自己所征服行省的共和时代老兵的后代)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元老院。尼禄的宫廷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西班牙的元老,而来自纳尔波高卢(Gallia Narbonensis)的罗马元老非常好地融入了意大利贵族,以至于在现有的证据中,想要区分这两个群体变得困难至极。正如意大利精英在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时期得到了更远大和广阔的前途,那些殖民市公民在弗拉维乌斯王朝时期也同样如此。随着弗拉维乌斯王朝的断绝,殖民市精英的这种新的重要性变得清晰。
公元96年9月,韦斯巴芗的小儿子图密善遇刺。这次没有像公元68年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末帝尼禄自杀后那样发生内战。相反,元老院采取了迅速行动,推举马尔库斯·科克尤斯·涅尔瓦(Marcus Cocceius Nerva)为皇帝。此人年纪老迈,受人尊敬但没有孩子,他的职业生涯可以一直追溯到尼禄当政时期。元老院的同僚喜爱和信任他。但他在平民和近卫军中不受欢迎,而且他性情软弱,优柔寡断。边境的军队变得骚动起来。某位高级统帅发动政变(就像让尼禄倒台的那次)和内战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传言四起,但几个月过去了,政变并没有发生。在关起的门背后策划了什么,我们只能想象了,因为事情的真相被仔细地掩盖了,不为后人所知。但公元97年,涅尔瓦看似出人意料地宣布收养了一位强势的将军马尔库斯·乌尔皮乌斯·图拉扬努斯(Marcus Ulpius Traianus),作为养子和皇位的搭档。我们称此人为图拉真,他是个西班牙人,来自贝提卡(Baetica)行省的意大利卡(Italica),这个富饶的南方行省以科尔杜巴[Corduba,今科尔多瓦(Córdoba)]为中心。收养取得了想要的效果,用一位士兵们乐意奉之为皇帝的人安抚了他们。元老院同样感到高兴,图拉真竭尽全力把自己变成“公民元首”的典范,这与图密善截然相反,尽管他事实上曾经非常忠诚地为那位皇帝效命。
涅尔瓦不久就去世了——所有人都认为是善终——而作为唯一的皇帝,图拉真(98—117年在位)尽可能地对元老院表现得恭顺,授予了元老阶层的指挥官和行省总督大量的自主决定权。我们幸运地拥有盖乌斯·普林尼乌斯·凯基利乌斯·塞昆都斯(C.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小普林尼——的书信集,他与图拉真的通信让我们得以一窥皇帝与一位元老等级的代执政官的关系。小普林尼表现得很恭顺,过分担心自己做出可能触怒元首的决定。而对于这位总督的优柔寡断、事无巨细都要一再请求他的指示,图拉真也表现出过分的耐心。这位元首知道,写信给一位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当的人时,礼貌宽容是理所应当的。他也明白自己的指示很重要。他一再提醒小普林尼,要像他本人一样真正关心行省人民,让他们和平地生活,不让他们相互伤害。
图拉真永远作为“最佳元首”(optimus princeps)被铭记,这不仅是因为他迎合了元老们的自尊。他大张旗鼓地保护臣民的安全,还为罗马之名增添了新的荣光。他在多瑙河畔同达契亚国王德塞巴鲁斯(Decebalus)展开大战,在达契亚设立3个新的行省,将帝国的领土扩大到喀尔巴阡山。这些横跨多瑙河的行省让罗马控制了特兰西瓦尼亚的重要矿藏,并使其得以监督喀尔巴阡山以东和以西的藩属国王。降伏达契亚让图拉真变成了皇帝中少有的“帝国扩张者”(propagator imperii)。事实上,“最佳”的尊号不是他死后才有的,而是在他生前就出现了,这个修饰语有时仿佛被当作他本名的一部分。
我们之前看到的皇位继承的不明朗让画面变得更加复杂。图拉真没有子嗣,在指定继承人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最佳元首”很难施行赤裸裸的王朝继承,那会暴露他的专制。与此同时,没有明确的继承方案可能会导致灾难,就像尼禄的统治终结后所发生的。此外,如果不指定明确的继承人,人们就会继续猜测,宫廷中会出现派系,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图拉真做了妥协,不情愿地放弃了同侪中的第一人这个身份。他有一位男性近亲,表外甥普布利乌斯·埃里乌斯·哈德里阿努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哈德良),是西班牙殖民市精英相互联姻的产物。哈德良的父亲普布利乌斯·埃里乌斯·阿费尔(Publius Aelius Afer)于公元86年去世,年幼的哈德良和他的姐姐多米提娅·保琳娜(Domitia Paulina)随即由图拉真监护。我们被告知,图拉真一生都把哈德良“视若己出”,也就是说,甚至是在他穿上标志着罗马男性从童年进入成年的成人托袈(toga virilis)之前。
随后,图拉真让哈德良和自己的甥孙女萨宾娜[图拉真的姐姐马尔基亚娜(Marciana)的外孙女]结婚,从而让乌尔皮乌斯家族和埃里乌斯家族关系更紧密。在一个预期寿命很低和未成年人死亡率很高的世界里,婚姻关系是罗马精英维系自身地位的方式:哈德良与萨宾娜的婚姻非常重要,但他的姐姐多米提娅·保琳娜同著名将军卢基乌斯·尤利乌斯·塞尔维阿努斯(L. Julius Servianus)的婚姻也同样重要,后者家族的继承人在整个公元2世纪都将出现在政治聚光灯下。图拉真授予了自己家族的女性大量荣耀,显然是在效仿奥古斯都对他的妻子利维娅曾经做过的。就这样,图拉真的妻子普罗提娜(Plotina)和他的姐姐马尔基亚娜都获得了“奥古斯塔”的头衔,从此统治者家族中身份显赫的女性通常都会被尊称为“奥古斯塔”。马尔基亚娜奥古斯塔于公元112年去世时,元老院将她封神,然后图拉真又把奥古斯塔的头衔给了她的女儿马提蒂娅(Matidia)。因此,哈德良娶了一位奥古斯塔的女儿和一位被封神的皇室女性——“神圣的马尔基亚娜”——的外孙女。
尽管这一切似乎都意味着哈德良会成为图拉真的法定继承人,但也有一些迹象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在“cursus honorum”——这个词无法翻译,字面意思为“荣誉之路”,是罗马寡头集团成员担任的“官职阶序”——上,图拉真对他年轻的亲戚并没有特别关照。“官职阶序”要先经过若干低级公职,让人积累资格,然后才是一系列可以追溯到共和时期的行政长官:财务官、营造官和法政官。担任过法政官的人会被派去担任行省总督,然后在年满44岁时有机会赢得执政官一职。与执政官一样,这些传统职务也都对任职者有最低年龄的要求,而且担任两个职务的间隔时间遵循奥古斯都建立的规定[这些规定被称为《年秩法》(lex annalis)]。在具备资格的第一年就任职是元老们为之展开竞争的巨大荣耀,但在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和弗拉维乌斯王朝,当政王朝的年轻成员常常不受《年秩法》的约束,让他们可以跳过通常的次序,远比理论上与他们地位相当的元老阶层成员更早任职。图拉真没有允许哈德良这样做,想来是因为皇帝想要展现出他对整个元老院以及约束其全体成员的规定的尊重,但这会让人们感到糊涂。有秘密传言称,图拉真事实上并不太看重他的养子。
直到公元113年,哈德良作为图拉真最可能的继承者的地位才得以确定,当时他被任命为“拥有代法政官权的皇帝特使”(legatus augusti pro praetore),也就是皇帝的卿官(comes,字面义是“伙伴”)和特别参谋,陪同图拉真出征。公元113年,日渐年迈的皇帝决定发动另一场征服战争。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不喜安逸,而是偏爱战场上的生活。在达契亚的战争让他荣誉等身,他很难抗拒在东方作战的诱惑。除了个人原因,那种诱惑也有历史原因。帕提亚帝国是罗马东边的邻国,是当时地中海或近东世界唯一的另一个组织有序的国家。罗马人从至少公元前53年起就把帕提亚人视作意识形态上的劲敌,当时共和国的大将克拉苏在卡莱的战场上阵亡,几个罗马军团和他一起被消灭。从此,对帕提亚的任何胜利都会被视作不仅是军事上的,也是道德上的,尽管帕提亚人往往不会回应罗马人的敌意。对“最佳元首”来说,追随亚历山大大帝的脚步,为克拉苏之死决定性地复仇,是很有价值的计划。
图拉真的借口是亚美尼亚王位争夺者之间的冲突,以及帕提亚对亚美尼亚的干涉。公元2世纪初,亚美尼亚是一个不安地夹在两大帝国之间的藩属王国。它在文化上更接近于帕提亚,其本土王朝与帕提亚国王一样信仰伊朗宗教。不过,它在政治上早已落入了罗马的势力范围,其国王传统上要得到罗马的首肯才可以进行统治。现在,帕提亚推翻了罗马指定的亚美尼亚国王,另立新君。这让图拉真有了他唯一需要的借口,于是他在113年对帕提亚帝国发起入侵,征服它、将其纳入罗马版图是他的明确目标。哈德良作为他的法定继承人的真正地位在这场战事中变得清晰。
对帕提亚的战事开始时,皇帝61岁,对罗马人来说已经很老,无法指望他活到战争结束。战事本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至少在军事层面上。亚美尼亚很快臣服,一些北方高加索腹地的小国国王也纷纷前来向图拉真宣誓效忠。然后,罗马军队沿着幼发拉底河而下,占领了经过的每座城市。帕提亚都城泰西封也陷落了,图拉真由此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位罗马将军。但这对他来说还不够。他继续南进,来到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交汇处,它们随后将一起注入波斯湾。图拉真在那里伫立远眺,慨叹自己太老了,无法追随亚历山大的幽灵一路前往印度。他将不得不满足于扶植一位新君登上帕提亚的王位,控制罗马的这个劲敌。
这位皇帝的成就并不完全像看起来那样。甚至在他离开底格里斯岛[位于今天伊拉克的巴士拉(Basra)附近]之前,东方的事务就已经陷入了混乱。几乎所有被征服的帕提亚土地和一些同盟王国都发动了起义。更让人担心的是,罗马各行省的流亡犹太人发动叛乱,拥立了一位犹太王,这是危险的弥赛亚式期望的信号。在罗马通常的政策下,如此规模的叛乱需要大规模的报复。图拉真派出他最好的将领去对付犹太人,而他本人也率军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回到罗马境内,一路上非常残酷地镇压帕提亚人的叛乱。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没有显而易见的办法来挽救局面。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将不得不被放弃。当图拉真回到罗马的小亚细亚时,他已经身染沉疴,无法行军,于117年8月8日在奇里乞亚的塞利努斯(Selinus)去世。他的死讯被封锁,直到可以通知哈德良并让他在军队面前现身,后者不出意外地拥戴了他。随着哈德良的登基,我们的主体故事可以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