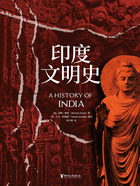
没有社群的国家;社群作为社群主义
到19世纪后期,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的政策旨在破坏社群的地方基础,这样的政策是通过几种方式实现的:将以前的地方首领转变为从属型地主,任何抵制这种变革的努力都被瓦解;拆分细化以前的统一领土;通过法律上的改变将以前属于群体的权利个人化;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偏袒某类团体和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文士种姓(scribal castes),特别是婆罗门人,兴旺起来,而长期被认为应该对民族大起义负责的穆斯林遭受了苦难;大多数地主都从中受益,而大多数佃户和无地劳工都蒙受损失。
然而,社群作为某种普遍道德的地方性体现的观念仍在继续,并且随后人们又构想出了通过社群主义促进某些群体利益的新方法。从历史和目前的情形来看,社群是印度人认为自己在其中出生、社会化并最终必然会延续的东西。他们出生在特定的地方,有语言、社会和种姓群体、政治和文化归属。地域性和时间性,或历史,一直是并仍然是社群的关键层面。“社群主义”是动员的手段,是激起人们采取行动的标志,这类行动通常是大规模和暴力的行动。这方面有一些众所周知的例子,首先是建立种姓协会(caste associations)以回应英国人在人口普查中使用的种姓类别,这些协会的目标是对殖民者推定的排名提出质疑,并挑战高等级种姓对低等级种姓的诋毁。19世纪后期,“牛保护”(cow protection)和“文字改革”(script reform)运动——后者要求用天城文(Devanagari)写的印地语(Hindi)取代用波斯语(Persian)文字写的乌尔都语(Urdu)——被证明是动员印度教教徒对抗穆斯林的有效手段,经常以此作为抗议某些地方性的令人不满事件的手段,或由此取得一些地方优势。
在这些复兴和改革运动中,增加了对单设选区的政治激励措施。1909年的莫莱-明托(Morley-Minto)改革改变了曾在19世纪60年代时向当地选民开放席位的填补方式;穆斯林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席位,他们有权选举自己的教友。[11]官员们认为,这种对民众政治参与的适度让步,只是承诺将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分开,但印度自独立以来的大规模选举不可避免地造就一些能唤起记忆的、动员性的符号与口号,这些符号和口号对各种社会分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复兴主义和单设选区共同作用,通过将种族、语言和宗教因素视作有界限的法律/行政类别的组成部分,重新定义了社群。20世纪初的这种重新定义对印度的政治生活将是一把双刃剑,并将为分治[12]创造条件——尽管不是必要条件。这对印度民族主义而言是个悲剧,但不是唯一的悲剧。
民族主义以几种方式加剧了涉及社群主义的活动。首先是英国人对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提出的参与行政管理、协商制定政策,以及政府支持印度经济的要求所做出的操纵性反应。1909年的独立选区代表了帝国政策从敌对到支持穆斯林的转变,从此以后,他们和地主们一起,成为反对英属印度时期中产阶级专业批评家的堡垒。
但是民族主义者对社群主义形式的组织和鼓动做出了更多的贡献。1925年,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作为一个文化组织成立了,使印度教成为印度政治生活和民族主义斗争的意识形态核心,几十年来,它成功地赢得了包括一些领导人在内的许多印度国大党运动成员的支持。除了对原始宗教情绪的诉求外,民族主义政治中的宗教部分还反映了印度民族主义的脆弱而混乱的另类意识形态基础。其他一些外围组织从RSS中涌现了出来,其中包括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va Hindu Parishad,VHP)、印度青年民兵(Bajrang Dal)和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所有人都致力于推翻国大党的世俗主义纲领。
在圣雄甘地领导国大党期间,为了推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自由斗争,印度掀起了一场群众运动。在1920年的那格浦尔(Nag-pur)大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特点,它将为其他种类的社群主义思潮奠定基础,从而把印度政治带入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甘地在那格浦尔大会上敦促对印度国大党党章进行改革,将语言区而非英国所设的省作为国大党组织和动员的基础。按照甘地的意图,政治行动和宪政可行性基于语言,这让那些之前被精英统治者排除在外的人能够参与甚至最终领导国大党。相应地,不仅国大党的成员构成出现了从高等职业、受过西方教育的城市男性向中下阶层比如教师等较低等职业成员的阶层转移,而且还为农民和其他中下等级种姓群体提供了提升他们的职业前景的机会,使他们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专业资格并长期操控着党派的人进行竞争。与此同时,那些尊贵的种姓以及城乡中下层阶级所普遍信奉的宗教,也都得到了新的重视,这是20世纪最普遍的公共话题。最后,甘地坚持国大党纲领中应回避阶级诉求,这意味着其他形式的动员活动获得优先考虑——最持久和最危险的是宗教活动——而印度穷人的正义要求却始终遭到拒绝。甘地只希望能够有一场能将印度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统一的群众运动,一场没有内部分裂的、他能够用个人魅力掌控的运动。
虽然寄予厚望、满怀理想并提出主张,但最终未能使印度人摆脱偏见、贫困和压迫,这可以使半个世纪以来摆脱外国统治的自由运动显得无足轻重。社群主义的修辞,无论是语言学的还是次民族主义的(subnationalist),种姓的还是印度教的,都只会越来越多地为殖民征服下由资本主义所形成的阶级服务。殖民政权及其民族主义反对者都使用“社群”这一概念,这就是为何社群主义未遭摧毁。“社群”这一概念在20世纪期间被剥离了其历史性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属性,它仍是一个被粉饰过的怪物,一个意义的外壳,容易被相互斗争的团体和阶级操纵,尤其是印度小资产阶级的教士/政客们。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选择不反对阶级压迫,因此,被重新塑造为“社群主义”的“社群”理想,虽然蓬勃发展但仅仅是一个修辞的外壳。
完整的循环:受压迫者的宗教诉求
直到最近,其他也借助某种宗教习语来推动他们正义呼吁的声音一直都被忽视。这些团体从属于小资产阶级,同时也是他们的受害者,小资产阶级成功地将宗教社群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就像专业资产阶级将世俗主义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一样。在一个不再存在完整的和有生命力的社群来赞美或维护的时代,宗教继续为索偿诉求提供一种语言,即使这些只是被压迫者的渴望,并终将是无效的恳求,他们希望他们的压迫者能够被传统束缚,能因旧价值观而羞愧,从而做到品行端正。不过,达利特人(dalits,被压迫者)利用宗教论点来推进其正义主张的努力至少值得简短的评论。
为什么印度社会中那些因身份污染(ascriptive pollution)而总是被禁止参加一般宗教活动的人,现在要用宗教术语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呢?18世纪末殖民当局的建立消除了次大陆中除土邦(princely state)以外的大部分王室权力。作为对王室裁决的取代,东印度公司成立了法庭,其职权范围是根据英国人对古代道德文本《法典》(dharmashastra)的理解来执行“传统”法律的一个版本。但是,法庭无法填补以往根据社群惯例和习俗做出的协商一致的裁决准则留下的空白。因此,只有宗教仍然是社会裁决的基础,东印度公司的政策非常愿意让乡村五人长老会[13](panchayat)和马汉特[14](mah-ant)解决殖民当局不感兴趣的争端,例如谁愿意或不愿意崇拜谁,谁有受人尊敬的地位,等等。小资产阶级宗教压迫的最直接受害者被迫求助于这些机构和这样的措辞。
印度的社群主义政治,同中东和美国的宗教激进主义政治一样,反映了中下层阶级大部分人民的利益和恐惧,他们的经济保障和社会保障都岌岌可危,而且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的危险在于它很容易粉碎持有较少财产者和卑微职业者长期享有的保护和微小特权。另一方面,包括印度在内的所有社会中最贫穷的人都要求社会正义。在20世纪,政治家们的承诺助长了穷人们对更好的机会、资源的欲望和渴求。在印度,由于其有力的民主制度和积极的选举参与度,这些期望通过频繁的竞选活动得以保持活跃。但是,如果大众能从中获益的话,那他们只是从那些稍微富裕一点的人身上获得好处,非常富有的人的财富是永远不会有风险的。印度的中下层阶级,似乎就像其他地方的一样,用宗教符号来掩饰他们经济地位的脆弱性——在此是藏红花色,在彼是黑色。[15]在印度、伊朗和美国的得克萨斯州,这些符号象征着传统正义,以及对事物原貌的维护。在印度,与世俗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非常富有和有权势的人,激发了中下层阶级对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的渴望,但也使他们明白实现这个目标对他们来说是多么不可能。赤贫者则扬言要选择更为恐怖的替代方案。面对带有危险的变化,宗教为维持勉强现状的人提供了一种替代性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