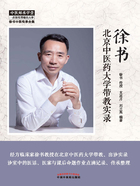
一、脉诊指导问诊
徐师言:“问诊有方向,不一定盲目按照课本来问,要以脉诊为指导。”
所谓尖端,即“先锋”之意。徐师的问诊,往往是从脉出发,有针对性地询问,而非一板一眼地按照“十问歌”来询,这也是临床诊断与书本上所学的差异。
如何从脉出发呢?这其实也和《伤寒论》中“抓主证”的思维方式有关。徐师会把脉象与证候对应,根据脉而定病位、定方。初步问诊与脉诊结合,心中有了大致方向,再针对性地提出问题,最终做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举例而言,有一次跟诊时遇到了一位50岁的男性患者,他患有冠心病3年。西医建议手术介入治疗,放置支架,现患者想结合中医一并治疗。对于这个患者,徐师先采集了基本信息,开始切脉,随后再展开详细问诊。首先问的是心脏的感觉,患者答最难受的时候会有胸闷、气短;接着,徐师又问他这种症状是否在晚上发作,他说晚上偶尔会出现气短的感觉,并且经常在凌晨两三点钟醒来,醒后胃部亦不适,且怕冷;之后又问大便情况是什么样的——干稀程度及次数如何,患者答偏稀,一天1~2次;最后一个问题,则是口干否,患者答口干。于是,徐师开具处方:乌梅丸加减。
事后,徐师讲解,切脉得此患者左脉弱,右脉浮弦,此为典型乌梅丸脉象。再根据主诉详细询问,得到夜间症状发作的反馈,继而根据脉诊所定的方向深入询问,“心脏不适、眠差、大便稀、口干”等乌梅丸的主症已经出现,验证了切脉所得的推断,于是开始处方。
还有一次,徐师治疗一位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人。首先切诊为脉象弦急但两尺弱,接着询问他是否有“口干、口苦、口渴”的症状,患者答是。通过“口干、口苦、口渴”可考虑少阳、阳明合病。然后询问患者大便情况与腹部感受,得到“腹胀、大便干结”的答复,于是方用大柴胡汤来攻下。但同时,通过闻诊发现患者身体及口腔都有着臭味,这说明患者的病情较为严重,元气亏虚较重,虚中夹实,当补虚与攻实并进。于是又加引火汤,引火归原,填精化气。两方合用,治疗一周,效果很明显。
总结来说,徐师问诊时必须要强调的几点为“口干否,大小便如何,睡眠怎么样,有无外感表证”。“口干否”判断病位是否在少阳、阳明,“大小便”来判断病位是否在太阴,“睡眠”则往往考虑厥阴,“有无外感表证”判断疾病是新感或久伤。由脉定虚实,由问诊来佐证、判断,这便是脉诊引导四诊,四诊合参的体现。徐师说,观仲景伤寒之标题,几乎都是把脉放在第一位,如“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辨少阳病脉证并治”,因此诊断时就要洞悉伤寒与病机,应当把“抓主证”“抓脉证”与“抓核心病机”相结合。以脉为门,我们就可以开门见山,指导其他三诊,而后以脉定证,以脉定方。
有时我们会好奇,徐师为什么看病又快又准。徐师说,这里面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长久的临床经验;第二,扎实的经典基础。二者缺一不可。
徐师认为,中医成才有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本科毕业后的五年,此时是迷惑的。当时徐师跟师朱良春先生抄方的时候有时也疑惑,朱老临证时经常只问患者:你口干吗?病人说:口不干。其余就都不问了,开始开药。随着积累,徐师最终也提炼出问诊的三句话——“口干否?食纳如何?大便怎么样?”问完三句话,方子就基本上已经浮现在脑海中,而这源于经验的积累以及对脉证的准确把握。因此,对于这第一阶段的迷惑,只有不断地夯实基础才可以解决。第二个阶段,则是毕业后五到十年。这时已有一些临床经验,但却还不能解决一些疑难病,于是又从头温故基础知识与经典,之后再去临床中总结经验,此阶段要善于思考,保证每天必有一得。而第三个阶段,已驾轻就熟了,但是也会时时遇到瓶颈。这时只能耐下性子继续突破。
由此可以看出,徐师是将经典烂熟于心,掌握其思维方式与知识体系,融会贯通,才能如此灵活应用的。也因此,这样的诊断方法是高效的。可能作为学生,一开始并不敢如此问诊,但是我们要以此为目标,敦促自己加强对脉诊的训练,并且不断阅读、理解、思考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