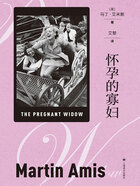
2:社会现实主义(或称见谁就爱的渣男)
基思盖着床单,躺在南边的塔楼里。他想着离开酒吧时,维特克甩上肩的那个脱线的粗麻布袋子,想不出什么来。那是什么?基思自问。邮包袋?他猜,意大利的邮包袋,和英国的一样,是国家监狱里做出来的。而维特克的粗麻布袋子的确看起来像是重罪犯织的(看起来完全是心怀怨懑地将线绞在一起),纬线的有些地方带着点变态的淡紫色调。基思发现,这些日子,他的思想总是转向执法上。或者说是无法可执,法律松懈得令人费解……不是邮件,维特克说,邮件都是直接送达的。里面装的是——世界。看到了吗?整个世界,就在里面:《泰晤士报》、《生活周刊》、《国家》、《评论》、《新政治家》、《听众》、《旁观者》、《邂逅》。由此看来,它还是在外面——整个世界。而世界早已看起来非常的宁静,非常的遥远。
“我想你同意,”丽丽在黑暗中说,“蒙泰勒的那些年轻男人。”
“不,我不同意,”基思说,“就这么跟你说吧。我想在你面前上蹿下跳。”
“……你知不知道那种感觉是怎么样的,对我来说?”
“是的,我想我明白的。我和肯里克一起时,我就有那感觉。他们不会在他面前上蹿下跳,可是他们——”
“嗯,他美极了。”
“嗯。挺受不了的,但记着,这世界品味很差,就喜欢显而易见的。”
“什么是显而易见的?”
“得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表面上的。她的外表可能讨庸俗的人喜欢。丽丽,可是你聪明得多,有趣得多。”
“嗯,谢谢。但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会爱上她的。当然,不是说你有什么希望。但是你会的。你怎么会不爱上她呢?你。所有动的东西,你都会爱上。你都会爱上女子足球队。更何况山鲁佐德,她又美又甜还有趣,而且傲慢得不得了。”
“这正是让我反感之处。她不相干。她来自另一个世界。”
“呣,事实是,你被比下去时,的确心里是有数的。”她说,一边把靠在他手臂上的身体摆了个更舒适的姿势。“像你这样一个一等一的傻瓜。像你这样一个坏脾气的小穷鬼。”她亲了亲他的肩。“名字里都写明了,可不是。山鲁佐德——和基思。基思大概是最大众化的名字,是不是?”
“可能是吧……不。不对,”他说,“苏格兰封伯爵的元帅们都叫基思。好几代呢,每个都叫做基思伯爵。不管怎样,都比提米好听。”他想到那个笨拙的懒洋洋的提米,在米兰,和山鲁佐德一起。“提米,叫那种名字?基思这名字比提米好多了。”
“任何名字都比提米好多了。”
“是啊。难以想象哪个提米做出点漂亮的事来。提米·米尔顿。提米·济慈。”
“……基思·济慈,”她说,“基思·济慈听起来也不像能做漂亮事的。”
“没错,不过,基思·柯尔律治?丽丽,有个诗人叫基思·道格拉斯(1)。他可是上流人。他的中名是卡斯泰朗,他和肯里克上的是同一所私立中学,基督公学。哦,对了,还有G·K·切斯特顿(2)的K也代表基思(Keith)。”
“G代表的是什么呢?”
“吉尔伯特。”
“你看,那就是了。”
基思想到基思·道格拉斯。一位战争诗人——一位勇士诗人。受了致命伤的战士:噢,母亲,我的嘴里满是星星……他想到基思·道格拉斯,在诺曼底死去(头上挨了弹片),那年二十四岁。二十四岁。丽丽说:
“好吧。她要是说,想操你给你口交,你打算怎么办?”
基思说:“我会吃惊的,但不会震惊。就是会挺失望的。我会说,山鲁佐德!”
“嗯,我信的。你知道,有时候我希望……”
基思和丽丽在一起有一年多了——最近有一个学期的间断,又被称作过渡期,幕间休息,也可简单地叫做春假。眼下是经过了试分手、试和好。基思亏欠她许多。她是他的初恋,特别意义上的初恋:他爱过许多姑娘,但丽丽是第一个也以爱相报的。
“丽丽,我爱的是你。”
这下,夜间的交流,不可描述的举动,就着烛光,开始了。
“好玩吗?”
“什么事?”
“假装我是山鲁佐德。”
“……丽丽,你总是忘了我情操高尚。马修·阿诺德。是人类思之所至言之所及的最好的东西。(3)F·R·利维斯(4)。感觉到生命完满的创造力。而且,她对我来说太高了。她不是我那一款。你是我喜欢的款,丽丽。”
“呣。你不像以前那么情操高尚。一点儿都不像了。”
“不,我还是老样子……是她的性格。她又甜又和善还幽默聪明。她确实不错。这恰是最不吸引我的。”
“我知道。简直令人作呕。而且她还长了一英尺,”丽丽说,她这下愤慨地全醒了。“而且都长在了她的脖子上!”
“这是条脖子,也没错。”丽丽早已就山鲁佐德和她的脖子说了一大堆。她把她比作一只天鹅,有时候是——取决于她的心情——一只鸵鸟(还有一次,是长颈鹿)。丽丽说:
“去年她……山鲁佐德发生什么事了?”
有天早上,山鲁佐德从梦魇中醒来,发现自己成了……没错,根据那个有名的故事,格里高·萨姆莎变形成了一只体积庞大的昆虫,也可说是大害虫,也可说是——基思很有把握那是最好的翻译——可怕的跳蚤。对山鲁佐德来说,变形是大大的升级。不过基思没法落实合适的动物。鹿,海豚,雪豹,有翅膀的马,天堂鸟……
不过,先提一下之前发生的事。丽丽和基思分手是因为丽丽想要像男孩一样举止行事。这是事件的核心,真的:人们似乎有感觉,女孩要像男孩一样举止行事了。丽丽想要先试试。于是,他们有了第一场大争执(荒谬的是,主题竟是宗教),丽丽宣布了试分手。这个词像是压缩的空气直冲出来:他知道,这样的试验几乎总是成功的。两天的极度悲痛,在他位于伯爵府区可怕公寓的可怕房间里,度过了无人陪伴的凄凉的两天之后,他给她打了电话。他们见面了,咖啡桌的两侧都洒了眼泪。她告诉他,这事儿,他得进化一下。
为什么男孩享有所有的乐事?丽丽说,一边往纸巾里擤了擤鼻子。我们不合时代,你和我。我们像是儿时的恋人。我们应当十年之后再认识。要一对一,我们太年轻了。就算是谈爱情,我们也太年轻了。
他聆听了这番话。丽丽所宣告的让他觉得如丧考妣。基思的确一出生就没了父母。这将是他生存的状态,这一想法对他是自然不过的。他听着丽丽说——当然她说的他早已知道。男男女女的世界正在翻腾,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或是沧海桑田的变化,在肉欲知识和情感需求之间重新调整。基思不想成为与时代不合的人。我想我可以说,这是他第一次为自我性格管理作出努力:他决定不让自己坠入爱河。
如果我们不喜欢,可以……我想做男孩一段时间。你可以继续老样子。
于是,丽丽重新做了头发,买了很多超短裙、短裙裤、露背吊带装、透视装、齐膝漆皮靴、大圈圈耳环、彩色眼线笔,还有所有其他林林总总要和男孩一样举止行事所需要的一应物事。而基思保持了老样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位置比她有利:他做男孩已经有些经验了。这下他又重新做起了男孩。前丽丽时期,在丽丽之前,他经常碰到一件难事,这与做女孩更相关:他的情感。而且对事情,他时常弄不清楚。比如说,他彻底搞错了每个人都称作自由性爱的事——一个接一个惊脱了下巴的嬉皮士都会默默地作证。他以为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但这不是都市里苍白如蘑菇的花样女儿带着星座图、塔罗牌和灵应盘自动送上的性爱。有些女孩还是想等到结婚,有些还信教——就连嬉皮士向世俗化的转变也很慢很慢……
在丽丽之后,后丽丽时期,男女关系的新规则似乎更为落实了。那一年是1970年,他二十岁:这一历史性的机遇,他备有少无可少的俊美相貌,如簧的口舌,诚挚的热情,还有一点努力装出来的但也令人精神一振的冷酷。有过到了紧要关头却大失所望的经历,也有过一些奇迹般的默许(就耻辱—荣誉的意义来说,仍旧感觉像是越轨之举:莽撞失礼,过于亲昵,占便宜)。不过,“自由性爱”一事,最佳对象当然是装做男孩的女孩。新规则——让万事出错的阴险的新规则。他的行为举止像个男孩,丽丽也一样,而且还能比他更像个男孩。
和我一起去吧,三个月之后,丽丽在电话上说,夏天和我一起去意大利过吧。和我一起去意大利的城堡,还有山鲁佐德。去吧。去度个假吧。你知道,那儿的人们甚至都懒得装客气有礼。
基思说,他会给她打电话的。不过,与此同时,他感觉到自己的脑袋突然点了一下。他刚和一位前女友(她的名字叫潘西)度过了几乎具有艺术性的痛苦的一晚。他又害怕又受伤,而且还平生第一次感觉到说不明道不白但却强烈无比的愧疚感。他想回到丽丽身边——丽丽和她的中间世界。
要多少花销呢?
她告诉了他。去程你还得花点钱。事实是,我不擅长做男孩。
好吧。我很高兴呢。开始借钱攒钱了。
他和丽丽那场荒谬的争执。她责怪他,在维奥利特还是个小女孩时,用基督教把她搞糊涂了,因此也损坏了她的心灵。就事论事,也不算错。他解释道,她九岁时,我试图让她反皈依。我说,上帝就像是贝尔格罗:你想象中的朋友。可是,她却粘上宗教不放了。丽丽说,你以为宗教会令她举止得当。而效果却相反。她深信所做的坏事都会被原谅,因为她相信天上那个傻瓜。而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丽丽自然是个无神论者——一目了然。基思争辩,这个立场不太理性,不过丽丽的理性主义一开始就不算理性。当然,她痛恨星相学,但她也痛恨天文学:她痛恨光有折射、引力越大时间越慢这些事实。对亚原子粒子的活动更是气恼不已。她希望宇宙能够合情合理的运作。丽丽连做梦都是日常琐事。梦中(这是她羞答答地说出来的),她要么去商店,要么洗头发,要么靠着冰箱吃点点心当中饭。她公开地对诗歌持有怀疑,对任何与最坚定的社会现实主义的小说相背离的小说,她全无耐心。她毫无保留地赞赏不已的唯一一部小说是《米德尔马契》。因为丽丽就是那样一个中间世界的产物。
和我一起去意大利的城堡吧,山鲁佐德也一起去。应当指出,丽丽的提议中山鲁佐德这一部分,就基思看来,左右不着道。他上次见到山鲁佐德时,大概是圣诞前后。她一贯的模样是穿着平跟鞋戴着眼镜的眉头紧锁的慈善家。她做的是社区服务,参加核裁军运动和海外自愿服务组织,开个小货车送免费餐,她还有个四肢柔软的男朋友叫提米。提米喜欢杀害动物,拉大提琴,上教堂。不过,山鲁佐德接下来就从梦魇中醒了过来。
基思原以为社会现实主义在意大利会守得住。可是,意大利本身看起来有传奇色彩,他们住的城堡也有传奇色彩,山鲁佐德的变形也有传奇色彩。社会现实主义是在哪儿呢?他一直觉得,上层社会本身可不是社会现实主义者。他们的行事方式,遵循宽松得多的规则。他是城堡中的——预兆不祥。但他还是认为社会现实主义会守得住。
“她仍旧和那些潦倒的老头子一起干那些事吗?”
“……照样干。她可惦记呢。”
“她那个小伙子在哪儿?那个提米在哪儿?他什么时候来?”
“这不就是她想知道的嘛。她对他生气着呢。照理他现在就该在这儿了。他现在在耶路撒冷,天知道他在那儿做什么。”
“……我喜欢的是她妈妈,蒂娜。娇小可爱。”他想到了潘西。想到了潘西自然就想到了她的老师,丽塔。于是他说道:“呃,丽丽。你知道我提过肯里克可能往这边来。他打算和狗宝儿一起去撒丁岛。”
“狗宝儿叫什么名字?是不是丽塔?……描绘一下。”
“好吧。从北边来的。有钱的工人阶级。眼睛很大,嘴巴很宽。一头红发,全无曲线可言,直得像一支铅笔。我们能不能让他们借宿一夜,肯里克和丽塔?”
“我问一下山鲁佐德。为这个北边来的无胸红发姑娘,我肯定,”她说着打了一个哈欠,“可以腾出一点空间来的。我等着见到她俩。”
“你会对她赞叹不已的。她扮起小子来,可像了。”
丽丽侧过身去。她看上去更小了,变得完整而紧凑。她一摆出这个姿势,总让他心里升起一阵柔情。他留心着她微微的抖动和抽搐,一路进入混沌忘我中。如果不接受无理性,她又怎能找到那片时空?丽丽抖动着进入睡眠之圣地时,有时候喜欢听着他的声音(他通常是总结一下自己在看的小说),他挪近了,说:
“以后会有很多小说的。听着。第一个我吻过的姑娘比我高,可能不过几英寸,但感觉像是足有一码。莫林。我们在海边。之前我已经在公交车站的遮篷下坐着时,吻过她。我不知道该怎么吻别道晚安。她家旅行拖车旁边的地面上有下水管道,我就站在那上面。美妙的吻。没有湿吻,我们还太年轻了。年纪不到,有些事不要做,这很重要。你觉得呢?”
“山鲁佐德,”丽丽大着舌头说,“带她到下水管道旁去吧。”随后,她的声音又清晰了点,“你,你怎么可能不爱上她呢?你爱上一个人多么容易啊,而且她还……晚安。我有时候希望……”
“晚安。”
“你,见谁就爱的渣男。”
等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他想),摆在面前的首要之事就是:分辨真假。我们得清理瞌睡带来的讥笑嘲讽。但一旦到了一天结束之际,又换了过来,我们寻找着杜撰的不实之事,有时候急于找到荒谬的联系,像是被扇了一巴掌,猛地醒了过来。
她说得没错,或者说以前是这样,见谁就爱的渣男,和他特别的出生相关。他轻易就爱上姑娘——而且还继续爱着她们。他仍旧爱着莫林:他每天都会想到她。他仍旧爱着潘西。难道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他琢磨着。难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和丽丽一起在坎帕尼亚的城堡?因为和潘西一起度过的那个悲剧之夜,那个晚上说过的话,还有话中的话?基思闭上了眼睛,找寻着注定备受困扰的梦。
山谷中的狗吠叫着,村里的狗不甘落后,叫了回去。
天色刚亮,他起了床,在瞭望塔上抽了一根烟。昼色像急流一般淌进来。突然,山脊上,上帝的红公鸡昂起了首。
(1) Keith Douglas(1920—1944),以其二战时期的诗歌知名。
(2) G.K.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以及神学家。
(3) 出自马修·阿诺德《文化和无政府状态》,原文是指文化。
(4) Frank Raymond Leavis(1895—1978),英国文学评论家,长期在剑桥大学教授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