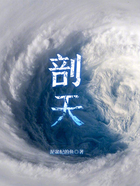
第30章 回家
“叮铃铃铃铃……”
陈相从绝望中醒来,赵栋梁和张瑾玥的脸在他眼前交叠。
他的心底生出一种极度渴望,渴望有一个全能全知者能把秘密全盘托出,告诉他为什么个性天差地别毫不般配的两个人能有机会结合在一起。他们明明那么不同,一个像阴暗潮湿的朽木,一个像光洁靓丽的大理石。究竟是什么,让这两块毫不般配的材料紧紧粘合在一起?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他人生中的前26年里,赵栋梁的表现离一个称职的丈夫差着十万八千里。而这里,在前九次的轮回中,赵栋梁始终流露出对张瑾玥可谓越界的关切,好似张瑾玥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他在婴孩期的记忆自两岁起,倘若他果真正在经历26年前的历史,那么在他出生后的两年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之事,才能让张瑾玥火速改嫁赵栋梁,赵栋梁对张瑾玥的态度又为什么迅速由殷切转为冷漠?还有最重要的,陈波的死因究竟是什么,才能让和他或疏远或亲密的所有人,都对他闭口不提,仿佛他从未存在过?
不断从心底冒出的疑问把陈相淹没,险些让他忘记那件最棘手的事:如何救下张瑾玥,同时救下被台风波及的所有人,结束这无尽的轮回。
上一次的经历已经给到他足够明晰的提示,要想让一切人和事都按照既定轨迹运行,就不能像游戏作弊者那样运用上任何超越时间的东西。
如果迟到的卫星数据注定不能被提前使用,那么要想做出一份完美的预报,就要用其它方式补充初始场中垂直方向的信息。方法只有一个,还是放气球,放很多个气球,像用丝网刀切熟鸡蛋丁那样,把老天爷切成一格一格的。
这个方法是完全可行的,气球胚子和氢气都足够多,况且如果只关注附近的天气形势,只在附近多放几个即可。用动力方法做数据同化的时候,内部网格的信息多多少少会被反馈给外部,使得整个初始场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
可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气球放得越多,耗时越长,越无法匀出时间去处理张瑾玥。而张瑾玥似乎只有亲眼见到自己,才能侥幸平安。
他被极其有限的时间限制着,就像往身上套一件缩水的羊毛衣,再怎么拉扯衣袖,都总有一只手腕要露在刺骨寒风中。究竟要怎样做才能破局?
头脑飞速运转,一张张熟悉的脸悬浮在眼前。他所要完成的事,一定不是单枪匹马就能做到的,他需要其他人的协助。由于要运行模式,并说服只信任他的张援朝,他自己一定是要尽早返回台里的。如果想要匀出时间去见张瑾玥,那么就要有人代替他放气球。
可又有谁能替他呢?为了保证安全,气球施放必须由两人配合进行。林芳是一瘦弱姑娘,估计连无线电仪都举不动,不可能让她去;张勇已经明确拒绝过他,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回心转意;陈德球要开车,要望风,且完全没有经验,容易操作不当耽误时间,也不可能让他放;赵栋梁就更不用说了,这事得完全躲着赵栋梁,否则那人一打小报告,谁也别想离开台里。所以,能放气球的只有任天富。
再一次回到死胡同,他根本不可能同时兼顾气球、模式和张瑾玥。自己和任天富是唯二能运行起模式的人,所以他们无法处理张瑾玥。陈德球要赶时间见儿子,也无法顾及到张瑾玥。林芳毫无行动能力,张勇不肯离开台里,张援朝要指挥防台,这三个人都无法解决张瑾玥的问题。按照之前几次的经历,即便于姐有能力顺利送张瑾玥到医院,张瑾玥也仍然逃脱不了死亡。
如此这般,仅剩的,没有尝试过的可能人选,就只有赵栋梁。虽然陈相向来不觉得赵栋梁对张瑾玥有什么感情,但在这里,那位卖卦哥似乎把张瑾玥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在铃声的尽头,陈相打定主意:就这么试试吧,让赵栋梁去试试吧。
晚间11点整,陈相利用上一次的探空数据和来自未来的卫星数据,跑上能够复现瑞云湖暴雨的模式。然后从抽屉里掏出湿漉漉的小草球,捏在手里,奔跑下楼,寻找赵栋梁。
一如既往地,赵栋梁的躲在半山腰的红桑丛后,一只手捧书,一只手打手电,来回渡步,口中念念有词。陈相趟过一丛红桑,停在赵栋梁面前。两人隔着一棵幼年棕榈树,面面相觑。
赵栋梁把书合上,拢入怀中,眉头皱出刀痕,警觉地望着陈相,一语不发。
“你在这里做什么?”陈相问。
“不用你管。我今天不当班,不归你管理。”
赵栋梁的回答在陈相的意料之中,早在第一次轮回时,陈相就察觉赵栋梁对自己有着莫名其妙的敌意。虽然他很想知道陈波和赵栋梁究竟是什么关系,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但时间已经不多了。
“张瑾玥要生了。”陈相单刀直入,以毫无攻击性的语气陈述。
赵栋梁的眼睛眯缝起来,凝视陈相,像在注视世界上最古怪之人,“你不会刚刚知道这件事吧?”
“当然不。”
得到陈相的否认后,赵栋梁脸上刚燃起一半的愤怒又开始消去。
“你怎么知道她快要生了,你们关系很好吗?”陈相把他最关心的问题问出口,心跳得像打鼓。他早已从各个角度揣测张瑾玥和赵栋梁的关系,却始终毫无头绪。他对赵栋梁的回答无比期待。
“她告诉我的。”赵栋梁轻飘飘的吐出这一句话,像在陈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他说完后,便开始呈现出一种回避的姿态,眼神从陈相脸上抽离,甚至慢慢转过身,倚靠在棕榈树干上,背对陈相。
赵栋梁的这番回避,让陈相心里轻松一大截。他不必再担心因为没有注视赵栋梁的眼睛而让对方感到不尊重,也不必焦虑对方的哪句话让他无法压抑多年的埋怨怒而暴起。那样的话,赵栋梁这种自尊心格外强的人,必不会配合他半分。
“你们关系很好吗?”对真相过于浓重的渴望让陈相逐渐失去理智,追问出一个赵栋梁明显不想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陈相等了很久,等到被赵栋梁手电吸引的蚊虫逐渐发现另一个美味猎物,簇在陈相身边。
“当然没你们两口子要好。”赵栋梁的挺直的腰板渐渐松垮下来,“她给你炖鱼汤是因为爱你,给我炖是因为可怜我。我比不过你。”
说完,他抬脚离开,依旧背对着陈相,为了绕过陈相,甚至不惜去钻最浓密的那丛红桑。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我预测到今天晚上要刮台风,发洪水。瑾玥快生了,你帮我送她到医院待产吧。”陈相冲赵栋梁的背影喊,以复杂的心情,真诚的语气。
赵栋梁的脚步停住了,他正卡在红桑丛里,连忙后退几步侧头望向陈相,满脸焦虑。
他沉默很久,像是在做复杂的心理斗争,斗争的尽头却是一句轻飘飘的话,“你可以请假。”
“我请假的话,就没人做预报了。”陈相已全然掩饰不住自己眼中的殷切,“我请求你,帮我这个忙,到我家巷东头裁缝铺里接到她,送她到医院,让她平安。”
说完,陈相主动走向赵栋梁,把还在滴答滴水的苔玉塞到赵栋梁手里。
晚间11点20分,陈相返回值班室把模式结果递交给张援朝。安顿好张瑾玥后,其余的一切工作都变得时间充裕并井井有条。
张援朝会在未来两小时内的某个时间点,发现探空和卫星数据的来源问题,只疏散赤坎河附近的居民而不肯和水文队一起做出炸堤的决定。但在张援朝踌躇期间,陈相会尽全力在瑞云湖中附近方圆20公里内,施放四个气球,然后回到台里,重新运行模式,把自己的违规行为和盘托出,用一份无懈可击的预报产品,彻底说服张援朝。
在这一次的计划中,唯一的变量就是张瑾玥。他无法保证张瑾玥见到赵栋梁能和见到自己一样安心,但他已做出最大的努力。他为她安排了一个同样喝过她鱼汤的人,并且带去了信物。
今夜的一切都格外顺利,凌晨1点20分,瑞云湖暴雨的预报结果被再次复现。当陈相出现在张援朝眼前时,那位焦头烂额的指挥官差点把他按在墙上质问他一整晚都去了哪里。陈相从未料想到张援朝会失态到如此地步,只能拼命认错,并以最诚恳的态度说服对方炸堤。
凌晨1点40分,霞山区和赤坎区的大街小巷,警报迭起,人头攒动。已经被从家里赶出来的人,被迅速接到附近的建筑物里。还未出门的,被勒令呆在原地。
距离命运的审判还有40分钟时,陈相已回到值班室,在呼呼暖风中,精疲力竭,无所事事。他坐在陈波的位置上,把摊在桌上笔记本,翻到开头,一页一页阅着。重温张瑾玥和陈波的过往,他不再感到尴尬,只觉得温馨。也许马上,他就要重新回到现实中,回到一个同样可惧的台风夜,再一次把她救下,让这种温馨和美好永远在自己的生活中延续。
他的全身都还在滴水,为了不沾湿笔记本,翻得很小心。张勇十分贴心,让空调风口调转方向,直冲陈相吹。干燥的暖风把周围的书页一齐刮得哗哗响,连同赵栋梁桌上的那本《渔樵问对》。
《渔樵问对》是赵栋梁托陈相带回台里的,赵栋梁自己则径直骑上二八大杠去找张瑾玥。在把这本书送回值班室的路上,陈相根本无心翻看,而现在他则有暇释放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他坐到赵栋梁的坐位上,望着那本厚得像砖一样的《渔樵问对》,从书右侧中缝处翻开,直接翻到正文处,惊讶到浑身木僵。
映入眼帘的不是艰涩难懂的古文,也不是精心注解的白话文,更不是形形色色的卦相,而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天气图和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
这不是古人用来参透天机的《渔樵问对》,而是《天气学原理》和《天气学分析》的合订本。被戏为卖卦哥的赵栋梁,从未问天买卦过,他算出的东西,也不是天机,而是脚踏实地的科学。
陈相一下子崩溃了。他刚刚拼尽全力给予赵栋梁最大的信任和期望,而仅在短短2个小时后,就发现那人从头至尾都在欺骗他。赵栋梁是一个骗子,一个小人,一个26年来秉性未改的小人!
赵栋梁始终在钻研专业,但却特意在所有人面前呈现出一个神婆的形象,不惜被领导批评,被同事耻笑,陈相无法揣测出他的动机。陈相现在最在意的是,在第八次轮回中,赵栋梁明明有机会指出天气图的错误,但却毅然放弃,放弃张瑾玥和几万人的性命。他毫无责任感。
一瞬间,悔恨涌上陈相的心头。他让一个薄幸寡义之人去照顾张瑾玥,亲手把一个心思阴暗的人送到一身两命的妻子身边,那个人甚至对他抱有敌意。他做错了。
时间指向凌晨1点45分,陈相拔腿冲出值班室。距离风暴潮激振还有15分钟,陈德球的车还停在山脚下,他还有机会赶到张瑾玥身边。
台风的14级风圈已经靠近,毫无遮挡的山头上,人已无法正常行走。陈相被风扯着,踉跄着,从将近30°斜坡上顺着已积聚成流的雨水滑落到山下。气象台大门口,陈德球的车在风雨里飘摇,成堆的绿色小钢瓶全然不见踪影。
陈相拼尽全力坐到驾驶位上,拧上钥匙,无比虔诚地祈祷,祈祷凶恶的雨水能看在他的颜面上留有余地,不要全都被风灌入发动机里。
一下,两下,三下。颤抖地把钥匙转到第三下,脚下开始震动,发动机嗡嗡起鸣。浓到化不开的雨线中,这辆大屁股三厢车颤颤巍巍地出发了。
凌晨2点04分,陈相艰辛行驶到南桥河附近。这里一片漆黑,毫无人迹。紧接着,沉闷的巨响从远处传来,吓得他扶不稳方向盘。他清楚,那是赤坎河堤坝被炸除的声音。炸堤不是一个小工程,他想象不到是如何在几十分钟内实现的,只觉得感动。
在这个夜晚,他成功救下几万人的性命,只剩下一条生死未卜。赵栋梁究竟会怎样行动,陈相无从得知。也许他还怀有良心,如约把张瑾玥送进医院;也许他正躲在哪栋坚固的楼里,暗自享受玩弄人于股掌之中的快感。岔路口就在眼前,陈相本能地倾向后一种可能。他要驶向二横巷,驶向家。
方向盘的转动通过传动系统传到给车轮,两个前轮一齐向右侧偏转45度角,眼见就要实现一个利落的不减速过弯,可猛然间车轮抱死,方向盘也再也转不动。
陈相拼尽全力也无法掰动方向盘半分,水温表的指针正在迅速移向红区。紧接着,这架灵活的钢铁巨物彻底脱离他的掌控,像死了一般,任由狂风拉扯,失速,转向,倾覆,顺着从远方倾泻而来的淙淙水流,滑进河里。
水下,陈相以最后一丝力气爬出车窗。南桥河不是一条小河,不是一个旱鸭子能轻易应付得了的。他被捂在漆黑的水面下,连堤岸的方向都摸不到。
不知挣扎了多久,水面上的波浪渐渐小下去,月光洒下,一片亮晶晶的。水体分了层,下层温暖浑浊,上层寒冷清澈,它们交汇在一起,逐渐变得咸腥。
陈相漂在水底,能隐约看清月亮的轮廓,分辨出水面和堤岸。海水的侵袭让水体的密度越来越大,让已失力的他感受到托举。即便是在夏天,被台风抽吸上表面的深层海水也依然逼近0度,但他却感到周身都暖洋洋的,像被裹在襁褓里,被轻轻抱着。他回家了。
第一次,在意识的尽头,他的眼前没再闪回那些翻涌的回忆。像在一个无风的春日夜晚,睡了一个安然的觉。
沉睡的尽头,叫醒他的不是清脆的铃声,而是呜呜的风和冰冷的水流。
他在黑暗里缓缓睁眼,手机横在眼前,嗡嗡地震动着,碎裂的屏幕像火一般明亮,其上显示的时间被雨滴扭曲。时间显示为:
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