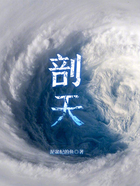
第28章 白色气球(三)
今夜的湛江市,注定不平凡。
凌晨12点半,陈相一行人已成功在瑞云湖附近施放一个气球,现在他们正驱车赶往瑞云湖北部,赤坎区内临近湛江水道的地方,放出第二个。
他们行驶在海滨大道上,有幸目睹台风淫威所造就的盛况。湛江水道附近的港口和渡口,比以往任何一晚都要喧嚣。
毫无遮挡的海岸线附近,风是永恒的。海洋和陆地之间的热力差异,致使海岸线附近永远存在一个日变化的环流,具体表现为在低空,白天风从海上吹到陆地,晚间风从陆地吹向海洋。
对于湛江水道附近的人们,夜间刮起偏西风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而今夜,港口上的调度员和桥吊司机照常面朝大海工作,陆风从后脑勺刮来,代表海风的东北风球却逐渐从信号塔上升起,塔身上亮起的一绿两黄信号灯,仿佛置身于一个不真实的梦。
紧接着,呜呜的风螺声抢夺一切注意力。预示风暴潮的风螺,鸣叫频率最高,比其它紧急场景中的鸣声更加刺耳。明明一切如常,收工返航的通知却以最快的速度扩散。
无线电台的水上专用信道一下子被占满,正在轮换休息的调度员也都被重新召集。已进港的船只被要求重新检查锚链,正在进港的秩序井然,还在远洋作业的也都调转航向,极速归港。
道路上,每隔一段距离,都设有一个交通指挥卡。卡旁站着或着便衣或着工装的人,举着喇叭,冲来往车辆喊话,喊他们离开这条能欣赏海景的路,躲开那些看起来还格外平静的海水。
海岸旁,大街小巷里,嗡嗡吊扇下沉睡的人,也都被扰了清梦。明明没下一滴雨,却有人叫喊着发大水,让他们都离开家,到安全地带避难。他们有的迷茫,有的恼怒,但最终全都信以为真。因为喊出这番危言的人,要么胸前有警号,要么胳膊上别着居委会的袖章。
凌晨12点40分,临近湛江水道的一片隐秘空地上,陈相迎着呜呜渐起的东北风,把氯丁胶乳气球坯子套在氢气瓶的出气口上,拧松阀门,把气球冲气到一人多高。任天富手忙脚乱为球炳挂上无线电探空仪,两人一同拽紧球炳,顺风摆好位置,倒数三声一齐撒手。
乳白色的气球急速升天,向西南方飘去,隐没入暗红色的云与水。在它移动的反方向,遂溪县逐渐亮起灯火。那里是东北部有低丘陵,其余三面地势平缓的宽广平原,既有繁华的集市,也有一望无际的甘蔗地。甜掉牙的砂糖和红糖在那里生产,远销全国。
在那里,被人从凉席上、毛巾被下拉起避难的农商,一定又悲又喜。悲是因为辛苦种植的甘蔗即将在丰收季来临之际,被不长眼的洪水冲倒冲散;喜是因为,他们还有来年。这本是属于赤坎区和霞山区的喜怒哀乐,却错误地让他们承受了。而在那些真正危难的地方,人们还在沉睡。
粗重刺耳的鸣笛声从不远处传来,那是停车在路边望风的陈德球给出的信号。凌晨12点45分,甩掉包袱的空载货车被狂风追赶着疾驰。从黑黢黢的无人区行驶到灯火通明的繁华地,车子停在人民医院附近,陈德球抱着气球胚心满意足地离开。
陈相从货箱里跳出,坐到驾驶位上。在他身边,任天富一直望向医院一楼一间窗户大敞并贴有白色瓷砖的小房间,满脸渴望。
凌晨1点02分,暴风雨吞噬一切。一辆甩着屁股疾驰的三厢货车出现在气象台大门口,它一个急转径直上山却一直打滑,甩出的水花飞溅很远。在水花落地的地方,并没有堆着墨绿色小钢瓶。它们早已被风吹散,不知滚落到何处。
凌晨1点04分,车子熄火在气象台大门口。陈相跳下车时,隐约闻到一股臭气,却又很快被泥土气息掩盖。他没有过于在意,只扒着各式树干和护栏顶风走到观测场里的铁皮房,从张勇手中接过潮湿的草稿本,护在胸前。
凌晨1点10分,狂风暴虐之时,本该肃清的户外有四个身影在移动。一个全力冲刺奔向主楼。两个紧贴在一起,步速缓慢。还有一个,像失了魂一样被雨墙任意推搡,走走停停,姿态扭捏。
凌晨1点15分,陈相坐在值班室的电脑前,浑身湿哒哒地滴不完水。他丝毫不理会赵栋梁的质问,只专心处理数据。自从下车之后陈相就再没看到过任天富,接下来的工作全部都要独自完成。
凌晨1点35分,模式运行完毕,结果符合预期,台风路径完全准确,暴雨中心出现在瑞云湖。他把这份无懈可击的预报产品递到张援朝手中,劝说张援朝炸堤。
期间,张援朝一直一脸怒气,无数次想要发问却都被陈相机关枪一样的嘴给堵回去了。陈相很清楚张援朝是要质问他一晚上都消失到哪里去了,可时间紧促,他不打算给张援朝机会。
这一次的劝说十分成功。张援朝被陈相牵着鼻子走,开始和陈相讨论炸堤治水的可行性。
“你的想法不错,可是容错率太低了!西有洪水,东有海水,水量还都不小。炸早了,洪水不往海里泄,只往赤坎区去,把那儿变成一片汪洋。炸晚了,洪水和海水撞在一起,溢出设计高度更低的南侧坝段,漫到霞山区去,把那儿给淹了。现在已经来不及撤离那么多居民,稍有偏颇,就要搭上许多条命。”
张援朝瞪着陈相把这段话说完,怒气和焦虑汇在一起,激得半边脸直抽搐。
“2点01,最晚2点05,这是风暴潮激振的阶段,在这个时间段内炸,保证成功。”
陈相这样劝说,神情笃定。早在11点多,张援朝就应该把他的预报结果递给水文队去跑耦合模式预报海浪了,虽然在那个结果中,降水预报有误,但台风路径整体上是准的,用来预报风暴潮绰绰有余。张援朝应该早就知道2点左右是风暴潮激振,他不应该如此犹豫。
张援朝既不认可也不反驳,只问出一个陈相无法回答的问题。
“你在11点多第一次提供给我的模式结果,用到的卫星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说完,他跳动的眼角安分下来,焦虑和不安也从脸上褪去,只剩下审视。
“你别管从哪里来的,你可以去和1点钟最新接收的对比验证它的准确性。”
陈相没有料到张援朝会把数据审核得如此仔细。数据来源的问题不可能如实正面回答。他不可能实话实说那份关键的数据来自未来,否则张援朝定会就此质疑自己提供的所有东西,让一切努力化为徒劳。
张援朝不表态,只沉默。沉默一会儿,开始翻电话本拾话筒。
“你相信我了是吗?”陈相连忙问,以一幅恳求的姿态,“我老婆现在在二横巷,霞山区地势最低的地方,她还大着肚子,我不会拿他们的命开玩笑。”
张援朝叹出长长的一口气,脸完全松弛下来,语气饱含无耐:“我相信,看你的面。”
凌晨1点50分,西二路派出所二横巷办事处内,早已被风撞得咣咣响的铁门被狠狠踢开。黄龙冲进屋,一把拽起睡眼惺忪的丁小幺,抬手狠扇了他一巴掌。
“抽风仔,鲁去死。给你打几个电话都不接,再不睁眼你就回家种地去吧!”
丁小幺一下子清醒过来,对上黄龙的怒目,一脸状况外。
黄龙一手掐上丁小幺的耳朵,大声喊:“刮台风,下暴雨,发洪水,要死人了!巷东头有个孕妇倒地上了,一地血。风太大医院暂时出不了车,让咱先行救助。人在小卖部旁边。”
丁小幺茫然应下,光着膀子往屋外冲,被雨淋个全湿后又返回来,问黄龙,“我一个人怎么救啊?我又不是医生!”
“我能不知道你不是医生? 2点多发洪水,好歹给人挪到安全的地方,别被水淹了。吃那么多饭搬个人不至于搬不动吧?”
黄龙一边说一边给丁小幺披雨衣,“这事交给你了啊,给我办好!赤坎河要炸堤,缺人手,我管不了你了。完事之后,别傻楞在原地,随便找个小二层的房子上房顶,记住没?”
丁小幺用尽全力消化掉黄龙的话,然后像往常那样和黄龙唱反调,“你一老寒腿的去什么水边?我去!你去搬孕妇吧。”
黄龙的怒气更重了,语气凶狠,“不管你认不认,我都是你师傅,是你上级!水边危险你知不知道?你要是不想卷铺盖回家种地,就老老实实的,别给我掉链子!”
“滚!”黄龙说完,照丁小幺屁股上狠踢一脚,确认他跑向正确的方向后,才又脚步匆匆地反向离开。
丁小幺冲到巷子上,才意识到安睡整晚的自己错过了什么。这场风雨非比寻常,风像刀,雨滴像锤子,砍砸在口鼻上,砸得他窒息。而本应沉睡的二横巷也逐渐变得喧嚣,巷子上立着几个西二路派出所的同事,举着大喇叭喊话,说马上要发洪水,让一楼和平房里的人就近上二楼躲躲。
他走得艰辛但还算顺利,顺利找到黄龙口中的孕妇。只是那孕妇的情况不像黄龙描述的那样惨。她倒在小卖部侧面的暗巷里,没有意识,但并不是一个人。于玲在守着她,用膝盖垫高她的头,避免呛水。
面对此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没有像于玲那样恐慌和崩溃。两人合力把人抬到小卖部的二楼,于玲一直在哭,哭得丁小幺心焦。
那孕妇出血很多,明显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了,丁小幺虽也心急但也无能为力。他现在十分挂念黄龙他们,赤坎河不是一条小河,暴雨天里水量一定很大,更何况按黄龙的说法,现在已经到了要炸堤泄洪的地步,可想而知河边有多危险。他一直看不起黄龙,但如今发现黄龙其实也看不起他,宁愿迈着两条不中用的老寒腿去充人头,也不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
于玲家里的挂钟指向2点05分,紧接着,远方传来沉闷的轰鸣。慢慢的,雨声越来越小,水流声越来越大。透过窗子,他看到浑浊的水流漫过整个巷子,水面升高,流动得也越来越急促,卷夹着各种垃圾和建筑碎片,漫过一楼小店半米高的入户楼梯。
正当他心中开始恐慌水面无限上涨淹没一切时,水流开始放缓,水面也不再升高。于玲哭得更加激烈,把贴在孕妇脸侧的手拿开,独自冲到楼下,不知给哪里拨出一个电话,然后开始哀嚎。
从她的言语间丁小幺得知,那孕妇咽气了。从未目睹过生死之景的他,不知该怎样做,只本能地觉得心痛。他想前去安慰却被窗外传来的喇叭声牵制住脚步。
寂静的夜空下,周遭的一切重回喧嚣。各种失真的喇叭声充斥耳间,用每秒340米的速度扩散一个又一个悲心的消息:
第三片区有伤亡,请求支援。
五区人手不够,过来帮个忙。
谁那里有电,给总队打个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