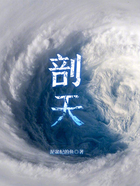
第21章 覃斗芒果一毛一斤(三)
凌晨1点10分,西二路派出所二横巷办事处里,丁小幺在一片黑暗中被惊醒。他从没铺褥子的钢丝床上坐起,闭着眼睛虚空摆手,“老黄我求你了,别拿芒果逗我,我忍不住!”
没人回应他。
吊扇在头顶不知疲倦地旋转,带出的风湿漉漉的,落在脸上,直痒痒。窗子不知被谁关严了,把不知何时下起的雨和阵阵疾遽的旋风拦在外面。
丁小幺逐渐清醒。老黄不在,办公桌上没有堆成小山的芒果,空气里充斥的是泥土味而不是浓郁的果香。
他大抒一口气,重新躺下,把身子蜷向另一侧,让被床压出红圈的胳膊松快松快。
这间小平房什么都好,就是没有空调。夏天的早晨,他总要手忙脚乱找自己在睡梦中脱掉的上衣。那时,老黄总是摊在他那把快要散架的竹椅上,一边把蘸上辣油的包子串往嘴里送,一边戏谑,“幺仔是想找媳妇了吧。昨天巡街,看见吴老太那糕点铺里新来一个捏面团的妹仔,长得水灵,介绍你们认识啊?”
老黄一把年纪了,还总爱开不着调的玩笑。被调侃得多了,丁小幺自是不乐意的,十有八次,他都会赌气一般放弃找衣服,打着赤膊冲到老黄跟前,把剩下的包子串全部拿走,坐在床沿狼吞虎咽。
这时,老黄又会换上一幅善气的面孔,“慢点吃,本来就是给你留的。看你这幅孩子样,贪吃贪睡的,以后准被媳妇嫌弃。”
对此,丁小幺会极为熟捻地反击,“不是你说的吗?能吃能睡是我的福分,吃包子比吃刀吃枪吃汽油弹强,睡床板比睡车屁股睡草窝睡棺材强,跟着你除了享福其它什么都不用考虑。”
老黄也不接话,依然笑盈盈地看他的幺仔吃完包子,把竹签子和塑料袋捏在手里,一边哼歌一边往外走。灰蓝色的短袖制服立立整整,后背上有三条褶,像刚从包装袋里拆出来一样,肩章上的一杠两星光亮亮的。
老黄全名黄龙,是丁小幺的师傅,从警30年,临退休了,依然只是个二级警员。丁小幺从警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黄龙手下,他打看到黄龙的第一眼就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丁小幺的悲观不无道理。黄龙顶着一个叱诧风云的名字,在西二路派出所做了一条最闲适的虫,守着辖区内最太平的片区,每天就是巡巡街,跟商贩唠嗑。偶尔解决一下纠纷,也不过是谁多占谁一尺摊位这种小事。
街市人杂,但即便遇到作风作浪的也轮不到黄龙出马。那帮商贩互相斤斤计较但一有事就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手脚不干净的人一般走不出店面就会被摁住,再难对付也就是一嗓子的事。在丁小幺跟着黄龙的这一年里,二横巷里发生过的最大的事就是有位流窜犯想吃一碗不要钱的牛腩面,面还没煮好人就被扭送到黄龙面前了。
闹市区如此,更不用说其他地方。被二横巷一分为二的几片居民楼里,大多是各种企事业单位的家属院,那帮斯文人好面子,家里吵架都不好意思大声。
所以,跟着黄龙的时间里,除了竹签串包子蘸辣椒油和虾饼只吃刚出锅的以外,丁小幺没学到其他东西,他从来不喊黄龙师傅,而是和西二路派出所里其他同事一样叫他老黄。
丁小幺清楚,黄龙表面乐呵呵,其实心里介意得很,否则也不会总提一兜青里透黄的覃斗蛋芒在自己面前吃。
丁小幺是北方人,平生第一次吃芒果吃得就是这覃斗的顶级蛋芒,核小肉厚入口即化,还有股椰奶与桂花的香气,甜得人想眯眼睛。来到二横巷的第一天,黄龙就招待他一大兜。他沉浸在果香里吃呀吃,一口气全吃完,越吃嘴越痒,还有点疼,一照镜子才发现,自己下半张脸肿得像山魈的红屁股一样。
这种只生长在雷州半岛西部沙土地的仙料他无福消受,一吃嘴就肿上好几天,一到夏天,就只能闻着满街的芒果味干吞口水。黄龙明知他过敏,却总要在他面前边吃边咂嘴,还时不时在他床头摆一个。
喧嚣的风雨里,丁小幺回忆着自己与老黄的过往逐渐入睡。那位淡泊明志随遇而安的顽皮老汉,已经攒满工龄随时可以退休了。有时丁小幺希望他早些走,这样自己也许会遇到一个有雄心壮志的新师傅。但有时丁小幺也舍不得他,因为得隙闲眠真可乐、吃些淡饭自忘忧的境界也是十足可贵的——在参加过几场同学同事的葬礼之后,丁小幺逐渐意识到这一点。
二横巷还是挺好的,除了芒果。丁小幺对自己的细碎念想做出总结,心满意足地回到没有芒果的梦乡,可没过多久就再一次被惊醒。
“覃斗芒果一毛一斤——”
纤细的叫卖声混杂在狂风骤雨间,送到丁小幺耳边时,已经弱不可察。但他确定自己听到的就是这句话,因为他的口水已经多到要在一分钟里咽三次。
于是,他穿戴整齐出门了。冒风冒雨的自是不好受,但他和老黄的职责就是守护二横巷乡里乡亲的一切:他们的命、他们的钱、他们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以及他们的好梦。
风雨比想象得要大。丁小幺穿过一片握手楼,来到二横巷还算宽敞的巷口时,才意识到这一点。二横巷是东北-西南朝向,此时正被一阵沿巷直吹畅通无阻的风贯穿,风砸在他身上,砸得他飘出几十厘米,一脚陷在没盖盖子的下水沟里,脚腕被水流拽着跑,劈出一个大叉。
这风像是刮了好一会儿了,而且出奇大。碎叶纷飞是夏日暴雨里的寻常之景,他早已习惯。让他感到惴惴不安的是同样卡在下水道里的灯牌,“劳保用品”四个大字早已熄灭,灯珠掉了几颗,背板上延伸出的电线在地面上来回扫。这家店上周刚刚翻修,装潢崭新,请的泥瓦匠和电工都是名头响当当的,做出的东西不应该这么脆。
他有些怕了,怕什么时候再砸下一块不长眼的招牌把自己带走,去见阴曹地府里的同学。那样多冤呐,死在刀枪之下是烈士,死在霓虹招牌下是笑话,清明节都收不到几束花的那种。
他想要挣扎起身,却发现一只脚被什么东西绊住。可他不敢改变姿态扭头察看,更不敢松开死扒砖缝的双手,否则一个不小心,整个身子跌进水流,定会顺着下行的沟渠被冲到不远处的南桥河里。南桥河可不是一条小河,至少不是一只旱鸭子能够对付得了的。
浑身的力气没处使,既尴尬又无奈。好在,祖宗先辈的照料再一次如期而至,几大团灯光逐渐靠近。他爷爷曾告诉他,小幺就是老末的意思,别看这名字不好听,可本命弱,外势就会强,遇到坎坷容易得到祖辈额外的庇护。
他曾觉得这种说法和把名字起成二柱和狗蛋孩子就会好养活没什么区别,但他现在体会到了,祖宗确实挺照顾他。灯光是一群人在打手电。傻子都知道躲雨,风雨交加的半夜,更不会有人想出门,那些人一定是冥冥之中受到召唤才来的。
不一会儿,有人脚步匆匆地靠近,把一把手电杵到丁小幺脸上,接着招呼人手忙脚乱把他拉了上来。
丁小幺揽着劳保店的立柱,喘了好一会儿气,待烙在视网膜上的光斑淡下去后,才定下神来,打量起眼前这群不安分的人。
他们全都披着各色雨衣,几人一组挤在一起挽着手,巷东头裁缝铺的张伯打头阵,身后跟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街坊四邻,有老人,有孩子,甚至总赖在二横小卖部前蹭人家摊位的残腿修鞋匠也坐着他的木头轮椅来了。
若不是越来越大的雨点砸得人脑袋疼,丁小幺还以为他们正提着花灯赶正月十五的庙会呢。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丁小幺问。
“去躲洪水!2点钟发洪水,喊我们到公园里去躲哩,快走吧!”张伯嗓音洪亮,语气焦急,激得丁小幺脑子里嗡嗡响。
“什么洪水?谁喊你们的?”
丁小幺心头发紧。他守着办事处的电话值夜班,发洪水这么大的事,他应该最先知道。他是睡得死,但也不至于一点都听不到那能吵死人的电话铃。就算他果真是被美梦勾心误了事,还有老黄和西二路派出所的其他同事呢。一定会有人一脚踹开办事处的门,把他从床上拎起来。
“巷东头大喇叭喊着呢!”张伯答,脚步没有停下,“快走吧,没剩多少时间了,我们这都是些腿脚不方便的人,不跟你一起磨蹭了!”
丁小幺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他确定发洪水的消息来源不是正经渠道,想要拦住这些在风雨里冒险的人。但他又怕,怕这已经把天下漏的大雨,真的能让南桥河里的水满到溢出来。
犹豫再三,他终于肯跺着脚动起身来,不过是往相反的方向,逆着人流往东边走。大晚上把一群老弱病残引出家门冒险,不论散布洪水消息的人居心何在,他都要去会一会。
逆风行进十分艰难,雨衣帽子被吹掉后,再也戴不上。雨水糊在口鼻上,产生一阵阵窒息感,让他像落水狗一样不住甩头。
他一个北方人,远道而来,艰辛地适应了永远潮湿的衣服,适应了回南天里会滴水的天花板,适应了拖布里长蘑菇,也适应了会飞的大蟑螂。但他第一次泡在这么大的风雨里,像在四九天里被街头混混堵在死胡同狠揍一顿,让他想要捂着脸跑回家缩在温暖的炕上一边吃猪肉炖粉条一边哭。
他从没这样委屈过,被人欺负了可以一拳打回去,可被天欺负了只能受着。街巷两侧的房子大都亮着灯,在这黑黢黢的夜里显得格外温暖。一路上他都想要钻进其中一家去暖暖身子,但终是忍住了,因为覃斗芒果的叫卖声愈发清晰,声源处立着一团灯光久久没动。
“覃斗芒果一毛一斤——今夜有洪水,请速到北桥公园山顶避难。”
喇叭声很大,大到甜美的嗓音在嗞嗞电流声中失真。在不知道听过多少遍后,丁小幺终于找到了他的目标。
一位瘦瘦高高的人窝在安铺糕点门口,一手揽立柱,一手举喇叭,手电筒掉落脚边,卡在皲裂的木制台阶的缝隙里。那人没穿雨衣,歪着头,把脸抵在柱后,以避开风雨的折磨,看起来比丁小幺还要狼狈。
丁小幺箭步上前,把手电筒杵到那人脸前,义正言辞地发问:“你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