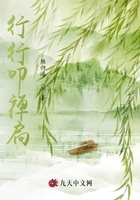
第18章 梨花酿⑸两相别
黑无常愤恨地掐了白无常一把:“黎平你个混蛋,碰到这么难缠的恶灵,每次都不帮我一把,害得每次都在那只山魈面前丢人。”
身边的白无常叹气:“技不如人有什么办法?何况这是人间,天庭定下的规矩,不能在人间使用咒法,你我再广大神通,仅凭这些没用的道具,又能维持及时。”
黑无常咬着舌头,指着他半天憋不出话来,“分明就是你……分明就是你”说个不停,白无常捏着锁麟囊,意有所指:“我们都有这么多了,还差三个而已,很快就能回地府了。”
黑无常按下头,急躁的话语不再脱口而出:“我的流浪人间啊,好不容易在人间集满四十七个魂魄,这都快饿瘪了,都没吃到一个生魂。”
白无常的眼底深不可测,他用独特的方式安慰黑无常道:“没关系,你又不是第一次让山魈逃脱了,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下次让严崇明那个家伙自己抓就行了,你人不行就别怪法器无名。”
黑无常更加想抽他一鞭了。
两人在和风细雨的夜里并肩而行,空寂的身后只有我楞楞的不能动弹,大概黑无常天生粗心,而白无常也并不想惯着他,兄弟俩每次出场都必杠,而黑无常口头声争不过弟弟,暗地里两人却很和谐。
最后两人遁地而走,我看着他们的渐影消失,看着山魈离开的方向,若有所思。
留在人间索性也没什么意思,不如找点事做。
我记住恶灵最喜欢群居了,如果我扮作同伴偷偷跟踪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清楚,黑白无常应该会念在恩情的份上,稍微对我好点吧……
就这样,我循着山魈拖沓的气息顺利跟上了她,我们魂魄身上都有种特殊的味道,这是属于某些被恶灵附身的魂魄,或长存于天地的魂魄,大概就是这么幸运,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山魈的老巢。
可是我没想到,噩梦才刚刚开始。
这只山魈的老家不在深山老林,而在远在酒香四溢的巷子里,这里的大多人都会酿酒,各家各户的酒各不相同,如虞美人、北雁塔、玉冰烧之类,因此当地人称“槐花巷”,槐花巷很窄,邻里间挨得很近,日常交流全靠吼一嗓子。
但西北方却有一座大宅子,已经荒废许久了,小院里存放的酒坛已经发臭,院子的杂草很多,其中却种着许多珍贵花卉,如百年一见的雪莲,遗世独立的决明草,称为稀世之宝的琉璃灯芯,可看出主人的用心。
山魈是从后面溜进去的,由于不通人识,门也是虚掩着的,这次机会我并没有趁机利用,而是选择了退而求其次,因为我觉得进来危险系数太高了,不是被山魈打个魂飞魄散,就是打个重级伤残,再加上孟婆的隐身术只能维持半柱香的时间,我就不敢赌了。
此时的我无比懊恼,当时怎么没有在海上好好护好十世镜的碎片呢,不然还能看看山魈的生平,顺便解答一下她心中的疑惑,可惜本来怀里护得好好的,在孟婆与摆渡人捉弄完之后,竟沉入了海底……
若十世镜没有被我打碎,转机估计也很大吧。
不过现在已经容不了我后悔了,我仔细考虑了一下,还是等这只老山魈觅食的时候再进来调查线索了,毕竟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况且我肚子也饿了,听黑白无常说,他们日常的吃食是生魂,不知道魂魄是否可以吞噬恶灵呢。
鉴于我的身份不方便,所以只好扮作黑白无常吓唬吓唬这些恶灵,不过大多数的恶灵都不好惹,都是他们反其道吓唬吓唬漂泊在外的生魂,不过还好,让我碰到几个胆小的,干脆就当点心吃了。
饭饱酒足,我打了个嗝渐渐有了睡意,我见天色透粉,大抵是远处的灯火熹微,于是美美的睡在了附近的老树上,没成想一觉醒来,被雨砸的脸生疼生疼的,竟神奇的发现,我的双腿消失了许多。
难道吃恶灵会让魂魄残缺?
难道使用咒法会受到诅咒?
我突然想起白无常说的那一番话来,一拍脑袋果然是真的。从此以后,我不敢再轻易动用咒法,看着一双残缺不全的腿,我的心里泛起感伤。
在树上守着山魈出来,我不知不觉地就陷入了美梦,也不知如何,自从重回人间就是如此留恋黄泉,虽然在那无边无际的沙漠之中,只有一个会颐指气使的大奸商孟婆,但是,我酿的沙棘酒还在那呢……至今没动一口。
天色渐明,我伸了个懒腰,还想着踩着地上的苔藓会滑倒,突然又想起一件悲伤的事情……
那山魈大概是出去了,我又循着她的气息溜了进去,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屋檐下空空的大瓮缸,大概是闲置在那里的,屋檐下隐隐的雨滴滑落,时不时敲打着瓮缸上的陶碗,发出有节奏的乐声。
首先进入的便是厅堂,这应该是主人落脚的地方,类似于小型书房,但墙上的壁画已经剥落,只有一地的粉尘,还有些书画霉变,画上的女子已然变形,眉心的朱砂痣失了色,衣服上的彩墨也晕开了,裱字画的架子开了也无人修补,卧榻上的棉被不见了,摆放的棉被早已不见,整个卧室散发着十分难闻的气味,我并没有多看一眼,捂着鼻子径直往里飘去。
接下来便是正厅,也许是主人家的品味独特,中间待客的地方竟摆着几把血红的木椅,木椅在敞开的窗,投射下的月光映象,看上去渗人的很。
然后是佛堂,佛龛旁的五排烛光湮灭,只有受人供奉的几排木牌,我扶着下颚端详起来,瞬间明白了,这是一户姓罗的人家,他们家因伐木而发家,上面写的都是逝去先辈的名字,但很反常的一点的是,不知什么原因,罗家举家迁徙去了更远的地方,走的匆忙以至于什么都来不及带,或者我有个更大胆的猜想……
——罗家被灭门了,以至于没有后人给他们立碑。
紧接着就是伙房,里面的草木灰已经变质了,后面堆着攒成捆的腐败木柴,厨具泛了铁锈,锅里的泔水还有,但有无数的老鼠在角落吱吱地叫着。
稍微让人舒服一点的就是书房,主人喜静,因此这里是一处僻静地,窗外有颗枇杷树,伸手便可以摘到,惋惜的是,树上的枇杷已经干枯发涩,还没来得及保存便被鸟儿吃掉了,案台上的香是浸在水里的,因此可以保证储存更久。
主人家的藏书不多,基本的四书五经还是有的,只是多了一些宝盒之类,大抵跟罗家的家世相关,才会铸造如此多的木盒,以盛放相当珍贵的宝物,我离开了这里,继续往外走。
池塘里的水已然泛青,可见没有园丁的照料,边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杂草,池塘里偶尔有几个窜动的影子,但水太浑浊了,根本看不清池里养了什么。
算算山魈出去的时间,我在空气中竟还没有嗅到那若有若无的气味,说明去了很久。我正打算往回撤,忽然在半路看到一个黑色的人影,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连忙躲到书房。不料蹭到了一个长方形的棠木盒子,那盒子“腾”地一下打开了,我料想终于找到蛛丝马迹了,连忙惊喜地察看,发现这竟是本日记,这是有关于罗家公子罗籍的生平叙事。
“庚子年七月初五,我携念初于西湖畔游玩,惠儿生性顽皮欲下水,一山魈忽下手伤人,我护住惠儿,无奈惠儿滚下山坡,额头中伤,大夫诊断要伴临终生,虽无甚大事,我心尤自责。”
“庚子年八月十五,正值中秋,我与念初本想出府逛汴洲,却在收拾行李时,遇到那日攻击惠儿的山魈,它哭闹着要与我团圆,惠儿当场吓哭,我与念初躲府中三日不出,方才幸免。”
“庚子年八月廿十,念初心疾难消,卧病在床,是故听闻山魈袭人事件,我欲上书但心不安,山魈纠缠数日,夜夜以鬼面视人,岳母居于府中告老还乡,半路翻下马车沉塘,我后悔不已,为时已晚。”
“庚子年九月一日,我与念初照常请安祖父,无奈山魈更加放肆,竟扮作出入侍从的丫鬟,掐住管家的脖颈威胁念初,将我换于她,我并不记得与山魈生过情面,管家被拖入池塘溺亡,下人打捞时已尸骨补全,呜呼!终是我之过。”
“庚子年九月初三,念初与我赌气,质问我与山魈的关系,我本想等念初冷静后解释,谁知山魈竟对惠儿大打出手,惠儿身上多处伤痕,最终撒手人寰。”
“庚子年九月十日,念初恼恨不已,终日食之无味,又听闻山魈当街啥壮年男子,吞食心脏,溺毙婴孩,我心生惧意,令其下加强管制,山魈重施旧技,吓得念初落气,我含泪与山魈争斗,脸又被山魈抓破。”
“庚子年十月廿十,府上人无故失踪,我向陛下禀明,陛下以谣言驳回,我见罗家无人生还,准备就此离去,念初与惠儿都已不在人世,我欲投身终南山作俗家弟子,半路被山魈袭击……”
后面的这一页突然被撕掉了。
我恋恋不舍地合上罗籍的日记,打包好放进木盒里,其中我是能感受到罗籍对于山魈的怨念的,还有山魈出现之前与妻念初、小儿惠儿一家人其乐融融,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山魈出现之后,罗籍忧心忡忡,念初一蹶不振,小儿闹腾不止,与原本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不难想象,罗籍生前有多么复杂的情绪,都是在遇见山魈之后。
可山魈跟罗籍究竟是什么关系呢?难道是前世的情人?
我收回了自己的思绪,生怕中了山魈的调虎离山之计,我快速从后门溜了出去,一路上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山魈的恨已经到了无法消弭的程度了,照罗籍说,是山魈杀害了所有人,如果罗籍还没有转世,他应该被山魈藏在哪里呢?
我的脑子一下变得古怪起来,我既想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又想做个旁观者,孟婆了却我的前尘后,黄泉关是短暂回不去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找到判官,给我的生死划上一笔,争取早日投胎做人。
而幽暗漆黑的地底深处,大殿之内却是灯火通明。
一袭黑袍的男子束着高高的发髻,整个人笼罩在黑暗中,只能看到勾起的唇角,和带着阴影的鼻翼。
女子抱拳而立,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样,始终红着脸低头不语,而黑袍男子的视线空洞,他看向桌上破碎的镜子,情绪没有丝毫细微的波动。
身后有一具鬼面具,巨大的鼻孔上挂着两副铜锁扣,铜铃大的眼睛死死注视着前方,严肃而具有威仪,而房间的布置很简单,堆得帙卷浩繁的书,桌上满是年代久远的卷宗,一扇透着白光的铁栅窗,四面八方都是通往地穴的门,略显危险的空间越发死寂,终是有个好听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孟婆,不要跟本王说你完全没有责任,本王赐予你十世镜,那是奖励你工作诚恳。不过那只魂魄也不可幸免。”
地上的女子稳下心来:“是,殿下管教的是,回头一定在黄泉关好好研究一下重塑十世镜的办法,请殿下放心,改日必将十世镜原封不动地还给殿下。”
男子叹息了一声,冷淡的声音终于回暖:“破镜终究重圆,罢了!你不必回翻阅那寥寥无几的孤本了,下次你做的好,本王再赏你便是。”
见阎王大人有大量,拂拂手表示不在意,孟婆稍稍定心,又听到这尊神仙点了点桌面,依旧用惯了风轻云淡的语气:“对了!你与那个摆渡人犯的事,别以为本王不清楚,本王只是念在你们对地府还算尽心的份上,给你们一份体面的活计,至于这个怎么罚,你心中有定数吧?”
孟婆心里一哽,听到这句话后更是不敢抬头:“殿下英明,释迦自愿领罪,释迦愿以百年忠守黄泉关为代价,换得花海永久安稳。”
“那……你私闯人间怎么算?”阎王冲她淡淡一笑,手中的念珠已然落地,他却不着急捡起来,而是继续看着镜子碎片的方向,如一尊雕塑的神佛。
孟婆如溺水的猫,一下子呼吸顿住了,试图狡辩道:“殿下,释迦在人间并没有胡作非为,也并没有使用法术,这点可以请判官佐证。”
阎王闭上双眼,身上有紫色的电流游走,孟婆讷讷不敢动,但阎王却没有因此暴怒,只是施用咒法捡起了念珠,孟婆看着念珠慢慢从半空扶起,恨不得把所有对不起阎王的事情都吐出来。
“你还留在这里干甚?”
阎王把念珠重新拿在手里,正过身抬起白花花的手,喝了一口水。
孟婆的注意力又开始挪移到杯子上:“殿下,释迦还有一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阎王觉得好笑,扯起好看的唇角,舔了一下被水润湿的唇:“既然你都如此说了,怎么还楞在这里不说话?”
分明每一句都是质问,孟婆却并不气愤,因为听殿下每次发言都如沐春风,每一句都是那么得体舒服。
她立即吞了口唾沫,肩膀下意识地缩了缩:“殿下,释迦不小心把忘川小馆毁了,请殿下借我一点银子,释迦这就把忘川小馆重新修订。”
阎王的语气还是漠不关心,好像自己的属下失去了家,是罪有应得。不过这个不小心可不是真的不小心,不然找阎王这个热心帮黑白无常抓鬼的性子,早就耐不住了。
见阎王没动静,孟婆扭了扭脖子,独自欣赏起殿下的美貌来,却不料阎王伸出三根拇指,俯身睥睨着跪在地上的孟婆。
孟婆不解其意,厚着脸皮说道:“殿下,释迦还是不明白。”
阎王夺声而出:“三年,这三年的俸禄给你扣了,其余的自己想办法。”
孟婆暗叫苦恼。
“是,释迦遵命。”
孟婆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三年啊……她要坑多少过路魂魄的银子,才能填饱自己的口腹之欲?这个谢秋娘还说我黑,她再黑哪有地府的最高管理者黑啊!
她微微福了福身,起身准备退下,然而在转身的时候,阎王又叫住了她:“哦,那个摆渡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孟婆十分纳闷,心里有十万个为什么也不能吼出声,倒是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
阎王有些发懵,肃清了两下嗓子,给自己找了个破借口:“地府公务繁忙,名录一千两百人,怎么可能个个都记得?”
孟婆就算暂且勉强相信吧,毕竟座位上的这位高官她得罪不起,目前找不到比他更大的神仙了,她只好毕恭毕敬地回答:“殿下,他叫阿九。”
释迦还感到奇怪呢,阿九向来与她不对头,殿下叫他是想问什么,难道是想再呵斥一顿吗?
见释迦楞了两秒,阎王的语气加重了几分:“还不传唤!”
孟婆下去了。
须臾之后,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大殿。
穿着粗麻,戴着斗笠,嘴里还嚼了根芒草在嘴里,他草草躬身,纵有十分的火气,到了这尊活神仙面前,一分也发不出。
“摆渡者……你…叫什么名字?”阎王低沉的缓缓启唇,他稍微迟钝了一小会,并不想让外人看出他的情绪。
阿九嘴里嚼着的芒草并未吐出来,反而铸就了他的含糊不清:“殿下又不记得我了吗?我是阿九,奈何桥畔摆渡的那个阿九。”
阎王看着那尊肃穆凝重的鬼面具,久久不能回过神来,阿九想,大概千年间变幻太多了,感情会淡,人心也一样,而他们这些传承者,作为地府的接班人,天庭给了他们千年不腐败的躯体,却没有给一个人该有的尊严与自由。
“殿下,阿九便是阿爹陈八尺的儿子,阿九诞生之日,我记得阿爹曾说过,您还在人间抱过我呢。”
阎王捻着手上肥厚叶子的蜘蛛草,忽然想到什么,忙补救道:“本王记得你,你是……你是……”
阎王眼神闪烁,过了好久才说道:“尘嚣十年,你的生辰宴上本王送了一对镯子对不对?”
……
阿九望了望头顶飞过的六只乌鸦:“……殿下,那是箬横,是阿九的枕头。”
两人的对话就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对下去,日出日落仿佛永远没有尽头,黎明的曙光也没有从此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