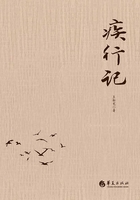
“学工”“学农”的日子
在初中的两年里,我先后参加过四次“学工”“学农”的活动。不说当时是什么政治背景,对我们这些稚嫩懵懂的学生来说,这成了走出校门看社会的人生第一步,能够与工人、农民朝夕相处,切身感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劳,“接受再教育”也确有裨益。
先说第一次“学工”。开学后不久,同学们就被分成了两拨,一部分到农村参加秋季农作物的抢收,我和其他同学在工宣队李师傅带领下,到了地处三元里的广州市蓄电池厂。三元里,这个地名大家都很熟悉,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当地103个乡民众反英侵略的英勇斗争,就发生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
该厂生产的是工业用蓄电池,是当年市里为数不多的工业名牌产品,也是每年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外贸产品。进厂后的第三天,厂长生动地给我们讲述了企业的发展史:就在脚下这块城北郊荒芜的土地上,通过十多年艰苦奋斗的历程,由几十个人发展到几百名职工的中型企业(以当年规模),从人工操作的笨重劳动到半机械化、全机械化生产,使我国此类蓄电池产品从原来单纯依赖进口,到不仅满足国内需要还成为出口的驰名商品,这巨大的变化实属不易。
在车间劳动中,让我感到最难受的就是浓烈的硫酸味,刺鼻呛喉得厉害。刚几天工夫,有的同学就不见踪影了,我坚持了下来。在“学工”结束前,我写了一篇约两千字的“学习小结”,工宣队的同志看过后,认为写得挺认真的,真实反映了“学工”思想认识,于是将它贴在了工厂的宣传栏上。
“小结”以“最高指示”开头,引用了两段当时使用频率很高的毛主席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三元里人民抗英纪念碑
“小结”的内容表述,自然脱离不开当时的“文革语言”,剖析自己的言行也多有自觉“上纲上线”,毕竟刚跨进中学校门才两个月呢,思想行为的幼稚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里面也蕴含着本质的,而且对后来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崇尚学习的精神和不怕吃苦的精神,说得更具体些,就是要使自己做到“学习靠自觉、进取有动力、吃苦能忍受”,这些成了我人生路上起步的垫脚石。
工业大道南端的广州市橡胶一厂,是我第二次“学工”的地方。它是广州市的重点大厂,主要生产“钻石牌”自行车轮胎,是当年我国主要的轻工业出口产品。
我被分配在硫化车间的质量检验组,这里是产品包装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我们的到来实际上是给工厂添了麻烦,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工人师傅依然对我们很热情。这里有一点和蓄电池厂很相似,就是车间的气味很难闻,每到硫化机开模出半成品时,整个车间都弥漫着“臭鸡蛋”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在“学工”期间,个别同学突发奇想地提出:为了向老工人学习艰苦奋斗的精神,要从家里步行到工厂,或从厂下班后步行回家,每天必须走这么一回。我也好强,心里想:“你们能走我也一样可以走。”从文德路到工业大道的金沙路,按当年的城市面积,几乎是跨过了半个海珠区。早上起来步行回厂是来不及了,我选择了下午放工之后,走慢点回家晚了也没关系。话虽这么说,走起来还是很累的,我想抄个近路,跟着同学在小巷里绕来绕去,这些地方从没来过,连方向都弄不清楚,结果是越走越远。还好,当时体力充沛,竟也坚持了下来。我现在回想起来是觉得挺可笑的,但这也不经意间成了润物无声的磨炼。
到了学工结束的时候,轮胎检验组的师傅送给我两本小红皮书,是“老三篇”和《毛主席哲学思想选编》。当我偶尔拿出来翻看的时候,工人师傅的音容笑貌,仿佛从过去的黑白照片里又浮现在眼前。
“学农”的地方是在花县(今为花都区)的松江村和巴江村,我们还曾在县农业中学旧址里住过。在计划经济年代,出于“备战、备荒”的需要,十多年来粮店卖的都是陈米,不知道在粮仓里搁了多久。凭“购粮本”的定量,每市斤卖0.146元,价格十多年不变。到农村后,我们没想到的最大快乐,就是能吃上当季下来的新米,煮熟了是亮白油润香喷可口,没有菜也能落肚三大碗,我当时真是在想,怎么会有这样好吃的白米饭啊!
整个连队五个教学班中,数我们班是最“理财有方”的。我和小何、小杜都来自文德南路小学,我们仨负责全班的伙食采购。在农村的那些日子里,每天早晨约莫7时许,同学们还在呼呼酣睡,我们已经浅一脚深一脚地走到了赤坭镇的集市。这几个人里我的经济条件算好的,带着同学进了喧闹嘈杂的茶楼,把肩上的挑子一撂,给每人要一碗排骨汤粉,每碗卖1角5分钱。那俩同学已经饿得急不可待了。等小店伙计端出来,只见厚实的土瓷碗里,铺满了新鲜排骨,雪白的米粉上泛着一层香喷喷的猪油,哎呀!真是肥而不腻爽滑可口。饱食过后,我们就蹲地倚墙闭目养神了。
“朝食”一过,南方的广东已经艳阳高照,脸上感到火辣辣的。地摊上本来水灵灵的毛瓜、白瓜和绿生生的通心菜、白菜等等,开始耷拉发蔫了,这时卖菜的老乡也越发着急,还得赶回去干农活哪。噢,时机到了,我向俩伙伴递了个眼色,讨价还价的“游戏”开始!他们论斤论筐地计较,我在旁听着,感觉到接受的底线了,点点头,就把一个摊档的瓜菜全买下来,我们悠然打道回府,农民兄弟也满意而归。
还有一招,就是和村里的知青们发展友好关系,用我们手里的粮票、油票与他们直接交换农副产品,“以票易物”,这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是没有的。双方各得其所,对我们来说不光“物美价廉”,而且就地取材,省了往镇上跑的奔波辛劳。
很快到了“学农”的最后一天。
我指着草棚木架子上装油盐酱醋的土瓦罐,问那俩“伙夫”同学:“这些怎么处理啊?”既拿不走,又不舍得留下送人,于是做了个人穷志短的决定:把剩下的黑砂糖、粗盐、菜油,一股脑儿全倒进正熬着红豆粥的大铁锅里。到开晚饭时,大家嚷嚷起来了:“哎呀,这粥什么味儿,怎么又甜又咸的?!”我们赶紧和盘托出,大家听后竟都领情也不埋怨了。不是吗,难吃也比没吃的好,何况落到肚子里谁也没吃亏啊。
唯独我们这个班,凡是交8.5元(全月伙食费)的同学都退回了2元,真是皆大欢喜。带队的工宣队长陈定兰师傅很惊讶,她疑惑不解地问我:“其他班级还要加收好几块钱的伙食费,你们班竟还有钱退?”听了这话,我心里一阵得意。
思之得
如果抽象地说向工人、农民学习,是不会有人站出来反对的,问题是学什么、怎么学?这看法就多了,想必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我觉得,应该学工农身上本质的东西。
那时候处于朦胧的年龄,还谈不上思想觉悟这一层,学“工农”随大流而已,充其量算体验社会生活罢了。当然也不必刻意必妄自菲薄,积极的因素还是有的。从大面上说,当年脱离了学生的实际,以荒废学业为代价,成了“形而上学”的积极实践者,方向当然就南辕北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