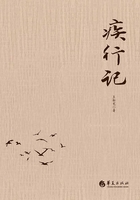
“复课闹革命”
1968年秋,我离开了先后两次就读的文德南路小学,到离家仅仅一里外的学校上初中,这就是广州市第二十五中学。

原广州市第二十五中学教学楼
学校,坐落在老城区的中心,处文德路西侧、文明路南面。学校前身为“大埔同乡会”,始建于1925年。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作“广东省女子师范学校”,抗战胜利后又改称“华南中学”。1955年,正式编定为“广州市第二十五中学”。2010年,合并到文德北路的第十三中学。
入学的那年,因“文革”的原因,已经停课很长一段时间了,由于学校秩序刚刚恢复,延迟到了11月初才正式开学。这要追溯到196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重要指示。11月26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强调“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到1968年秋,虽然大部分学校已经复课,但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大多数人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前行。作为学生,我们当时也想弄明白:是为了“革命”而复课呢,还是复课为了“闹革命”?有趣的是在40年前,鲁迅曾对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呼吁“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想想,这会是一回事吗?
当时,中学只设了初中部,我所在的教学班按序列编为“一连三排”,共有55名同学,其中男生27人、女生28人,分别来自文明路、文德路和回龙路的三所小学。我们的班主任是王玉琴老师,驻班工宣队员先是李永攀师傅,后来是陈定兰师傅。课室安排在老楼的二层,第二学年又移到了东侧新楼的首层。
新学年伊始,校方提出了第一个要求:每个同学都要自己动手做一个“忠字牌”。做法是用约25厘米宽、40厘米长的硬纸板做底子,外面裱糊上彩色花纸,上方贴上毛主席的头像,下方再嵌上一个巴掌大的“忠”字,这就算符合要求了。“忠字牌”制作完了以后,还要进行全班级评比,谁做得精美别致或有创意,除了老师给予表扬外,还能获得在全校陈列的“荣誉”。此外,学校还有一项硬性规定,就是人人要做课间操,作为每天的“规定动作”,而课间操又分两种形式,一是普通的广播体操,二是手拿“红宝书”跳集体“忠字舞”。
从1969年开始,广州市中学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等课程都恢复了,还增加了如“农业知识”一类的课,内容有农业“八字宪法”,教授农机、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方法等。这时候,“文革”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我仅存下来的几篇当年的语文作业,虽说是管中窥豹,也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燥热和喧哗。
这是1969年6月写的一篇作文,题目叫《胸怀朝阳干革命 大风浪里炼红心》。同年10月,又写了《工人宣传队好!》,用了两千多字的篇幅,讲述学校一年来各方面的变化,但内容与题目没有太多联系,通篇充满华而不实的豪言壮语:
时代的列车,朝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奔腾呼啸,滚滚向前!
革命的航船,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航道,乘风破浪,高歌猛进!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广州市第二十五中学,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人换思想校换装。在伟大祖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全校革命师生更是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以跃进的姿态跨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在作文《七·二三布告发布的日子》里写道:
天刚泛白,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开了门,是一个同志通知我们早上去开会,他说还要通知别的家。我望着他的背影,心中猜不知又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我回到学校,跟着队伍往越秀山体育场的方向走。队伍走得很快,我开始还可以跟上,走不多远就掉队了。到中山五路口,我已经是满身大汗,双腿发软几乎抬不起来。
各单位的队伍高举红旗陆续进场了。重型机器厂工人走那么远的路不怕辛苦到这里,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最听毛主席的话,雷厉风行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人民解放军列着整齐的队伍全副武装进来了,雄赳赳气昂昂,为我们有这样的革命队伍而感到自豪,让一切帝修反在我们面前发抖吧!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过来了,他们对毛主席有无限深厚的阶级感情,长年累月战斗在农业第一线,他们不愧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各行各业的队伍还在不断地进来……
大会在庄严的《东方红》歌声中开始了。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孔石泉同志宣布大会开始,顿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孔政委宣读了中央委员会关于山西问题的布告。山西省是我的家乡,对那里的问题我怎能不格外关心呢?当听到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反革命罪行时,我恨得咬牙切齿,全体革命同志也被激怒了,不断高呼:打到一小撮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愤怒的口号响彻了越秀山麓,使阶级敌人胆战心惊。七·二三布告大长革命人民志气,大灭帝修反威风,是对阶级敌人疯狂进攻的有力、坚决回击,它不但适用山西,而且适用全国。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提高革命警惕,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了。
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号召,在学校布置的功课中,“指鹿为马”的文章我也写过。比如《鼓吹的是什么东西——评毒草歌曲〈在松花江上〉》,全文共两千字,仅摘录开头一段,就可以看到是如何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来体现所谓“革命的批判性”的:
《在松花江上》以“九·一八”事变为历史背景,作于抗日战争初期。但是,这个作于一个如此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的文艺作品,却丝毫没有歌颂人民战争和表现中国人民同自己的敌人英勇斗争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而用凄凄惨惨的声调,把中国人民的伟大形象刻画成跪倒在敌人脚下、忍气吞声的亡国奴。这是一株狂热鼓吹国民党“亡国论”和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
这些当年“高大上”的语言,我没有原创的水平,基本上是从一些报刊、广播和文件中引用、改造过来的。在狂热的洪流中,没有人能独善其身,这种文字上的极端更不值一提了。要知道,当年人们不像现在人们提到那段历史时那么平静,而是争先恐后积极投身“革命”,要当不掉队的“革命造反派”。
当然,是不是“革命派”,也不是自己就能说了算,别人要根据“实际表现”,来鉴定你是属“革命派”“保守派”还是“骑墙派”。在珠江园院区里,凡是面积最大的住户,都要退出一间房,让住房困难的职工入住。我家住进来的是一对新婚夫妇。裴叔叔与父亲观点基本一致,他的妻子徐老师和母亲同属“另一派”。他们经常在客厅争论不休,甚至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也会争论几句。幸运的是,我们两家人几年下来都相处得很好。可笑吗?当时可是认真的。你看看1968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的文章吧,就引用了毛主席的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同年5月,两报一刊社论《乘胜前进》又提出“派别是阶级的一翼”,从理论上阐述派性的“客观性、正确性”。当然,在“派性斗争”中,也有动机不纯粹的,在对老干部使狠劲的人中,既有出于对“修正主义”的公愤的,也有因私怨而借机发泄报复的。
1970年的夏天,马上要初中毕业了。7月3日的那天,我参加了入团的“通表会”,介绍人是冯老师和阿容同学。同月27日,与其他同学一起正式宣誓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下面是“誓词”中的一段:
我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是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我坚决、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今后我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自觉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执行党团的决议,履行团员的义务,密切联系群众,做名副其实的共青团员!
我们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战争的时代,勇挑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重担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而又艰巨的战斗使命!我决心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当大跃进的闯将,为彻底埋葬帝修反而奋斗终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段誓词是全市统一的还是学校自己的,今天已难以考证。不管怎么说,它也成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学校生活的特殊印记,给许许多多同龄人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思之得
有人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也有人说“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所谓见仁见智。“文革”十年旷世浩劫,付出的是两代人的痛:中壮年,是旧中国的过来人,他们迎来了新社会的巨变,正年富力强厚积薄发;青少年,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大军,风华正茂正当时——可惜,多少青春年华被不期而至的“极左”思潮吞噬了。
相信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曾经发生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