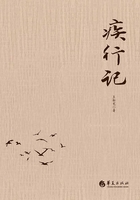
当上工人了
在街道打“散工”六个月后,来到了1970年的岁末。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下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市民政局承担起市革委会交给的任务,将近200名应届毕业的残疾学生,集中安置到其下的福利工厂。可能是家住在东山区的缘故,我被分配到地处东山口铁道旁的广州市东升电器厂。
当年,属于广州市民政局管理的福利工厂共有十二间,大致分为化工、机械电器、木材制品、缝纫制衣和其他等五个行业,主要产品有二十八种。据《广州市民政志》资料记载,当年创建这类工厂的目的,是为了组织市内残疾人、城市贫民、烈军属和荣复转退军人等民政对象实现就业,借此摸索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途径。
至今,我还保留着老厂子的一张旧信笺,上面印着“地址:东山署前路关园4号,电话:776259,供销电话:751531,电挂1346”。东升电器厂的前身,是市社会福利五金制品厂,成立于1958年5月28日。建厂初期,厂址设在广州市维新路340号,即现在的广州起义路165号址。1959年9月,搬迁至东山署前路关园。1965年1月,因试制交流电焊机成功,并成为厂主要产品,经上级批准,更名为广州电器五金制造厂。当年建厂的手续是严格完备的,由广州市民政局申报,经市计委正式批准成立。
话又回到了当年的12月,根据市革委会的有关要求,市民政局将我们集中在华宁里小学,办了一周的学习班,讲啥内容我完全忘了。记得最后一天是在民政局四楼礼堂,召开学习班总结会。学员阿关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表决心,显得很紧张,话说完了,离开时一下子把桌上的话筒绊倒在地,惹得会场“哄”的一阵笑声。
当上工人了,我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啊,心里有股捂不住的高兴劲儿。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最具权威的口号,能当工人就有发自心底里的满足,特别是在全民所有制的单位,还有些莫名的优越感。
第一天进厂是什么情景,我没有印象了,记得在民政局集中后,我们是二十多人一起乘车到厂的。在车上,我仅与身旁叫“马仔”的青年聊了几句,没有与其他人搭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40年后为了纪念这位我最早认识的、憨厚的伙伴,我在《三月风》杂志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就叫《马仔》。
一进厂里,感觉整个厂子真像个小社会,当时还没有“社区”这词,各车间可以说就是社区里的街道、胡同。我被分配到制造电器产品外壳的车间,当时也叫“箱壳班”。为什么当时许多工厂都把车间叫成“班”呢?我想是与提倡“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有关,当时许多学校、企业、农场的内部,设班、排、连,成了一种“革命”的时尚标志。
我的班长叫黄秀珍,她是个热情正直、快言快语的女强人。副班长是冯巨流,腿有残疾,人挺温和厚道的。他们相当于车间的正、副主任,既是车间里说一不二的指挥者,又是通情达理的带徒师傅。
我所处的生产环境是很艰苦的。南方夏天的热,那叫酷热,室内温度常常超过人的体温,外面是四十多度,把沥青路面都烤化了。车间内几乎没有通风设备,靠几台大功率风扇“呼呼”地吹,浑浊的空气被它来回搅拌着,弄得人头昏脑涨,温度却一点没降下来。待到了又冷又潮的冬天,又是另样的难受。车间的墙壁、机器设备和工具材料等等,能看到的东西都是冷冰冰的,它们把活人身上那点暖气都吸走了。我们实在熬不住了,就偷偷把废旧棉纱点燃,烤一烤那冻得生痛发硬的手,耳朵、脚趾经常长冻疮,又痛又痒难受极了。
只要开工的电闸一合上,车间噪声始终在80分贝以上,相距半米就听不清对方说话,把“震耳欲聋”用到这儿一点不夸张。地板上横七竖八的角铁、槽钢等型材,剪切后薄钢板的锋利毛刺,稍不留神就会把人绊倒或扎伤。每天下班后工作服沾满铁锈、油渍和汗斑,用毛巾往鼻孔一抠,能带出两个黑圈,全是工业粉尘。
生产柱上油断路器缸体、电焊机和变压器箱体,是厂里的重活脏活。我有时候累得两腿发抖,站都站不住了,顾不得难看一屁股坐在地上,实在是干不动了。师傅在旁看着,谁不辛苦呢,他毫无表情地劝道:“来吧,抽根烟提提神,这口气就歇过来了!”就这样,我从16岁开始,因“生计”所迫成了真正烟民。起初为了省钱,抽七八分钱一包的“百雀”“电车”香烟,转正后工资高了些,就买贵一些的,像两毛多的“丰收”这一类,已经算是享受上好烟了。
开始干的钣金工活儿,每天挥动铁锤不止上万次。约一年后,我感觉右手老是酸痛无力,于是到东山区人民医院就诊。我询问大夫是什么毛病,他捏了一下我的右手肘关节,又看了看我后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有没有长时间的机械动作?”哦,医生的话马上使我明白了。医生知道原委后说:“用手强度太大,关节过早劳损了。你想好得快就打封闭针吧,但会很疼,你忍得住吗?”我茫然地点点头。医生把我的右手向内作弯曲状,拿着比一般针头都要粗的针头,直接扎到肘关节的骨头缝里,哎呀太痛了!我眼泪都出来了。
一段时间后,班长分配我在车床加工柱上油断路器的缸盖,每个有三十多斤重。有的同志说,这么大的缸盖在一米多高的车床搬上卸下就够累了,加上老车床运转震动又大,如果稍不注意,就会出事故。又因为自己走动不灵活,干起来更吃力,但我考虑到艰苦的工作正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虽然累一点,还是一声不吭,坚持完成了生产任务。
这是我当时记下的另一工种的劳动感受。
话题转到中午时分的厂食堂,在这里,劳动者度过了短暂放松的快乐时光。工友们自觉地排着队,这里头有管理人员借此时机拉着职工说公事的,有打诨说笑的,也有绷着脸就等着填肚子的。食堂每顿收1角5分的菜金,提供没有油腥的青菜、三片薄得透光的肉片,大米是粮店专卖的,都是仓储了多年的陈米,这些都没有人抱怨。
工人阶级也有“觉悟”不高的时候。食堂大厅里经常有职工嚷嚷,源头是“分配不公”,彼此关系好的,伙房师傅“高抬贵手”多抖动一下,饭盒就多落得了一片肉。觉得吃了亏的人,指着食堂的小窗口骂:“妈的!等着吧,你们生的仔都没屁眼!”哎呀,这话骂得是够毒的。
骂归骂,其实里面的师傅还是挺尽力的,为改善伙食也绞尽了脑汁。我举一例:他们从市场低价买来北方人叫“下水”的猪大肠,不嫌腥臊难闻反复刮洗冲净,沥干水后抹上老抽酱油,再放到柴火上慢慢烤,熟后只见色泽金黄油亮,入口甘肥香脆,成了职工极爱的荤食,取其雅号“假烧鹅”,这是“短缺经济”逼出来的招啊。
南方的中午,无论寒天暑地,职工都习惯眯上一会儿。午饭后,大家都在第一时间抢占车间的凳子“据为己有”,我不好意思多占,就将三张二十厘米宽、三十厘米长的“日字凳”相对拉开点距离,头、身和脚各垫一张,就靠这两巴掌宽的小凳,半悬着身子躺下竟也睡着了。
我还有一些“自我放松”的时候。厂里开例行的职工大会时,我觉得无聊了,就将工友名字编成打油诗来取乐儿。偶尔生病医生给了假条,我舍不得在家休息,就到文德北路中山图书馆借阅《红楼梦》《西游记》《牛虻》等新华书店没卖的书,回来就和阿洪、小任这些“文学青年”讨论书中的章节内容、诗词歌赋,来比试、“炫耀”自己的阅读能耐。
其实,我在图书馆借阅最频繁的还是技术书籍。比如苏联在卫国战争前出版的《工模夹具高级教材(中文版)》,是当时国内能看到的也是工艺水平最高的教科书了,里面从简单模具到复合模具都有系统、翔实的介绍。由于书不能外借,遇到难题就得去查阅,我对馆藏这类书的索引早已烂熟于心。有些常用的技术书籍,在新华书店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比如我身旁备用的《机械制图》《五金机械手册》和《钳工手册》等等。
当工人手里出活儿是最要紧的。车间交给的生产任务,我大多都能提前完成,余下的工夫就去帮助别人。有时候任务很紧,也不会太急躁。黄秀珍师傅常对别人说,“新宪什么时候都咁老定”(粤语,镇定的意思)。也不奇怪,中学时班里同学都已经叫我“新伯”了,我当然不愿意有这个“称号”,无奈那时已经有点少白头,加上又是班长,老师经常在外集中学习,遇事我得拿出主意。
时间到了1975年9月1日,黄师傅接到通知,要调到喷漆班当班长了,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工作需要,厂部决定自己从今天起担任班长,此事的确出乎我的预料,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自己在这个车间工作四年多了,可是对管理的事注意得不多,许多问题都是门外汉。困难是有的,但有一条,就是组织上决定了的事,须先照办,并办好。我想有一天,当不需要当班长的时候,再写一篇略长的日记,谈谈收获和想法。”
20世纪的七十年代,是计划经济的鼎盛时期,老百姓戏称社会上有“三件宝”:医生、司机、猪肉佬,和他们拉上关系好处多着呢,医生可以无病开出假条、司机可以用公车帮拉私货,肉铺师傅能多给些肥肉、杂碎什么的,他们都能给亲戚朋友带来“实惠”。车间有的人干活没有啥积极性,借口说厕所“客满”,跑到厂外的公共厕所,逛一圈个把小时才回来,连厂长也觉得奈何不得,这厕位“供不应求”也是实情。有的还经常“装病”,到记账的延安路卫生院弄假条,这些成了一些职工长期心照不宣、乐此不疲的准“福利”。
那时候工人眼里还有一种“实惠”,就是停电。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广州严重缺电,工厂实行每周“开四停三”,而且供电局还会随时拉电闸。当隆隆轰鸣的车间突然静下来时,工人们欢声鹊起,这意味着可以歇啦,甚至能回家了!可是当用电恢复了,他们又拼命把耽误的活抢回来。这种现象着实令人费解,在这“特殊的年代”,人们的心态往往是扭曲的,但工人师傅身上的责任心和是非观念,对自身行为起了压舱石的作用。
思之得
“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
这是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自己还是普通工人的时候,就反复学习过。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看,通过周而复始的学习与实践,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实现自我革新、自我完善,在与时俱进的当今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