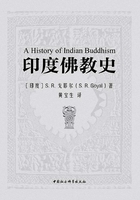
序言二
佛教是沙门传统的一个分支。它的早期源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多年,是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好几种争论集中围绕沙门传统的性质和古老性。沙门的历史和哲学的许多问题还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虽然几十年来学者们作出不懈的努力。甚至沙门 这个词的词源和原义都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个词的词源和原义都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
正如希腊的telos和吠陀的 ,似乎
,似乎  原初是一种游荡者传统。源自印欧语系的
原初是一种游荡者传统。源自印欧语系的  ,沙门的原义,samana是一个游荡者。这从《百道梵书》的好几个段落得到证实,在那里,词根
,沙门的原义,samana是一个游荡者。这从《百道梵书》的好几个段落得到证实,在那里,词根  的动词形式与 car(“移动”)配搭,如
的动词形式与 car(“移动”)配搭,如 (1.2.5.7,1.6.2.3,1.5.3.3等),
(1.2.5.7,1.6.2.3,1.5.3.3等),
 (1.8.1.7,1.8.1.10,25.1.3,3.9.1.4,11.1.6.7等)。《游荡赞》(《泰帝利耶梵书》8.15)中的一首诗清楚地提供这种意义:
(1.8.1.7,1.8.1.10,25.1.3,3.9.1.4,11.1.6.7等)。《游荡赞》(《泰帝利耶梵书》8.15)中的一首诗清楚地提供这种意义:
asya sarve 
 prapathe
prapathe 
所有他的罪恶通过
在路上游荡而灭除。
其中的 意谓“游荡”。
意谓“游荡”。
 与游荡联系也见于《梨俱吠陀》少数颂诗,如
与游荡联系也见于《梨俱吠陀》少数颂诗,如
 ,即一个步行的游荡者。
,即一个步行的游荡者。
为了确定 ´ 的含义,研究印欧语系中的同源语很有用。粟特语的 šmn 或 šrmn,于阗语的
´ 的含义,研究印欧语系中的同源语很有用。粟特语的 šmn 或 šrmn,于阗语的  ,古典希腊作者的sarmanoi,都意味佛教比丘,确实是后期借用俗语
,古典希腊作者的sarmanoi,都意味佛教比丘,确实是后期借用俗语  。斯拉夫语的 šamana 意味祭司、医生、巫师和驱邪的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早于俗语的词。但是,吐火罗语 A 的 samam和吐火罗语 B 的
。斯拉夫语的 šamana 意味祭司、医生、巫师和驱邪的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早于俗语的词。但是,吐火罗语 A 的 samam和吐火罗语 B 的 ,两者意味“行动者”(有别于吐火罗语在佛教比丘意义上的šaman一词),肯定是早于俗语的用词。在伊朗语传统中,帕提亚语cam(“跑动”)和波斯语
,两者意味“行动者”(有别于吐火罗语在佛教比丘意义上的šaman一词),肯定是早于俗语的用词。在伊朗语传统中,帕提亚语cam(“跑动”)和波斯语 (“跨步”)可以联系亚美尼亚语的 cemaran,贝利(Bailey)译为游荡者集会,以及 cemkan(祭司)。
(“跨步”)可以联系亚美尼亚语的 cemaran,贝利(Bailey)译为游荡者集会,以及 cemkan(祭司)。
在这个语境中,芬兰-乌戈尔语族的shaman一词在祭司的意义上很重要。乔吉(Aulis J.Joki)已经充分研究芬兰-乌戈尔语族和印度-伊朗语族之间词汇的相似性。苏联学者阿巴耶夫(V.I.Abayev)和阿西诺夫(M.S.Asinov)也在这方面作出进一步研究。试图依据语言、语音和语法特点对这两个语族互相接触的编年史研究,赫莫特(J.Hermatta)已经发表许多成果。贝利也提到雅利安语与芬兰-乌戈尔语族之间词汇相似性。这些词汇互相借用无疑表明可能在前于《梨俱吠陀》时期的很早阶段印度雅利安语和芬兰-乌戈尔语族之间的接触。依莱亚德(Mircea Eliade)和斯泰尔(Fritz Stall)近年来竭力将斯拉夫地区的萨满教与早期印度文化相联系。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他们提供的证据。
这首先表明  是一个游荡者。其次,游荡被认为是一种宗教实践。最后,这是最重要的,
是一个游荡者。其次,游荡被认为是一种宗教实践。最后,这是最重要的, 实践流行于原始吠陀时期。
实践流行于原始吠陀时期。
沙门( )具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印欧语系中的游荡者群体的形象。像
)具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印欧语系中的游荡者群体的形象。像  一样,吠陀的
一样,吠陀的 源自词根car(“移动”),最初是一个吠陀游荡者的组织。但是,不像
源自词根car(“移动”),最初是一个吠陀游荡者的组织。但是,不像  ,吠陀的
,吠陀的 崇拜各种天神。他们吁请诸神,向他们供奉祭品。在原初的
崇拜各种天神。他们吁请诸神,向他们供奉祭品。在原初的 中,祭祀由祭司(
中,祭祀由祭司( )履行简单的仪式,吁请天神和供奉祭品。
)履行简单的仪式,吁请天神和供奉祭品。
吠陀文献表明 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原始义当然是游荡者群体,其次的含义是一起游荡和居住,即确立暂时的聚居地,崇拜各种天神。这样,在《梨俱吠陀》(9.113.8)中,一个祈求者希望居住在神圣的
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原始义当然是游荡者群体,其次的含义是一起游荡和居住,即确立暂时的聚居地,崇拜各种天神。这样,在《梨俱吠陀》(9.113.8)中,一个祈求者希望居住在神圣的 (“游荡者群体”)中,维婆斯婆多王统治的天国领地中。在后期文献中也提到神圣的
(“游荡者群体”)中,维婆斯婆多王统治的天国领地中。在后期文献中也提到神圣的 。在《百道梵书》(4.4.4.5)中,在完成祭祀后,受邀的众天神遣散他们各自的
。在《百道梵书》(4.4.4.5)中,在完成祭祀后,受邀的众天神遣散他们各自的 。还有,在这部梵书(4.4.4.17)中,提到楼陀罗的
。还有,在这部梵书(4.4.4.17)中,提到楼陀罗的 越过摩遮凡山。
越过摩遮凡山。
然后, 表示敬拜和祭祀天神的特殊方式。在好几处,说到“如同天神的习惯,凡人也是这样”
表示敬拜和祭祀天神的特殊方式。在好几处,说到“如同天神的习惯,凡人也是这样”
 。应该注意到,这种说法出现在规定各种小型祭祀仪式的语境中。这些宗教实践代代相传。“一位仙人祈祷:‘如果在祭祀仪式
。应该注意到,这种说法出现在规定各种小型祭祀仪式的语境中。这些宗教实践代代相传。“一位仙人祈祷:‘如果在祭祀仪式  中记忆
中记忆  失灵,出现疏漏,火神啊,请保护我们!'”(《阿达婆吠陀》7.3.1)
失灵,出现疏漏,火神啊,请保护我们!'”(《阿达婆吠陀》7.3.1)
最后, 转变成吠陀集会中的祭司,诵习和教导各种吠陀传本。
转变成吠陀集会中的祭司,诵习和教导各种吠陀传本。
注意到拉丁语词根colore=梵语car,从游荡转变成聚居地,最后转变成崇拜,与 的词根car从游荡转变成聚居地,最后转变成崇拜诸神平行,也是有趣的。
的词根car从游荡转变成聚居地,最后转变成崇拜诸神平行,也是有趣的。
如同拉丁语的colore和梵语的car,希腊语的telos也源自印欧语系的quel,它的派生义是人民、祭司群体、入会仪式以及社会和神秘仪式。莱赫曼(Wilfred P.Lehmann)指出:“如果telos反映早期的人民甚至部族的用词,我们在telestos中有这类组织的残留痕迹,入会者,祭司。……相关的形式如 telete,即‘神圣的祭供’和它的复数形式,即伴随有神秘仪式的‘节日’,支持这种解释。”(《原始文化中的语言音变证据》,见《印欧语言和印欧人》,第9页)
莱赫曼简要地指出的这一点需要详细说明。我们会在别处讨论这个问题。总之,可以说 telos 原初表示早期希腊的游荡者组织。为准许入会者举行入会仪式。如同 ,它最后转变成举行社会和神秘仪式的祭司群体。
,它最后转变成举行社会和神秘仪式的祭司群体。
这样, ,游荡者(colore)—聚居地—崇拜,游荡者组织(telos)—祭司群体(telestos),表明从原初的游荡者向崇拜天神者的转变过程。共同的传统祭神仪式是这些组织的基础。
,游荡者(colore)—聚居地—崇拜,游荡者组织(telos)—祭司群体(telestos),表明从原初的游荡者向崇拜天神者的转变过程。共同的传统祭神仪式是这些组织的基础。
转回到沙门  传统,我们可以指出,在《阿达婆吠陀》(11.1.30)中,提到可能前于梨俱吠陀的三种古老的宗教传统。“人们通过游荡
传统,我们可以指出,在《阿达婆吠陀》(11.1.30)中,提到可能前于梨俱吠陀的三种古老的宗教传统。“人们通过游荡  、煮食(
、煮食( ,即供给祭司饭食)和榨苏摩汁
,即供给祭司饭食)和榨苏摩汁  登上天国之路。”当然,榨苏摩汁无疑是在伊朗人、印度人和在亚加亚曼尼亚铭文中提到的塞种人流行的早期雅利安人传统。《梨俱吠陀》(4.33.11)中偶尔提到游荡传统,“除非完成游荡训练者,否则不能成为天神的同伴”
登上天国之路。”当然,榨苏摩汁无疑是在伊朗人、印度人和在亚加亚曼尼亚铭文中提到的塞种人流行的早期雅利安人传统。《梨俱吠陀》(4.33.11)中偶尔提到游荡传统,“除非完成游荡训练者,否则不能成为天神的同伴” 
 。这个观念在《泰帝利耶梵书》(33.3)也有反映:“因陀罗是游荡者的朋友,你就游荡吧!”
。这个观念在《泰帝利耶梵书》(33.3)也有反映:“因陀罗是游荡者的朋友,你就游荡吧!”
 因此,《梨俱吠陀》颂诗中的
因此,《梨俱吠陀》颂诗中的 (“游荡者”)应该解释为梵书这半行诗中的
(“游荡者”)应该解释为梵书这半行诗中的 的意义。可以注意到这首诗的含义是赞扬游荡实践,开头提到
的意义。可以注意到这首诗的含义是赞扬游荡实践,开头提到 ,即完成游荡
,即完成游荡  训练的人。“光荣不属于没有完成游荡训练的人。”
训练的人。“光荣不属于没有完成游荡训练的人。” 

原初的沙门传统除了游荡外,还以梵行和苦行为特征。在巴利语文献中,梵行(brahmacariya)几乎是沙门性  -或 沙门
-或 沙门  的本质的同义词。这首诗表达获得沙门性,常常出现在尼迦耶中,如《中尼迦耶》(2,第66页):
的本质的同义词。这首诗表达获得沙门性,常常出现在尼迦耶中,如《中尼迦耶》(2,第66页):
khnā jāti vusitam brahmacariyam
katamkaranīyam nāparam itthattāyā
生已灭寂,梵行完成,
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还有,批判邪说,说是如果邪说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接受荒谬的做法,甚至没有梵行,也能获得沙门性。
“我们两个,一个修习梵行,一个不修习梵行,而同样获得沙门性。想到这样,他抛弃修习梵行。”
 ,《中尼迦耶》,2,第101—123页)
,《中尼迦耶》,2,第101—123页)
里斯·戴维斯以及伯鲁阿(B.M.Barua)追随他,认为“沙门或比丘群体源自梵行者”。至少可以很有把握地断定梵行是沙门修行的最本质部分。在这方面,戈耶尔博士正确地注意到《阿达婆吠陀》中的梵行者崇拜。
比丘的实践确实与梵行相联系。比丘(bhikkhu)这个词一般译为托钵僧(mendicant)。mendicant源自mendicus(“穷人”)和mendus(“受责备者”),而mendicant是行乞的穷人和受责备者。另一方面,比丘  希望分享(
希望分享( 是bhaj即“分享”的派生词)大地的产物,因为大地实际上也属于他。《阿达婆吠陀》(11.5.9)中说“这个广阔的大地和天空,梵行者首先用作乞食
是bhaj即“分享”的派生词)大地的产物,因为大地实际上也属于他。《阿达婆吠陀》(11.5.9)中说“这个广阔的大地和天空,梵行者首先用作乞食 ”。
”。
游荡  的实践与苦行(tapas)关系紧密。在《阿达婆吠陀》(4.35.2,6.133.3,10.7.36等)中有好几处,游荡
的实践与苦行(tapas)关系紧密。在《阿达婆吠陀》(4.35.2,6.133.3,10.7.36等)中有好几处,游荡  和苦行(tapas)连用。此外,从活命派到佛教的各种派别,显然是沙门传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苦行被不同程度地接受为修行的核心行为,由此表明它们形成原始沙门传统的一部分。
和苦行(tapas)连用。此外,从活命派到佛教的各种派别,显然是沙门传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苦行被不同程度地接受为修行的核心行为,由此表明它们形成原始沙门传统的一部分。
沙门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是苦行者,源自askein,即通过折磨身体的方式进行自我修炼。苦行者(ascetic)这个词源自希腊语aske-tikos,拉丁语asceticus,意谓身体训练, (Strabo,15.1.61)是一种宗教实践。苦行(tapas)同样表示通过折磨身体的方式自我修炼。意味苦行的tapas不应该与意味热的tapas混淆。这是同音词,含有不同的意义,源自不同的词根。tapa 作为折磨,与古斯拉夫语tep(“打击”,BSOAS,26,1963)、巴列维语
(Strabo,15.1.61)是一种宗教实践。苦行(tapas)同样表示通过折磨身体的方式自我修炼。意味苦行的tapas不应该与意味热的tapas混淆。这是同音词,含有不同的意义,源自不同的词根。tapa 作为折磨,与古斯拉夫语tep(“打击”,BSOAS,26,1963)、巴列维语 (“毁灭”)和现代波斯语
(“毁灭”)和现代波斯语 (“毁坏”)相联系。当然,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词在《梨俱吠陀》中的全部使用范围,但我们偶尔可以注意到 tapana(《梨俱吠陀》10.34.7)是一种折磨人的工具,类似刺棒
(“毁坏”)相联系。当然,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词在《梨俱吠陀》中的全部使用范围,但我们偶尔可以注意到 tapana(《梨俱吠陀》10.34.7)是一种折磨人的工具,类似刺棒  ,能刺进
,能刺进  肉、伤害(nitodana)身体。在另一首颂诗(10.33.2)中,tap用于表示老鼠咬肉。
肉、伤害(nitodana)身体。在另一首颂诗(10.33.2)中,tap用于表示老鼠咬肉。
在《梨俱吠陀》中,几乎没有苦行或折磨身体作为宗教实践的证据。然而,在《阿达婆吠陀》中,苦行被认为是通向精神实现之路。当然,在原始的沙门传统中,苦行是一种重要的成分。
原始的沙门传统是前于梨俱吠陀雅利安人的传统。不像其他印欧人的游荡者( 和telos),它既不与天神,也不与任何仪式相关。它也没有经典文献。可以肯定地说,它以梵行和苦行为特点。沙门僧团包含老师和他的学生,像哲人那样持续讨论关于真实的问题,乞食和随处游荡。
和telos),它既不与天神,也不与任何仪式相关。它也没有经典文献。可以肯定地说,它以梵行和苦行为特点。沙门僧团包含老师和他的学生,像哲人那样持续讨论关于真实的问题,乞食和随处游荡。
与以神为中心的游荡者( 和telos)相比,沙门组织围绕称为阿罗汉(arhata)和祖师
和telos)相比,沙门组织围绕称为阿罗汉(arhata)和祖师  的导师发展。
的导师发展。
arhata源自梵语词根arh>印欧语词根algu,主要是产生经济意义的词,如希腊语alphe-alphano、伊朗语arjah和梵语argha,都意谓价值和有价值的。与这相关联,有一连串词表示有价值的和值得尊重的意义。
但是,在早期阶段,可能在印度-伊朗人阶段,arhata这个词或它的同源词获得一种宗教含义。
在《梨俱吠陀》中,arhata这个词一般表示值得崇拜的和值得尊敬的,而特殊地表示火(Agni,或火神),是履行祭拜天神职责的人类祭司的原型。这样, (2.3.1,“让火成为arhan,祭拜诸神”),或者,
(2.3.1,“让火成为arhan,祭拜诸神”),或者,
 (2.3.3,“你是arhan,比人类祭司更古老,我们心中渴望祭拜诸神”)。
(2.3.3,“你是arhan,比人类祭司更古老,我们心中渴望祭拜诸神”)。
 这个词源自areg=arh,这是arhat的阿维斯陀语形式,出现在《耶斯纳》(Yasna,53.9)中,
这个词源自areg=arh,这是arhat的阿维斯陀语形式,出现在《耶斯纳》(Yasna,53.9)中, arejis(“随同异教徒,仇恨导致谴责值得尊敬者”)。巴托罗迈(Bartholomae)在他的《词典》(第34页)中,指出这些
arejis(“随同异教徒,仇恨导致谴责值得尊敬者”)。巴托罗迈(Bartholomae)在他的《词典》(第34页)中,指出这些 是预言家和他的学生。塔罗波雷瓦拉(Taraporewala)告知我们在琐罗亚斯德波斯人中有个家族名为
是预言家和他的学生。塔罗波雷瓦拉(Taraporewala)告知我们在琐罗亚斯德波斯人中有个家族名为 ,意谓“信仰者”。
,意谓“信仰者”。
在巴利语和半摩揭陀语中,阿罗汉(arhat)是一个觉悟者,类似预言家的精神导师。佛音( )在《如是语经注疏》
)在《如是语经注疏》 中提供一个想象的词源,但也使他的含义变得清晰:
中提供一个想象的词源,但也使他的含义变得清晰: (“阿罗汉毁灭轮回的轮辐”)。同样,在《达婆拉注释》
(“阿罗汉毁灭轮回的轮辐”)。同样,在《达婆拉注释》 中,将arhat解释为
中,将arhat解释为 (“由于杀死表现为污垢的敌人”)而称为“阿罗汉”(arihanta)。
(“由于杀死表现为污垢的敌人”)而称为“阿罗汉”(arihanta)。
这样,这个词的古老可以追溯到印度-伊朗人时期,沙门传统几乎接受它的阿维斯陀语含义,虽然俗语和巴利语语法家和注释家已经忘却它的原始意义。这本身就具有历史意义。
像阿罗汉(arhat)一样,祖师  一词也是历史悠久。源自词根
一词也是历史悠久。源自词根 ,
, 或
或 的原始意义是浅滩或桥梁。虽然在吠陀文献中没有明显提到,但桥梁在各种印欧语传统中已经变成一种重要的精神象征。我们可以从最早的拉丁语语法家瓦罗(M.T.Varro)说起,他活跃在公元前二世纪。他解释大祭司(pontifices)的词源和原始义,说这个词最初意谓架桥者。他接着说“通过他们,即pontiffs,首先在桥墩上架桥,同样由他们反复修缮。与此相联系,在台伯河两边举行规模不小的仪式”(De Lingua Latina,5.83)。这座木桥在罗马旁的台伯河上,由马修斯(AncusMarcias)建造,这是历史事实。伴随架桥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古典语文学家正确地观察到这座桥在这里象征这个世界联系下一个世界的通道。尽管如此,这种仪式属于建造台伯河上这座物质的桥。
的原始意义是浅滩或桥梁。虽然在吠陀文献中没有明显提到,但桥梁在各种印欧语传统中已经变成一种重要的精神象征。我们可以从最早的拉丁语语法家瓦罗(M.T.Varro)说起,他活跃在公元前二世纪。他解释大祭司(pontifices)的词源和原始义,说这个词最初意谓架桥者。他接着说“通过他们,即pontiffs,首先在桥墩上架桥,同样由他们反复修缮。与此相联系,在台伯河两边举行规模不小的仪式”(De Lingua Latina,5.83)。这座木桥在罗马旁的台伯河上,由马修斯(AncusMarcias)建造,这是历史事实。伴随架桥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古典语文学家正确地观察到这座桥在这里象征这个世界联系下一个世界的通道。尽管如此,这种仪式属于建造台伯河上这座物质的桥。
在阿维斯陀神话中,经常提到分界  桥。在《阿维斯陀》中,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报告阿胡拉·马兹达
桥。在《阿维斯陀》中,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报告阿胡拉·马兹达 说:“我将引导他们崇拜你,我将与他们一起通过分界桥。”(《耶斯纳》46.10)
说:“我将引导他们崇拜你,我将与他们一起通过分界桥。”(《耶斯纳》46.10)
值得注意的是琐罗亚斯德负责护送马兹达崇拜者通过分开两个世界的桥。伊朗学学者相信分界桥神话前于琐罗亚斯德,而被这位预言家采纳。
在《梨俱吠陀》中,没有提到这样的分界桥。但是,在奥义书中有好几处出现分界桥的观念。例如,《歌者奥义书》(8.4.1)中, (“现在,这个自我是桥,为了保持这些世界不分离”)。奥义书中的分界桥观念也是后期在外来影响下引进的。无论如何,这是像琐罗亚斯德这样的预言家保障从这个世界通过这座桥。祖师、架桥者或制造浅滩者都可以比拟这样的预言家。
(“现在,这个自我是桥,为了保持这些世界不分离”)。奥义书中的分界桥观念也是后期在外来影响下引进的。无论如何,这是像琐罗亚斯德这样的预言家保障从这个世界通过这座桥。祖师、架桥者或制造浅滩者都可以比拟这样的预言家。
总之,祖师  概念是非吠陀和前于吠陀的概念。因为它见于大多数沙门派别中,可能是原始沙门传统的一部分。
概念是非吠陀和前于吠陀的概念。因为它见于大多数沙门派别中,可能是原始沙门传统的一部分。
阿罗汉-祖师  在沙门传统中的重要性不能过分强调。他只是与吠陀游荡者
在沙门传统中的重要性不能过分强调。他只是与吠陀游荡者  中的祭司和天神共享崇高的地位。吠陀祭司引导祭拜天神,而祖师将追求者引向他自己或他自己的教导。几乎是面对一条死胡同,阿罗汉祖师通过他的教导保障追随者们前进,越过这个苦难的世界。
中的祭司和天神共享崇高的地位。吠陀祭司引导祭拜天神,而祖师将追求者引向他自己或他自己的教导。几乎是面对一条死胡同,阿罗汉祖师通过他的教导保障追随者们前进,越过这个苦难的世界。
在吠陀领域中,只有奥义书接受教师(guru)的重要性,但也是与天神共享基座。“对待老师像对待天神” gurau,《白骡奥义书》6.23),与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
gurau,《白骡奥义书》6.23),与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  相同:“祭司像全能的天神”
相同:“祭司像全能的天神” 。
。
这里,我们可以指出沙门传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即再生理论。它“在佛陀时代,几乎被这个国家整个文明地区的普通人普遍接受”,而与吠陀的死后说(eschatalogy)不相容。普善(Poussin)提出它是“一种野蛮人的思辨”,查特吉(S.K.Chatterjee)提出“它证明原始南方人的影响”。这些看法都已被正确地抛弃。我可以指出再生理论令人想起希腊传统中流行的命运律(thesmos te Adrasteias)。在讨论命运律时,苏格拉底被说成观察到“一个灵魂转生为哲学家,或爱美者,或音乐家,或爱自然者,第二个灵魂转生为执法的国王或好战的统治者”等等(《寓言集》,公元前248年)。
人们感到惊奇,是否再生理论流行在某些印欧人分支中,并由原始沙门带进印度,时间在梨俱吠陀的婆罗多族、俱卢族和其他族进入这个国家的西部地区之前。
总之,这些原始沙门是雅利安种族的游荡苦行者,他们在前于吠陀时期迁徙印度。
说沙门传统是《梨俱吠陀》中耶提(yati)和牟尼(muni)的苦行和非仪式主义实践的继续,这种理论是依据十分可疑的和后期的证据。
在公元前八世纪前后沙门传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对立的沙门和婆罗门同时发展,反映在后来的阿育王铭文和巴利语文献中。虽然在钵颠阇利的《大疏》( ,2.4.9)中,提到沙门和婆罗门的永恒敌对
,2.4.9)中,提到沙门和婆罗门的永恒敌对  ,而在巴利语文献中,没有发现经常提到或暗示这种互相的敌对。在经藏中有好几处批评婆罗门实践(《增一尼迦耶》中的《婆罗门品》),这也是事实。但是,复合词沙门婆罗门
,而在巴利语文献中,没有发现经常提到或暗示这种互相的敌对。在经藏中有好几处批评婆罗门实践(《增一尼迦耶》中的《婆罗门品》),这也是事实。但是,复合词沙门婆罗门  只是表示他们是两类精神导师,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例如,在《长尼迦耶》(8.5.25)中,说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和下方分别象征父母、老师、儿子和妻子、朋友和亲戚、奴仆和侍从,而上方表示沙门和婆罗门。对立出现在梵书时期。《爱多雷耶梵书》提到当时出现的一种争论。它围绕比较两种生活方式的重要性:(1)禁欲和苦行的游荡者采取的生活方式,(2)依据婚姻和农耕的定居生活。因陀罗(Indra)乔装成一个婆罗门鼓励罗希多(Rohita)王子持久游荡,在这过程中宣说游荡哲学。因陀罗说:
只是表示他们是两类精神导师,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例如,在《长尼迦耶》(8.5.25)中,说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和下方分别象征父母、老师、儿子和妻子、朋友和亲戚、奴仆和侍从,而上方表示沙门和婆罗门。对立出现在梵书时期。《爱多雷耶梵书》提到当时出现的一种争论。它围绕比较两种生活方式的重要性:(1)禁欲和苦行的游荡者采取的生活方式,(2)依据婚姻和农耕的定居生活。因陀罗(Indra)乔装成一个婆罗门鼓励罗希多(Rohita)王子持久游荡,在这过程中宣说游荡哲学。因陀罗说:
我已经听说,罗希多啊!
光荣属于完成游荡的人,
停留在人群中间是罪恶,
游荡者是因陀罗的同伴。
他进而鼓励罗希多:
幸运随他坐下而坐下,
幸运随他站起而站起,
幸运随他躺下而躺下,
幸运随他行走而行走。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因陀罗以同样口吻诵出这首诗:
游荡者会发现蜜汁,
发现甜美的无花果,
他想到光辉的太阳,
也是永不疲倦游荡。
针对这种游荡者哲学,那罗陀  仙人宣说定居生活的哲学,抚养家庭,举行祭祀。他在同样的狗尾
仙人宣说定居生活的哲学,抚养家庭,举行祭祀。他在同样的狗尾  传说中说:
传说中说:
父亲生下儿子,
看到儿子的脸,
他便还清债务,
也就获得永生。
那罗陀否定禁欲和苦行实践,接着说:
儿子是装备精良的渡船,
污垢和羊皮衣有什么用?
长头发和苦行有什么用?
婆罗门啊,求取儿子吧!
那罗陀反复强调说:“对于一个没有儿子的人,整个世界变得空虚。”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传统的游荡生活与依据兴起的农业和永久的乡村定居生活之间的斗争。伴随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是游牧生活和社会生活展现的两种价值体系的紧张关系。持久的游荡者关注自己与自然的斗争,想要超越世俗生活的束缚和限制及其种种弊端。社会与他无关,因此不进入他的哲学思考。他首先关心的是通过苦行方式斩断世俗生活。
社会有它自己的世界观。在前于社会的阶段,人在宇宙等级体系中无足轻重,与野兽和植物差不了多少。“人确实像林中的一棵树”(《大森林奥义书》3.9.28),这是处在社会之外的人的看法。打破宇宙等级体系,放在社会背景中,人变得无限重要。他占据舞台的中心。因为人在社会中,主要的价值与社会义务和责任相联系,即偿还对祖先、圣人和天神的三种债务。
沙门是与游荡者团体一起游荡的优秀游荡者,讨论关于世界真实的本体论问题,实行禁欲生活。另一方面,婆罗门是履行社会义务和责任的家主的典范。因此,沙门和婆罗门形成对立。
吠陀人社会的形成和永久的乡村定居生活,将社会的人推到前面,而使传统的游荡者处在边缘地位。这里,社会的人面对孤独的人。孤独主要不是身体意义上的孤独,而是在精神背景中,他撤出社会,进入自己的意识深处,理解他自己的存在。在身心两方面生活在社会边缘,他主要关注人的意识的性质。对于他,人的意识的内在统一,超越身体、生命和心理方面,远比通过梵(brahman)的概念表达的宇宙意识的外在统一更重要。因此,焦点从早期吠陀时代的梵转移到后期的自我  。
。
这样,实际上我们发现三种价值体系:沙门强调世界的罪恶和短暂无常的特点。婆罗门主要关心社会义务和责任。奥义书关注人的意识的性质。
戈耶尔教授以批评的方式全面地讲述这个故事,展现种种迷人的景观,确实值得我们赞美。关于佛教的不同方面,有好几部著作,但是,涵盖整个领域——哲学、宗教、国家和社会,概述从佛教产生前直至现代的历史,这样的一种权威性著作是人们盼望已久的。戈耶尔教授提供这样清晰、全面和批评性的叙述,确实赢得学者和一般读者的感激。我肯定这部著作会成为今后几十年的标准参考书。
帕塔克(V.S.Pathak)
戈罗克普尔大学古代历史、文化和考古系前教授和主任
戈罗克普尔,1987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