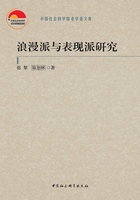
三 德国浪漫派的评价问题
如上所述,德国浪漫派是德国文学史上最复杂、争议最多的领域。争议的核心是评价问题。一个半多世纪以来,褒贬双方一直进行着激烈的论战。这场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反映了浪漫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遭遇。
对浪漫派的批判始于歌德。早在1805年,这位诗人就开始与浪漫派决裂。在《温克尔曼》(1805)一文里,诗人赞扬了温克尔曼不信奉宗教的思想,表达了自己对浪漫派所皈依的天主教的憎恶态度。在以后发表的论文《说不尽的莎士比亚》里,在他的书信、言论、谈话里,都着重批判了浪漫派崇尚主观幻想、“背弃”现实以及它的宗教神秘倾向。歌德的言论,深刻地影响了后代对德国浪漫派的评价。
首先起来同歌德唱反调的是拿破仑时代流亡德国的斯塔尔夫人。她在《论德国》里,把浪漫派诗人和哲学家誉为“人类思想军队的先锋队”。她强调浪漫派的思想自由、创新和挖掘文化遗产的乐趣,以此来跟拿破仑专制下法国文化生活死气沉沉的局面相对照,并力图把魏玛古典主义与浪漫派的努力联结在一起。
二十五年后,1835年,流亡在巴黎的海涅撰写了一部与斯塔尔夫人的《论德国》同名的著作,[5]执意要跟这位法国名流唱对台戏。他笔下的浪漫派,“无非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是“基督的鲜血里萌出来的苦难之花”,而他心目中的浪漫派作家乃是“专制主义的刽子手”,“神圣同盟”的盟友。海涅的评论,实际上就是从文艺上,政治上宣判了浪漫派的死刑。
几年后,1842年,著名文学史家格尔维努斯(1805—1871)在他的《德意志民族文学史》[6]里,声称歌德和席勒是德意志民族文学的高峰,同时也是终点。从而浪漫派被视为异端,被排斥在德意志民族文学传统之外。稍后,诗人艾兴多尔夫(1788—1857)和文学史家赫特纳(1825—1882)、海姆(1821—1901)都先后在自己的文学史著作里为浪漫派辩护。艾兴多尔夫认为,德国浪漫主义年代的德国文艺,“从根本上说是生机勃勃的”。针对海涅和格尔维努斯的论断,赫特纳强调指出,“毫不犹豫地把浪漫派与反动派等量齐观是非常不公平的”。在海姆看来,浪漫派不存在所谓复辟问题。
德意志帝国1871年建立前后,人们重视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追求政治经济的向外扩张,向往过去、总是主观幻想的浪漫派遭到冷遇。但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德国已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社会的危机和矛盾,对自然科学思维方法和理性主义、实证主义文化的不满,导致了浪漫主义的“新生”。女作家胡赫(1864—1947)的论著《浪漫派》[7]和哲学家、文学史家狄尔泰(1833—1911)的文章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胡赫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浪漫派领导人想要复活过去的甚至中古的状况”。浪漫派这次“新生”,被称为“新浪漫派”。但是浪漫派的“好景”不长,不久即遭到新兴的自然主义的排斥而再度被打入冷宫。20世纪20年代里,德国思想文化界又出现了所谓启蒙——理性主义危机。浪漫派又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文学史家柯尔夫(1882—?)在其四卷本的文学史巨著《歌德时代的精神》里为浪漫派唱响赞歌。
第三帝国时期,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流行一种看法,认为纳粹某些思想理论起源于浪漫派,[8]“反动派赞助浪漫派,浪漫派为反动派效劳”(阿·阿布施语)。鉴于浪漫派与法西斯的这种“关系”,加之它(由于自身的问题和历史的原因)本来名声就不佳,因此在反法西斯阵线中,它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卢卡契的观点。他在其1947年出版的《德国文学中的进步与反动》一书中,把文学传统分为进步的和反动的两类,浪漫派自然属于后者。他认为浪漫派并非一个封建主义运动,而是一个资产阶级运动,它要重建的“不是封建社会制度,而是一个政治上、社会上反动的资本主义”,一个“‘有机地’容纳并保存封建残余”的社会。卢卡契的评论深深地影响了反法西斯阵线和苏联学术界对浪漫派的评价。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和苏联等国,德国浪漫派普遍遭到冷落。人们的评论基本上遵循过去歌德、海涅、卢卡契的批判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伊瓦肖娃编著的《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里,德国浪漫派简直是一股十恶不赦的逆流,与反动派几乎是同义语。
德国浪漫派经过长期的“沉眠”,十多年前又“苏醒”了。首先“唤醒”它的是苏联学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在某些重要问题的评价上,就出现了为浪漫派“平反”的势头。苏联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1966年出版的五卷本《德国文学史》第三卷,起了带头作用。它的有关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篇章,断然纠正了苏联学术界当时仍居主导地位的消极评价。该卷分析了耶拿派的矛盾,论述了它的美学的积极内容和它的艺术成就,同时也指出它在社会和美学方面,有一些反动倾向。它关于浪漫派的论述,标志着苏联学者在关于德国浪漫派评价上开始克服教条主义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从那以后,在苏联其他学者(如德米特里耶夫和贝尔柯夫斯基等)的论著里,都可发现对德国浪漫派的较积极的评价。
欧洲对浪漫主义的重新评价,促进了研究工作的蓬勃开展。目前,浪漫主义问题在苏联文艺学中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自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以来,苏联加强了对欧洲浪漫主义,特别是德国浪漫派的探索,成果累累:《浪漫主义美学》(万斯洛夫著,1966),《关于欧洲浪漫主义》(诺波柯耶娃著,1971),《德国浪漫派》(贝尔柯夫斯基著,1973),《奥·威·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美学》和《耶拿派问题》(均为德米特里耶夫著,前者1974,后者1975)。普里雪夫和顾尔雅耶夫两位教授分别领导一批专家学者从事德国浪漫派的研究。此外,莫斯科莱蒙托夫大学和列宁师范学院有一批博士学位论文也是写关于德国浪漫派的。
20世纪70年代初期,浪漫派开始引起民主德国文艺学家们的兴趣。弗里德里希和龙格[9]的浪漫派画作轰动一时的成功展出,安娜·西格斯和克里斯塔·沃尔夫等作家在探索继承浪漫派积极传统方面获得的可喜成果,这些不仅激发人们对浪漫派传统的兴趣,而且也给人以启示:浪漫派传统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效劳。与此同时,苏联等国学者在探索浪漫主义,特别是德国浪漫派中不断提出的新观点、新问题,对民主德国同行的研究工作也是个有力的鞭策和推动。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民主德国的专家学者们开始加强其研究工作,并着手审查过去的评价。从《德国文学史》[10]和近几年来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民主德国的文艺学家们正在逐渐地纠正过去的消极评价。丹克[11]在一篇题为“论德国浪漫派文学的地位和成就”[12]的评论文章中,以卢卡契为例,批判了过去在浪漫派评价上的片面性,指出:民主德国文艺学家同卢卡契的观点有了根本区别,认为浪漫派特别是早期和过渡阶段(即中期)浪漫派在政治上是积极努力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在美学革新方面也有贡献。
和民主德国一样,浪漫派在联邦德国开始被重新发现,也是在七十年代初期。诗人恩岑斯贝格、赫尔特林等在继承浪漫派传统基础上产生的作品,颇具魅力。在众多的关于浪漫派的论著中,勃令曼的《德国浪漫派》较为突出。
这场围绕德国浪漫派评价问题,展开的大论战,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1.持续时间长久(历时已一百七十多年,至今尚未结束);2.“战线”长,范围广(从德国到欧洲);3.涉及问题多(美学、政治、哲学、宗教……);4.形势复杂(褒贬两方“阵线”不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内部都有“褒派”“贬派”;各方时胜时负,“战局”不明朗)。
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的产生,究其原因,除了立场、观点、方法(这是统一认识的大前提,是首要的)因素外,就在于德国浪漫派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问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于:其一,德国浪漫派是个派中有派的文艺思潮和流派。按地区分布,有耶拿派、柏林派、海德堡派、施瓦本派等。此外在各小派系之间还有不参加派别活动的人士(如克莱斯特和霍夫曼)。各小派系和成员,思想倾向不同,贡献大小各异。其二,浪漫派自身在发展变化。随着法国革命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浪漫派在其存在的三十多年内,经历了政治斗争、社会变动的风风雨雨,自身发展也随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早期、中期和晚期。这些阶段的划分,标志着浪漫派内部世界观和美学思想的某些变化发展。年长的耶拿派跟年轻的海德堡派互相反目就是例证。前者不承认后者为内行,后者也不买前者的账,斥之为匪帮。另外,在政治风云变幻不定的年代里,浪漫派成员发展变化更快。有人倒退,有人前进,弗·施莱格尔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和复辟时期的政治态度是矛盾的。早年的霍夫曼,思想较保守,晚年趋向进步。——这些情况都说明了浪漫派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鉴于浪漫派问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对它功过是非的评价,就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进行辩证的、具体的分析;企图以“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积极的”或“消极的”这类修饰词来为其定性,未免有简单化之嫌。
德国浪漫派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流派呢?有人说它是消极反动的流派,“根据”有三:一曰它反对法国大革命,而这是区分积极或消极浪漫主义的重要标志;二曰它提出的“回到中世纪”的口号有着反动的含义,就是要回到中世纪封建制度和天主教的统治,“要在新世界恢复中世纪的生活方式”;三曰它在复辟年代里充当复辟势力的辩护士,反动倾向更加突出。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欧洲的封建统治,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开辟了资本主义在欧洲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德国来说,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远比政治经济领域深刻。德国知识界,从老一辈的克洛卜斯托克、赫尔德尔和席勒,到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包括几乎所有早期浪漫派作家,无不为伟大邻邦推翻封建统治而感到欢欣鼓舞,都把它当作一个新时代“壮观的日出”(黑格尔语)加以颂扬。1792年12月28日,年方十九岁的蒂克在给他的朋友瓦肯罗德尔的信里写道:“现在,我日夜思念着法兰西,如果她遭殃,我就蔑视整个世界。”[13]即使在革命逐渐深入,尤其在1793年雅各宾党开始专政时期,一些浪漫主义者仍没有改变对法国革命的态度。1793年3月5日,瓦肯罗德尔在给蒂克的信里说:“……法国国王的处决,使整个柏林都对法国人的事情感到惊恐,我却不是这样。我像往常一样思念他们的事情。”[14]1798年,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诺瓦利斯)在他的《政治格言》第二十二则里表达了他对共和主义的信仰:“世人普遍怀有如此信念的时期即将来临:没有共和国就不可能有国王,同样,没有国王也不可能有共和国,两者犹如身躯与灵魂,不可分割……”[15]翌年,这位诗人又写道:“普通的境况,[16]使人无动于衷,感到无聊。在共和国里,这当然较好,在那里,国家是每人的主要事情,每人……都几乎本能地为巨大的整体而要忘却他狭小的自我。”[17]1798年,德国浪漫派代表人物弗·施莱格尔在《雅典娜神殿》上发表的《断片》第二百一十六则里还这样热情地称赞法国革命:“法国革命、费希特的《科学论》和歌德的《迈斯特》,乃是时代最伟大的倾向,谁不满意这样的并列,谁以为没有公开表现为物质形式的革命不重要,他便是还没有站到人类历史高瞻远瞩的立场上。”[18]当然,弗·施莱格尔及其派友们,并非革命家,他们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对革命暴力的认识和态度毕竟还是有矛盾的。譬如,同一个弗·施莱格尔,一面赞颂法国革命,同时却又对革命暴力胆战心惊。他在《断片》第四百二十四则里写道:“法国革命,可以看作为诸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和最值得重视的现象,看作为政治领域上一次几乎是全世界性的地震,一场极大的洪水……”[19]德国浪漫派作家对法国革命的认识和态度,虽不是前后一贯、始终如一的,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积极的,可以说,他们胜过当时德国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歌德在内。这位诗圣在法国革命深入时不是写过《市民将军》一类讽刺作品污蔑革命暴力吗?
德国浪漫派作家对法国革命的积极态度表明,他们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政治上所追求的是自由解放,而不是恢复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他们“回到中世纪”的口号,并非政治行动纲领,而是一种文艺主张;它说明德国浪漫派对民族传统,特别是对中世纪民间文艺的向往。他们之所以迷恋中世纪民间文艺,是因为这种文艺想象丰富,感情真挚,语言生动,表达方式自由。特别是在受外族侵略和压迫的时期,他们对民族传统和民间文艺的重视,还含有鼓舞民族精神、唤起民族意识的因素。他们在收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特别是中世纪民间文学所做出的重大努力和贡献,说明了问题的实质。
对复辟年代的浪漫派要作具体分析。如上所述,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希望祖国统一的基本要求无法实现,爱国主义的进步倾向遭到扼杀,悲观失望、垂头丧气的情绪在人民中重又滋长起来。一些陷入思想危机的浪漫派作家,企图到宗教信仰中去寻求精神寄托,他们作品中的一些消极因素有所增长。弗·施莱格尔后来甚至堕落为梅特涅的公使馆参赞。这些无疑都是事实,应该受到批判。但据此就能笼统地宣判后期浪漫派为反动的吗?阿尔尼姆、沙米索、霍夫曼等的发展道路和创作实践表明,这样的判决是错误的。
阿尔尼姆在他的创作(如短篇小说《社会的变化》,1826)强化了对普鲁士当局和贵族的批判。沙米索以其中篇小说《彼得·施莱密尔的奇妙故事》(1814)批判了资产阶级的金钱万能思想。他在19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初期写的诗歌,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矛头主要对准欧洲的复辟势力和教会反动派。同时也针砭国内社会时弊,抨击德国的反动制度。例如,《更夫歌》嘲弄了军警制度,当年的警察原来是耶稣教徒。又如《黄金时代》揭露和讽刺了德国警察的专横。诗的末尾风趣地写道:“把那个雅各宾党人逮捕起来!我们亲眼看到他的罪恶勾当。他敢公开地宣扬二加二等于四!把他弄掉,免得让人听到他说教!”当然沙米索对普鲁士当局的本质还是认识不清的,譬如他后来把普鲁士当局说成“父亲般的政府”,说它能确保社会不断地进步,虽然是缓慢的。
如果说沙米索对普鲁士当局的态度是矛盾的,那么与其有交情的“派友”霍夫曼的态度就大不一样了。长期以来,霍夫曼被贬斥为德国“反动浪漫主义的最大代表”,现代“颓废派的祖师爷”。鉴于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也鉴于他长期蒙受曲解,这里有必要就他对普鲁士当局的立场和创作思想倾向多说几句,以正视听。
霍夫曼同普鲁士的冲突,集中地表现在一桩诉讼事件上。1819年,普鲁士反动派根据同年9月批准的卡尔斯巴德决议,更加残酷地迫害进步人士。霍夫曼被任命为所谓“叛逆集团及其危险活动直属调查委员会”成员,并被委托审理著名的“体操之父”雅恩。他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对雅恩的起诉是没有根据的,建议将其释放。控告虽破产,但由于内务部头子卡普茨一小撮反动派的反对,雅恩未能获得释放,雅恩鉴于个人名誉而反过来对卡普茨提出控告。这期间,为卡普茨诬陷中伤的法官霍夫曼,无所顾忌地接受了雅恩的起诉。由于普王的干预才迫使霍夫曼放弃审理此案。霍夫曼对当局的专横深恶痛绝,不愿同流合污,便提出辞职,以示抗议。次年,他的辞呈被批准了,但斗争并未就此了结。后来,他在《跳蚤师傅》里,对当局的专横进行了揭露和讽刺。这部艺术童话里的枢密顾问克纳尔潘蒂,就是卡普茨的写照。这些章节在付印时已被传开,卡普茨派人劫取霍夫曼的邮件,发现说明此作的一封信。稿件因此被没收。卡普茨一伙反动分子并不以此为满足。1822年,他们竟然以“违反纪律”的莫须有罪名,对四肢瘫痪、重病在身的霍夫曼提出起诉。
晚年的霍夫曼,更加面向现实,靠近人民,摆脱了悲观神秘的倾向,除《跳蚤师傅》外,还写了不少出色的作品,如《侏儒查赫斯》(1819)、《堂兄弟的屋隅之窗》(1822)和《公猫摩尔的人生观,附乐队指挥约翰·克赖斯勒的传记片段》(1819—1821)。《侏儒查赫斯》写一个形态古怪的侏儒靠招摇撞骗飞黄腾达,窃据了部长的宝座。后来终于垮台。查赫斯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作品揭露和嘲弄了宫廷社会的尔虞我诈、故弄玄虚,具有普遍意义。《公猫摩尔的人生观》是霍夫曼的代表作,是德国浪漫派反映时代和社会最杰出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了两个对立人物的生活经历:一个是会写作的公猫摩尔,另一个是乐队指挥克赖斯勒。前者是一个目光短浅、事事知足、自私自利、高傲自负、善于随机应变的市侩典型,后者是个富有理想、思想高尚的艺术家典型。在摩尔经历部分里,小说以迂回曲折方式揭示一个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的市侩世界。在克赖斯勒传记部分里,作品描写了一个过时、没落、腐朽、摧残人性、敌视艺术和艺术家的封建宫廷——德国社会的缩影。宫廷中的两个统治者——王公和一个女贵族(王公昔日的情妇)——都从维护封建权位出发考虑并决定各自女儿的婚事。前者要把女儿嫁给一个富有的罪犯;后者要把自己的千金(她与乐队指挥情投意合)许给一个痴呆的王子。克赖斯勒在宫廷中的遭遇可想而知。
阿尔尼姆、沙米索和霍夫曼等的思想发展和创作倾向表明,即使在特别黑暗的年代里,浪漫派内部仍然存在进步倾向。因此,对后期浪漫派也要一分为二地分析,不能一概否定。
总体来说,德国浪漫派在政治上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文学上做出过重大贡献,在美学上有所创新,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也存在某些消极因素,并因此产生过消极的作用。我们认为,这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
[1]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1984年第9辑。
[2] 海涅和文学史家格尔维努斯和海姆等个别人称它为“romantische schule”(习惯上也译为浪漫派)。
[3] 以创始人格林兄弟命名,篇幅多达三十几卷的《格林德语大辞典》,经过数代语言学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初编纂完成。这是日耳曼语言文学史上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4] 文学史家把德国浪漫派传统在世纪更迭前后那次复苏称为“新浪漫派”。
[5] 海涅的《论德国》共两册,第1册《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2册《论浪漫派》。
[6] 此系德国第一部完整的文学史,全书共五卷。
[7] 全书共两卷,第1卷:《浪漫派的兴盛时期》,1899年;第2卷:《浪漫派的发展和衰落》,1902年。
[8] 据称,戈比诺的种族论,可从浪漫派作家富凯的作品里找到某些“一致性”。
[9] 弗里德里希(1774—1840)和龙格(1777—1810),均为德国浪漫派绘画的代表人物。前者擅长风景画,后者擅长人物画。
[10] 全书共12卷,第7卷(1978)涉及浪漫派文学。
[11] 丹克教授,《魏玛评论》杂志编委,《德国文学史》第7卷主要负责人之一。
[12] 载《魏玛评论》1978年第4期。
[13] 《法国革命在德国文学中的反映》,雷克兰出版社1979年版,第376页。
[14] 《法国革命在德国文学中的反映》,雷克兰出版社1979年版,第378页。
[15] 《法国革命在德国文学中的反映》,雷克兰出版社1979年版,第384页。
[16] 指当时德国那种令人沮丧的社会生活。
[17] 转引自《遗产理论与遗产继承研究》,雷克兰出版社1981年版,第280页。
[18] 《法国革命在德国文学中的反映》,雷克兰出版社1979年版,第400页。
[19] 《法国革命在德国文学中的反映》,雷克兰出版社1979年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