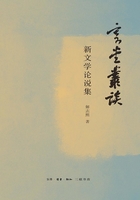
三
早年的格非是以先锋派的小说艺术书写都市人生著称于文坛的。我还记得,当我们都还是年轻学子的时候,格非在上海写出了他早期的代表作《褐色鸟群》,我在北京偶然读到这篇小说,很为叹赏——那时的我也是一个现代派—后现代派迷,所以立即为这篇小说写了一则短评《〈褐色鸟群〉的讯号——一部现代主义文本的解读》。其时我和格非还不相识。此后的格非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不断有出色的作品问世,而我则故步自封于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与当代文学越来越疏远。直到新世纪之初,我们不约而同地调到了清华中文系,成了同事和朋友。北来的格非已人到中年,人与文更趋稳健练达,陆续贡献出了“江南三部曲”和《隐身衣》等长篇与中篇小说。每有新作,格非都会送我一本,我也大都翻阅过,但由于避嫌也因为懒惰,再也没有写过评论,只是隐约感到格非创作的兴趣似乎渐渐回归到乡土中国叙事,并且在艺术上也有渐渐回归中国古典叙事艺术传统之趋向。
《望春风》是格非回归乡土叙事的力作,同时格非在其中创造性地复活中国古典叙事艺术之努力,也令人刮目相看。比如中国古典说书艺术的传统在《望春风》频频出现,就是很显然的事,此处不论。我觉得更重要的也更值得赞赏的,乃是格非这部新作对中国古典历史叙事的“纪传”传统之化用。不难看出,《望春风》里事关核心人物的专章,如“父亲”“德正”“春琴”诸章,颇近似于正史里的“本纪”,“余闻”一章集中叙写其他人物,则很近似于正史里的“列传”,并且全书各章也采取了史传叙事的“互见法”。比如第一章“父亲”比较完整地叙写了“父亲”的坎坷命运,可说是“父亲”这个人物的“本纪”,但该章叙事也不完全局限于父亲的故事,其中也穿插着其他几个主要人物如德正、妈妈、春琴等人的故事片段,而“父亲”之本事也在其他章节里得以补充。如此有“纪”有“传”、“纪”“传”互文,无疑使《望春风》的乡土中国叙事在结体上“得其体要”、显得很有章法,同时也使作品的蕴含更为丰富多彩而且精彩纷呈。就我眼目所及,还没有见到哪部现当代小说如此创造性地化用古典历史叙事的“纪传”传统(唯一的例外是《阿Q正传》对正统史传的反模仿),并且化用得相当灵活,这是很值得赞赏的艺术成就。
当然,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古典纪传体史著,既有成功处也有局限性,其成功在于突出了杰出人物,而其局限则是削弱了历史叙述的连贯性或完整性。此所以作为对纪传体局限性的补正,后来又出现了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著,但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也都有其缺陷,那就是它们往往会使历史人物淹没在历史叙事的长河里了。中国古典史著的这两种叙事模式的短长互见、难得兼顾之矛盾,其实是所有叙事的共同难题,自然也会反映在小说这种虚构的艺术叙事里,那便是小说的叙述到底是以人为主还是以事为主?如上所述,《望春风》似乎较多地借鉴和化用了古典史著的“纪传体”传统,所以其叙述便以重要人物为主,但格非显然也意识到这种叙述模式的局限性——对整个作品叙事脉络的削弱,所以他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努力使《望春风》对多半个世纪的乡土中国之叙述有一个贯穿始终、有主有次的叙事脉络,这个叙事脉络隐含在人物“纪传”之中,但确实存在着。事实上,构成全书草蛇伏线的就是叙述人的父亲所不慎卷入的潜伏案,这个案件潜延多年、迹近无形的存在,却深深地影响了“父亲”“母亲”和叙述人自身的命运及他们的人际关系,从而也就成为整个《望春风》的主要叙事脉络。在把控这个若隐若现的叙事脉络上,格非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先锋派小说家的叙事能耐。我们都知道,格非早期的创作原本取法于西方现代派与后现代派文学,很擅长通过变幻莫测的叙事技巧和迷离惝恍的悬疑情节来暗示人生的不确定性和暧昧性。这种叙事能耐在《望春风》里仍有出色的发挥,所以作品的叙事颇富引人入胜的悬疑性,而且这种悬疑性的情节线索牵连全篇,确乎构成了潜在而却主导性的叙事脉络,如同音乐里主题动机的时时重现和反复变奏一样,灵活自如而又富于规律性。
仍以第一章为例,该章原本是“父亲”的本纪,可是格非却没有直奔“父亲”的生平命运,而是从一个腊月里“父亲”领着小小的“我”到半塘“走差”开篇,以看似浑若无意的随兴笔调,抒写着父子之间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的交流、问答和游戏。父子俩仿佛随兴地讨论着村子里这个那个人物,儿子且看着父亲机智幽默地打发着一个个迎面而来的问难,一路像是游戏一般轻松地过去了,直至在春琴家说媒成功,“父亲”才不无得意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件事,先不要对外说。春琴很快就要嫁到我们村里来了。”其实,此行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么轻松写意,因为就在轻松的路途中间,父亲还有一点不同寻常的举动——
这时,父亲突然毫无来由地将我揽入怀中,在我的额上亲了一口。随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有点令人费解的话:“办完了这件事,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就要好过多啦!”
这就预埋了一个关乎作品整体的悬疑或者说悬案,它像草蛇灰线一样时隐时现而贯穿全篇,读者只有读完全书,才能明白其曲折的来龙去脉及结穴。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具有暗示性而又暧昧得很恰当的开头,堪称神来之笔,充分显示了格非叙事才华的现代性。
如此,《望春风》就同时展现了格非在叙事艺术上的延续与转变。所谓延续的一面是格非老早就擅长的,即取法于西方现代派与后现代派文学、善于通过变幻莫测的叙事技巧和迷离惝恍的悬疑情节来暗示人生的不确定性和暧昧性,这一面在《望春风》里仍有余绪,所以作品中其实暗含着贯穿始终的悬疑性故事,显示出高度精微的叙事能耐;所谓转变的一面即是对中国古典史著“纪传”传统的创造性化用,写人物乃“纪”“传”并用且互见互文,构成了颇具规模的写人阵列,这使《望春风》呈现出自然老到而且井然有序的新古典风貌。
我觉得多少有点遗憾的是,上述两方面似乎在《望春风》中未能达到兼容无碍、相得益彰的程度,而不免留下了一些相互扞格、融化未熟的痕迹。诚然,不论在历史著作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其写人和叙事要达到两全其美、水乳交融的境界都非易事,但并不是不可能。在这里,需要克服的最大艺术难题乃是找到写人和叙事之间的恰当关联。《望春风》的写人和叙事相互扞格、融化未熟的问题,恐怕就出在这里:不论是关系到“儒里赵”村半个多世纪命运的主要人物之纪传,还是困扰着叙述人的“父亲”多年之疑案,分开来看都足以构成相当出色的文学叙述,可是把二者融合起来的关联点却微弱而且勉强——尽管那个疑案故事很精彩,怎奈与作品真正的叙述主体和主题“儒里赵”村的变迁史基本上不搭调、不匹配,则再精彩的叙述和设计都不免多余了。窃以为,很难设想在那么一个小村庄里的小老百姓身上,竟然隐埋着如此奇特的间谍悬案,让一个乡下算命先生为此多年来提心吊胆、食不甘味、寝不安席,那对他实在是不必要的折磨;而由于他的悬案,竟至于让他的爱妻,一个出身农村底层的革命女性,悄然而神秘地离婚、出走、再婚、隐遁,仿佛神龙见首不见尾,并且最终蜕变成了一个像林黛玉一样自闭自伤的知性仕女,这也离奇得不可思议。然则,恕我大胆设想一下:倘若以土改、办学、平坟、修渠以及土地的承包与拆迁等一连串大事件作为勾连《望春风》的叙事脉络,或许就与这些乡土人物的纪传比较匹配了——不知格非兄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