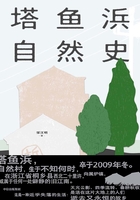
东弄堂
在邹介里,阿兰家与六节头顺林家之间。
春天来临,油菜花开,捉蜜蜂的时节到了。我们就转移到东弄堂去玩了。东弄堂也是两家人家的墙面相夹而成,不过,两家都是村里的贫困户,前后房子没几间。如此一来,东弄堂较西弄堂就短了许多。东弄堂两边的墙面,还都是泥墙。其中的一段,墙基的上面顶着稻柴,这在村子里是不多见的。
我们喜欢东弄堂两堵泥墙上密密麻麻的小洞。洞口的碎泥屑,是那么的亲切,蜜蜂很容易钻入这些泥墙洞,因此,花香纷飞的时令,成群结队的蜜蜂,就开始进驻东弄堂的小洞穴。蜜蜂们是有前世的记忆的,年复一年,它们飞来打洞,入住,嬉戏。这条脏兮兮的小弄堂,因为有蜜蜂可捅,现在回想起来,确乎是塔鱼浜每个小屁孩的乐园。
西弄堂和东弄堂的人家,平时少有往来,大家各过各的小日子。但每年总有那么几回,两条弄堂莫名其妙就有了关联。能够把两条弄堂连在一起的,说来奇怪,乃村里某个精明的老婆子的叫骂声。原来,她家少了一只鸡,少了一只鸭,或地头的南瓜、丝瓜之类的蔬菜让人摘了去,老婆子不知谁做下的事,也是为了警告某人下不为例吧,她就扯开嗓门满村坊游走,叫骂。那可是没来由的叫骂。说白了,没有一个具体叫骂的对象。这种叫骂自然不会站定在一个地方,而是游走在整个村坊,每个角角落落,务使大家都明白无误地能听到她的叫骂,一般老婆子就从东弄堂,一直叫骂到西弄堂,来回游走一圈,时间还必选在吃夜饭的当口。
东弄堂的西边,是顺龙、顺林、顺祥三兄弟家。老大邹顺龙后来全家搬迁到严介里戤壁路东口,此不赘述。顺祥岁数不大,人有点憨傻,力气倒蛮大,走起路来,脚步奇阔。顺林一表人才,与老培荣的女儿莲宝好上了,一到晚上,两个人想着法子找地方幽会。莲宝人瘦瘦小小,长得倒也精致。莲宝娘家就在我家西隔壁,辈分上,她其实比我大一辈,也长我七岁。她少女时代的样子,我也还记得。顺林的一只手上,拇指外侧多出一指,是个六指儿,故绰号六节头。
顺林家的房子,比起西弄堂聋子阿二和小阿六两家来,就低矮得多了。他家的后门头,还是草棚,某次下雨,好像还坍了一只墙脚,这可是大失面子的事体。
东弄堂的东边,是阿兰和彩彩夫妇家。彩彩面团团的,是从小就领到阿兰家的童养媳。彩彩一辈子都留着圆滚滚的包菜头,如此,她的面相,就越发地面团团了。阿兰脸黑,和善,人也不高,与人无争,属于张嘴就要露齿微笑的一类人。夫妻俩倒是一股和顺之相。那些年,我总看到彩彩背着一只竹篰,一个人去长坂里割草,或者看到她挑着一担菜,累了,半路上歇一歇,反手敲一敲自己的腰背。夫妻俩育有一双子女,儿子明祥长大后,脾气好,嘴巴甜,去了红木家具厂当管家,很得老板信任。
阿兰家房子,比顺林家的还要来得低矮,走进去,屋顶是亮晃晃的,直接就通了天。底下,因为漏水,脚踏上去,滑里滑㳠的。他们家的墙基还是泥巴打造,可见这一家的贫穷。但这堵泥墙的外侧,密密麻麻地钻满了蜜蜂洞,那里,蜜蜂们营造了一个嗡嗡响的乐园。
这东弄堂的后边靠西,有三个连成一线的草棚,是大毛毛家的。塔鱼浜草棚不多,大毛毛家的草棚,远近就较为注目。这地方离塔鱼浜最东边的雪明家近。雪明人长得矮小,鬼点子却不少。雪明走来走去,一路都是笑眯眯的,他生就一副和乐之相,这可真让他捡了便宜。雪明的父亲是大队书记,很快,他身边就聚拢了一群小屁孩,屈指一数,有邹鸣、建祥、新潮、祖林、玉祥等,年龄都差不多。雪明八岁那年,跟围着他的一帮小弟兄做游戏。他把一串鞭炮一小根一小根拆散,还相中了顺荣家的四只小狗。狗主人建强,还一只只去抱了来。雪明手里的鞭炮,就一根根分别插入小狗的屁眼,这家伙将火柴头划燃了,“嗤——啪——”小狗吓着了,也感觉到撕裂的疼痛了吧,一边汪汪直叫,一边跑得比奔马还快。四只小狗被轮换着放了鞭炮。四只小狗走马灯似的奔跑在塔鱼浜的东弄堂,风驰电掣一般,甚至比风、比闪电还快。雪明和几个小伙伴玩了一阵,彻底玩疯了,很快,整整一长串鞭炮放完,他们还不过瘾,还想玩下去。忽然想到了一个更刺激的办法,他们从东弄堂最北边顺荣家廊屋晒得干燥的稻柴堆里,扯出一把稻柴,干脆绑在母狗的尾巴上,然后,呼的一下点着了火。母狗受惊,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发疯似的奔窜开去。不料,老狗一个激灵,窜入大毛毛家的老草棚。母狗从这边窜入,瞬间,又从那边跑出,尾巴早已烧得焦黑。经此一奔窜,老狗倒也无事,可老狗身后的三个草棚,忽然,呼啦啦地火烧起来。四五个小屁孩赶紧提水救火,哪里还来得及,哪里还救得了这一团紧裹的烈焰。火借风势,越烧越旺,不过几分钟,三间老草棚烧得精光,连屋架子都不剩一个。雪明自知闯祸,跟几个同伙交代一声,一个人悄悄地躲了,他独自躲入塔鱼浜西北严家浜的机埠。后来,雪明的母亲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一问,他老实交代,就被拎着耳朵回到了家。雪明的父亲邹根富一向话不多,这回眼睛瞪得奇大(大队书记的眼睛本来就大),可倒也没发脾气。第二天,邹根富去了翔厚集镇,他独自扛来一堆毛竹。另外几家孩子的父亲也不约而同地拿来一捆捆稻柴,男人们一道,费去一天的工夫,给大毛毛家新盖了三个大草棚。
东弄堂的南头是一块大稻地。稻地尽头是水坝弯进的一只河浜。水流至此,形成塔鱼浜南埭屋门口最大的一只漾潭。河北岸,有一个很考究的河埠,块块条石,全都是金黄色,还一般大小。这河埠头,当年应该是停靠官船之用。河埠理所当然属于金福金宝金发金海四弟兄家。四弟兄的祖上,当过京官,其中的某个祖上,曾是道光年间赠封的侍郎,按现在的官阶,应是副部长那么一个级别。塔鱼浜墙内坟的三个大墓,是他们家的祖坟。
这一天,不知是不是揭不开锅了,四兄弟一商量,决定将家里的老狗杀了。他们让养了多年的看门狗饱吃一顿。吃罢一歇歇,呼狗进屋。老狗摇着尾巴进门,大门随即关紧。四兄弟各抱一根门闩,向着这条可怜的老狗围拢。看到这架势,老狗顿然明白自己的大限已到,不由自主地,狗的前腿趴到了地上。老狗拉长身子,趴到四弟兄面前,一条冗长的尾巴,紧贴地面,一动不动,狗眼里甚至还滚落几滴眼泪。砰的一声,四兄弟中,不知谁敲下了第一棍。地上的老狗,一个箭步蹦跳起来,开始没命似的满屋乱蹿,一边逃窜,一边呜呜之声不绝于耳。这一阵少有的狗哭声,凄厉至极,惨烈至极,整个塔鱼浜的人都听到了,大家悄悄地围拢,都一声不吭,拿眼睛看着四兄弟热火朝天地忙乎着。
可怜,狗头都打烂了,可这老狗,竟然还没有死去。人群中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对着四弟兄嘀咕一声:“狗心是泥做的,只要狗的脚还踏在地上,它是死不了的。”四弟兄忽然开窍,找来一根捆稻柴的担绳,捆住狗的一条后腿,绳子一抛,挂上河埠头一棵斜欹的枣树。担绳的一头用力一拉,狗身就离了地面,挂了上去,但见狗嘴里滴沥着血水,仍在呜呜直哭。怎么回事?四兄弟停手,一看,狗的一条前脚,似断还连,还踏实在塔鱼浜的泥土上。于是,又是一阵紧拉,整条老狗,终于完全地挂空了。不到一分钟,狗哭停歇,老狗呜的一声,合上了狗眼。
四兄弟里,老大金福一副好相貌。老二金宝年纪老大了,仍讨不到老婆。20世纪90年代初,外乡人涌入桐乡淘金,金宝与小他十五六岁的一个安徽歙县女结婚。三弟金发,与塔鱼浜南埭西横头玉娥相好,做了上门女婿。他与矮玉娥育有一子建华,一女丽华。建华七八岁的时候,“双抢”时节,去长坂里捉泥鳅,天刚擦黑,脚下一滑,扑通一下翻入一只深水荡。也是巧合,我正好路经此地,听到荡子里啪啪啪的水声,我也不知何故,走近一看,始知有人落水。那时我读初二,不过十五岁光景,也根本来不及细想,直接就跳入大荡,水没头没脑地淹没了我。我一把抱住男孩的双腿,往上一送,男孩求生心切,双手牢牢抓住荡口,身子本能地就挨了上去。人一站上荡岸,哇的一声,没命似的哭开了。我随即上岸,喊他回家。他一边呜咽,一边抹眼泪,紧步赶回家去。那只随他落水的尼龙袋,始终牢牢地抓在他的手里。
东弄堂长期没有人打理,一年四季,总湿答答的。弄堂里也没有垫哪怕一块半块像样的石块,来回非常不便。尤其是新年里脚穿新布鞋,经此,常要湿鞋。舍不得,脱了鞋赤脚再走吧,又嫌东弄堂的淤泥龌龊。其实,田间地头,乡村的泥巴并不让人感到龌龊,可是,东弄堂的淤泥黑乎乎的,混合着鸡屎鸭屎,人粪羊粪,我们白净的双脚,实在踏不下去。我们宁可绕道也不走东弄堂。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东弄堂与西弄堂相比,不够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