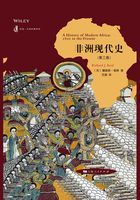
“非法”运送:19世纪的奴隶贸易
18世纪后期,欧洲的各种力量正获得废除奴隶贸易的动力。人们有些争议的是,一些特殊因素的力量应该如何考虑。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初,一些著名人士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主张废除奴隶制度,他们与启蒙运动人道主义以及福音派的愤慨结成一种奇特的联盟,来暴露奴隶贸易本身让人无法接受的残忍。欧洲知识分子和教会团体以一种信仰团结起来,那就是所有人类都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普遍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这场“运动”是一场广泛的礼拜,它把“启蒙”人士、诚挚的反教权主义者、被基督教良心驱动的人、被福音派所激励的人,都团结起来了。就所涉及的基督教会自身而言,这是一场福音派新教会复兴的开始,它带来了非洲传教活动的快速发展,本书第八章将介绍这方面情况。人道主义者的论点得到革命时期法国雅克·皮埃尔·布里索的强有力阐述;[16]在英国,它的领袖人物包括格伦维尔·沙普和威廉·威尔伯福斯,后者在1787年至1788年领导了一场巨大的公众运动;还有乔瑟厄·威奇伍德这样的工业慈善家,他生产了一种令人难忘的徽章,描绘一个戴着铁镣的黑人,上面有这样的话:“难道我不是一个人、一个兄弟?”[17]一些非洲人也参与到这场人道主义运动之中,比如欧罗达·艾奎亚诺的写作和公开演讲,在18世纪90年代就很有影响。这位前奴隶赎回了自己的自由,在英国受到教育,加入到废奴主义者行列之中,他自己也成了一位名人,尽管后来有人对他一些故事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然而,他的公开形象和他的自传《有意思的叙述》(Interesting Narrative)看来在当时是证实着一种伟大主张,这种主张因向文明的基督教著名人物暴露黑暗而获得价值。[18]
英文版原书页码:31-32

约1865年的西部非洲。引自J.E.弗林特所编《剑桥非洲史》第5卷《约1790—约1870年》(剑桥,1976),地图7,1976年版权属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许可复制。
除了将奴隶贸易废除之外,关于奴隶贸易辩论的另一个长远结果就是对非洲的主观化,辩论者面前出现了一个想象的实体,除了爱克伊诺这样的人之外,他们对非洲本身都所知甚少。非洲成了一个“客体”,一个观点或一个问题,以表达当时那些伟大的博爱人物和政治人物的看法。而且,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非洲”一直被外部世界的关切和议程所塑造,这个过程把19世纪乃至于20世纪的动能聚集到一起。如同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看到的那样,非洲协会是在奴隶贸易的辩论引发公众激情的19世纪70年代于伦敦建立的,协会宣布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非洲大陆与奴隶贸易断开,建立起多样化的贸易和互利、进步、文明的关系,它将“改善”非洲,促进对非洲的了解,当然也给英国自身带来贸易收获。[19]
协会在主张改变欧洲与非洲经济联系的同时,寻求切实的收益。尽管普遍而言的“人道主义”观点令人感动、强大有力,但毫无疑问,经济思维的改变,以奴隶贸易为基础的经济所获利益的改变,也导致对这种贸易能否生存下去的更为冷静的重新考虑。当然,奴隶的抵抗长期以来一直使这种贸易的投资者不安,奴隶船上的反抗已是相当普遍,而最引人注目的奴隶起义于1791年发生于海地岛,由杜桑—卢维图尔领导。[20]另外,18世纪90年代早期至1815年,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席卷欧洲,也使国际贸易受到抑制。全球海运航线被严重破坏,包括与非洲和美洲连接的航线,奴隶贸易就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而且,更普遍地看,奴隶劳动力不再被许多西欧经济学家视为有利可图,人们争辩说,未来经济增长靠的是使用自由的、有薪酬的劳动者的产业体系。比如,加勒比海地区以奴隶为基础的食糖生产,其利润在18世纪后半期已严重下降。欧洲的制造业投资一直在快速增长,尤其是在英国,而海外的种植园奴隶经济则在萎缩。[21]当然,这些并没有被普遍接受,至少是没有被立即接受。奴隶劳动在美国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巴西也是如此,它是19世纪最大的“非法”奴隶进口国。[22]19世纪30年代之前,奴隶制本身在大英帝国一直是合法的。[23]不过,人们说主要欧洲大国对奴隶贸易的废除带来了一个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新时代,这也就是为什么“1800年前后”可以是一个观念上的分水岭。关于非洲的经济思考有了重要的改变,非洲越来越被视为各种原材料的一个来源,也是工业制品的一个市场,而不再仅仅是奴隶劳动力的一个来源。北半球的工业化将因来自“热带”的植物油和橡胶得到进一步推动,欧洲的制造商们——这些公司中有许多是靠奴隶贸易发财的——在寻找海外市场,以出售它们廉价制造的商品。[24]
英文版原书页码:33
丹麦和英国这两个17和18世纪最大的奴隶运送国,属于第一批禁止本国公民参与奴隶贸易的国家,时间分别是1803年和1807年。接下来这样做的有美国(1808年)、荷兰(1814年)和法国(1817年)——尽管法国在18世纪90年代的革命时期就已多在谈论废除奴隶贸易的话题了。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同意废除奴隶贸易,唯有葡萄牙主张只在赤道以北禁止奴隶贸易。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执行却是极其困难。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死亡很是艰难,进入19世纪以后很长时间还在持续,像达荷美这样一些西非海岸国家,拒绝放弃这种被视为是基本的经济而且也是政治的活动。约鲁巴四处蔓延的战争也在产生大量的奴隶以供出口,我们下面会讲述。中部非洲地区,尤其是现在的安哥拉这一区域,如同奴隶贸易早期一样,也仍在从事奴隶出口。19世纪奴隶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拉丁美洲,也有少量奴隶更朝北去。不过,大西洋奴隶贸易在19世纪的确是逐渐衰退,到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部分已经消失,这部分是因为英国反奴隶贸易舰队在美洲大西洋海岸线巡查的结果,不过这种巡查的真正效果不应被夸大。美洲对奴隶需求的缩小,尤其是19世纪中期以后,以及“合法”贸易的扩展,在本质上是更为重要的因素。[25]
欧洲政治家、人道主义者和慈善家们的一个基本误判,就是认为奴隶制与“合法”贸易会是相互排斥的,但事实上它们能够而且也真的共存。无论如何,非洲统治者认为奴隶贸易如此之深地嵌入他们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之中,没有办法停止,至少是要有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剧变才能停止。达荷美的国王盖佐在1848年告诉一位英国官员,他无法放弃奴隶贸易,因为军队必须有事可做,如果国王自己试图改变“民众整体的情绪”,达荷美就会陷入政治混乱和革命,这“将把他自己推下王位”[26]。这类话其实是相当虚伪的。在达荷美,废除奴隶贸易不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它对奴隶贸易有完全的控制,它不愿失去与奴隶贸易相伴的特权,如果放弃奴隶贸易,代之以鼓励棕榈油生产,这就会使得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对那些普通的农户生产者开放。[27]压制奴隶贸易、传播“合法”生产福音的活动在大西洋海岸一些地方展开,这显然导致了欧洲在这一区域对非洲政治越来越多的卷入。盖佐是那种不顺从的统治者的一个例子,他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成为英国外交部非常关注的焦点,他拒绝(或者说不能)停止奴隶贸易,导致了英国外交使团的到来和强化的政治压力。[28]在其他地区,英国使用了军事力量,或者是威胁使用它,以强迫非洲统治者接受他们废奴主义者的要求。英国人发现战舰可以创造出有利的贸易条件,但这也意味着正式的政治控制在扩张时通常就不受欢迎。在拉多斯就是如此,这是一个位于约鲁巴海岸的很固执的奴隶出口城邦,于1851年被炮击,并最终于1861年被合并。[29]所以,欧洲经济利益在大西洋非洲的扩大,导致了它政治和军事干预程度的加深,这在开始时是有限的,但无疑奠定了后来彻底瓜分的基础。
英文版原书页码: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