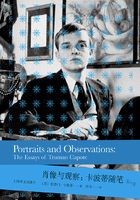
第1章 新奥尔良
(1946)
院子里伫立着一尊黑石天使像,天使的头部高耸在巨大的象耳草叶上方;天使明亮的眼睛,凝望着天空,像水手的眼睛一般,经过海水的冲刷变得蔚蓝。蓊蓊郁郁中,你可以站在一个隐秘的阳台上看到那尊天使像——这是我的阳台。我就在上面的三间房里住过,房子虽年代久远,却一尘不染,屋顶就像是婚礼上做工精细的蛋糕,宽敞的拉门,高大的落地窗。每逢暖暖的傍晚,只要这些窗子是开着的,屋内总会传来欢声笑语,清风拂过里屋,沙沙的响声,就像老奶奶在扇着扇子。在这样和暖的夜幕下,整个城镇也格外寂静。唯一能听到的说话声,是爬满了常春藤的门廊里交织着的家长里短;一个打着赤脚的妇女嘴里哼着歌谣,在人行道上摇着摇篮,大庭广众之下,哄着她怀里的宝宝进入梦乡;一个不耐烦的女子,坐在阳台上,一边嘟囔着外语,一边拔着鸡毛,准备把鸡扔进油锅,鸡毛从她的手中散落,慢慢悠悠地在空中飞舞,慵懒地徐徐飘落。
一天早上——我估计应该是十二月的某个礼拜天吧,天气阴冷,黯淡无光——我穿过那片街区,到老集市上去,每年的这个时候,集市里总会有些精美的时令水果兜售,譬如二十美分一打的蜜橘,还有冬日的鲜花——圣诞节用作装饰的一品红,以及白山茶。新奥尔良的街道通常呈现的是一幅幅漫长而孤寂的景象;闲暇时,这里的氛围和契里科很像,一切都是那般质朴,通常情况下(亮光穿过百叶窗的空隙斜射进来,透过百叶窗,你可以看见远处走动的修女,一只肥硕黝黑的胳膊懒洋洋地搭在窗台,一个寂寞的黑人小男孩正蹲在巷子里吹着肥皂泡,黯然神伤地望着这些泡泡飞到半空,相继破掉)可以从中看到激情。如今,在这样的一个早上,我驻足在街区的中央,一动不动,因为从我眼角的视线中,看到了一条地下隧道,一个杂草丛生的院子。一只凶神恶煞的白色猎犬一动不动地站在绿色的蕨类植物里,隧道的尽头闪着亮光,于是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隧道里面有一个喷泉;水从一个猴子模样的铜制雕塑嘴里溢出来,落在池中的鹅卵石上,发出清脆而凄楚的响声。他吊在一棵垂柳上,模样像个匪徒,一头铂金色的卷发,悬吊的身体绵软无力,就像这棵垂柳一样。恐惧飘浮在这样一座安静得令人窒息的花园里。紧闭的窗户袖手旁观;蜗牛沿着象耳草闪亮的银色区域爬行,除了他的影子,其余的都一动不动。垂柳前后晃动了一下,却并没有风。他手上戴的人造钻戒在阳光中一闪一闪,手臂上纹着一个名字,“弗朗西”。那只猎犬低下头去喝池中的水,于是我快步走开了。弗朗西——他自杀,莫非是因为她的缘故?我不清楚。新奥尔良是个神秘的地方。
我那岩石天使像的玻璃假眼就像是日晷,它们可以通过太阳光聚焦在上面的光量来显示时间:正午时分,是纯白色,而后会变得越来越暗,到了日暮时分,眼睛的颜色就会变深、变黑——暮色中的天使像,头上是那双暮色的眼。
一群金发小女孩,嘴唇干枯,正觊觎着屋子前方日渐倾斜的广告海报:畅饮纳特博士、胡椒博士、内喜、葡萄果汁、七喜、可乐、可口可乐。新奥尔良,素来也是以软饮料招牌而著称,在这方面同每一个南方城镇并无二致;孤寂的街区,大街小巷中,可口可乐的瓶盖密密麻麻,铺满路面,雨后,这些镶嵌在尘土中的瓶盖熠熠生辉,像是掉在地上的10分硬币。海报剥落了下来,横七竖八,散落一地,而后暴风又将它们吹散到沿街遍地,像是沙漠鼠尾草——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些海报还挺漂亮的;还有人把它们捡回去糊在墙上,和纳特博士、胡椒博士还有可口可乐的广告美女们放在一起,整日在租户们的床头挂着笑脸,夜晚扮演守护者的角色,早上又成了接受膜拜的圣人。海报随处可见,有拿粉笔写的,有印出来的,还有画出来的:“奥特加夫人——读物集”,“最爱的部分”,“魔幻文学”,“看见我”;“若你无事可做”……“不要在这儿做这事”;“你准备好见上帝了吗”;“当心恶狗”;“关爱可怜孤儿”;“我是一个聋哑寡妇,家里还有两张嘴要喂”;“注意;今晚我们教堂有蓝翼歌手(手写签名)牧师”。
爱尔兰海峡区的有个门上一度还贴着这样一则海报:“入内可瞻仰耶稣矗立之地。”
“你想干吗?”我按门铃的时候,一个妇女这样问道。“我想看看耶稣矗立的地方,”我对她说,一时间,她看上去有些茫然;她脸上的褶子,像是被刀刻过的一样,脸上的颜色,如同棉花糖一样雪白;她既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穿着印花棉和服。“你年纪太小,亲爱的,”她说着,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笑得连乳房都上下颤动,“你个鬼家伙太小了,看个什么耶稣矗立之地。”
我所在的街区,有一家咖啡馆当之无愧是最无趣的一家,那儿也是新奥尔良客人最少的一家,通常这里会是办丧事的地方。不过这家的老板娘莫里斯·奥托·昆泽太太,看上去似乎并不介意;她整天就坐在酒吧的后面,摇着蒲扇乘凉,除了打打苍蝇,几乎不怎么动弹。酒吧后面破旧的镜子上贴着七则内容相近的箴言:不要担心生命……没人能活着出去。
7月3日。Y小姐上周寄了一封“在家”邀请卡[1],于是我当天下午前去拜访。她以她那种古朴的方式给人愉悦,同时令你不禁莞尔,虽然她并非有意为之。我们初次邂逅时,我就想到了埃德娜·梅·奥利弗;她俩当然有一些相像之处。Y小姐说话的语气像是事先酝酿好的,但她说的话却很随性,而她雪利酒颜色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环顾四周。她的体态像是当兵的,手里拿着马六甲拐杖,因为一只腿短嘛,这番情形,使得她走路的时候一蹦一跳,那样子活像企鹅。“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这事儿让我很难过;的确,我得说确实如此,因为爸爸非逼着我去参加各种舞会,到了那儿我们就坐在漂亮的金色小椅上,我们就坐在那儿。没有一个男士邀请Y小姐跳舞,的确没有,不过有一年冬天,琼斯先生到这里来了,这个年轻人来自巴尔的摩,可是天啊!——可怜的琼斯先生——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唉——摔断了脖子——当场就一命呜呼了。”
我对Y小姐的兴致是纯逻辑性的,我也不是像她想的那种朋友,这点我得承认,尽管有些难为情,因为你无法对Y小姐有亲近之感:她太像是一个童话了,她真实存在——又虚不可及。正如她自家客厅中的钢琴——优雅,却有些走调。她的房子即便是在新奥尔良也足够老旧,周围的黑色铁护栏同样是破破烂烂;她住在一个贫穷的街区,街区里,房屋出租、加油站、自动点唱机酒吧的招牌随处可见。不过,在她一家子当年刚刚来此居住的时候——当然,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在新奥尔良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住处了。这座房子被倾斜的大树庇护得严严实实,从外部来看,简直就是一片黑影;但房屋的内部,Y小姐家族传承的奇幻风格随处可见:在她从鸟翼形楼梯上走下来的时候,颤颤巍巍的拐杖点地的声音清晰可辨;她的脸,像一块皴皱的丝绸,映射在高及天花板的镜子里仿佛烟雾;她低下身子(注意,她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格外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子骨),坐在她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椅子上,椅座看上去朴素得离谱,椅子上还有一对狮子头扶手。在屋内昏暗的光线下,她看上去漂亮而安详。这些就是她童年时期的围墙、栅栏和家具。“有些人生来就变老;譬如说我,就是一个怎么都找不到闪光点的坏孩子。可我喜欢变老。老了会让我某种程度上感到更加——”她迟疑了一下,打了手势指着昏暗的客厅——“更加舒坦。”
Y小姐不相信新奥尔良之外的世界;有时候,她的这种狭隘会带来一些近乎可怖的言论,就像今天一样。我向她提及近期的纽约之旅,而后她皱起一边的眉头,轻声地说道,“哦?乡村里都发生了哪些事情?”
1.我在想,为什么新奥尔良所有的计程车司机,听他们说话都像是从布鲁克林进口过来的?
2.对这里的食物,众人已久闻其名,诸如阿诺德和科博这样的餐馆算得上是全美数一数二的,或许这半点不假。这些餐馆的氛围很吸引人,也很宽松:慢悠悠的电扇,一张张大桌子,没有嘈杂的人群,有的是一片宁静,服务员都是临时工,而服务却很专业,看起来像是专为服务业而生的。我的一个朋友,在谈及新奥尔良和纽约的时候,曾说到过类似的东方菜肴,且不说价位比这里的要贵上许多,由于有些大厨过分矫揉造作,加上一些华而不实的配菜,已近乎于繁琐。正如大多数的极品一样,新奥尔良美食的特质,在他看来,正是源自于它那天生的简约质朴。
3.一直以来,对于“老式的魅力”这个说法,我多少有些反感。这里的建筑也好,古玩店也罢(存在于这样的城市当中真的是实至名归),抑或是在法国集市周遭听到的方言交谈,我想你都能从中发现这一点吧。然而新奥尔良与南部的其他城市相比,却算不上更有魅力——事实上,还不及那些城市,因为这儿是最大的。这座城市最主要部分的构成是精神洼地:远离观光带的街道与城区。
(选自致R.R的信)楼下的公寓又有新人入住了,也是去年的第三拨租户;这公寓是一个临时的栖身之所,总有问候与话别。我初来乍到的时候,这里住着一个名副其实的恶棍。此人不拘小节,衣着邋遢,人品恶劣——属于那种沉迷酒精、放荡不羁的好色之徒。巴迪先生——光杆乐队。要是你此前在哪儿见过此人,那也再正常不过——当然不是说在这里见过,而是在别的城市,因为他总是东奔西走,居无定所,一个人,带着他的旧班卓琴、架子鼓和口琴。我时常碰见他在不同街头的角落里敲个不停,周围聚集着一帮游手好闲的人。意识到他是我的邻居后,这样的碰面总是让我一阵难受。现在说句实话,他的歌唱得也不算差劲——事实上,还挺出众的,某天下午很晚的时候,他伴着吉他唱着民谣,算是自娱自乐的那种吧,歌声鬼魅,带着悲伤与酒精:恋爱中的人啊,是多么可怕。
“嘿,小子,说你呢!站住……”我就是他喊的那个你,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叫什么,也没什么兴趣知道。“给我下来,帮我去杀了一对情侣。”
他的阳台比我的还小,爬满了紫藤花,幽香扑鼻;屋子里也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于是我们就坐在绿荫下的地上,喝着一种杜松子酒,跟药用酒精差不多的那种,他开始拨弄吉他的琴弦,哀伤的旋律令他震颤的声音愈发突出。“全玩儿完了,来的来,去的去,一切的一切;六十五,任何跟我交往过的女人都不会跟其他人怎么样;是啊,我有过很多妻子,很多儿子,可上帝才知道他们过的如何——我也压根儿不在乎——大概除了朗达·凯伊。有一个女人,嗯,甜蜜动人,和我也是格外来电!无时无刻不激情四射,后来她又嫁给了一个牧师,生了四个孩子——五个,算上我的那个。我总在想到底是个——儿子还是女儿呢——儿子吧,我想。我那些女人总是生儿子……那都是多年以前的事儿了,发生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没错,哪儿都去过,去过监狱,去过像洛克菲勒住的那种豪宅,来的来,去的去,周而复始。”
他就一直这么唱啊唱啊,直到月亮出来,他的嗓音变得像蛤蟆一样低沉,吐字含糊不清。
他的脸,脏兮兮又皱巴巴,带有一种欺骗性的善良,眼神看上去很幼稚,但他的眼睛是斜的,像东方人的模样,他把指甲也蓄得很长,尖得像把小刀,像中国佬[2]那样磨得锃亮。“留着方便抓痒吧,打斗的时候还能随时派上用场呢。”
他总是穿着单一:一条黑长裤,一双红袜子,像发动机的颜色,一双网球鞋,足尖有个豁口,图个舒服,一身大礼服,一件灰色天鹅绒马甲,他说,是他的先辈本杰明·富兰克林穿过的,还有一顶贝雷帽,上面镶着“把票投给罗斯福”的钮扣。他身边没什么亲朋好友——他确实有过一大帮女性朋友——每周一换,这一点不假,而哪个女人不给他做饭的时候却几乎没有;每逢那些场合,我登门造访的时候,他总会很谦虚而又不失威严地说,“认识一下巴迪太太。”
一天深夜,我一觉醒来,隐隐感觉身边还有人在;没错,房间里确实有人,我从镜子里可以看到月光下的这个人。就是他,巴迪先生,鬼鬼祟祟地打开写字台抽屉,随后又把它关上,忽然间,我的一盒硬币散落在地板上,蹦蹦跳跳,滚得遍地都是。这个时候,任何的掩饰都无济于事,于是我打开台灯,巴迪先生看着我,俨然一副光明正大的表情,没有半点狼狈的神色,他咧着嘴笑道。“听着,”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清醒的样子,他说,“听着,我立马就得离开这儿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他望着地板,脸色开始有些泛红。“行行好,做点好事吧,你有钱吗?”
我只好指了指地上散落的硬币;他二话没说,便蹲了下来,把这些硬币拢在一起,挺着腰杆,出了房门。
第二天早上他就不见了踪影。三个女人来此打听过他的下落,我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或许他是去了莫比尔。如果你在那附近见到他,R,请给我寄张明信片过来,好吗?
我想有个肥老妈,耶!耶!猎枪的手指,长得像香蕉,厚得像莳萝泡菜,敲击着琴键,脚跺着地板,令整个酒馆震颤。猎枪!本城最盛大的演出!狗屁不值的歌唱,可老兄,他居然可以弹琴——听啊:她体温夏天凉来秋天暖,四季老妈的好啊说不完……他就这么唱着,肥硕的嘴巴大张着,活像鳄鱼的大嘴,他那红红的舌头,品味着这段旋律,钟情着这段旋律,与它尽鱼水之欢;啪,猎枪啊,啪啪啪……看着他大笑的样子,那张疯狂的黑色面孔,满是子弹掠过的伤痕,伴着汗滴闪烁。还有他不知道的人间罪恶吗?不过有些遗憾……几乎没有白人与猎枪谋面,因为这是间黑人酒馆。去年圣诞节留下的落满尘土的装饰,为油漆剥落的墙面平添了色彩;橙、绿、紫相间的条纹瓦楞纸,悬挂在没有灯罩的灯泡旁,在慢悠悠的电风扇中来回摇晃,酒馆老板是个混血儿,长得挺英俊,乳蓝色的眼睛耷拉下来,他倚靠在吧台,大声吆喝,“朝这儿看,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施舍铺子吗?收起你那两毛五,黑鬼,快给老子滚开。”
这是个礼拜六的晚上。屋子在香烟的云雾缭绕和周六晚间的香气中漂浮了起来。所有油腻的小木桌周围都有两圈椅子,大家彼此认识,一时间整个世界就存在于这间屋子里,这间漆黑、奔放而又恐怖的屋子;我们的心跳就是猎枪的步点,我们生命中每个欢愉的元素都浓缩在他那凶险的眼睛里。我想有个肥老妈,耶!耶!他在凳子上一直说唱着,抬起头正视着我们,夜色中升起一片急促的呐喊声:我想有个肥老妈,浑身是肉尽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