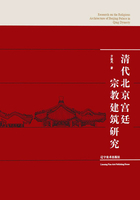
第二节
明代的宫廷宗教建筑情况
一、明代皇城内的宗教建筑情况
明代的情况可以确知的要比前代充分得多。一则年代未为久远;二则史料尚未湮没;三则清代的皇家建筑有许多是因袭明代的旧物,有一定的延续性,可追索的线索多。因此对明代宫廷之中的宗教建筑情况的考察,对研究清代宫廷宗教建筑具有非常直接的意义。
有些建筑在史料中露出了蛛丝马迹,但具体情况无所考证者,本书暂不予讨论,尤其是连方位也不能确定的建筑,如弘治五年六月,光禄寺造皇坛祭器,皇坛是宪宗斋醮之所[1],此皇坛就无法判定其位置。明代崇道,历代都有所兴修,也有所变更,以一人之学力恐难一一辨清了,就目前所掌握的概述如下。

图3 大高玄殿平面
(一)宫苑之外的宗教建筑
明代的皇城禁卫森严,非清时可比,皇城可以看作是宫城的放大,某些功能辐射到了禁宫之外,或者说有些活动,如宗教玄修,只有在禁宫之外才张扬。皇城之中有许多功能性很强的建筑和场所,用来辅助宫廷生活达到一个较为舒适的水平,或弥补禁城之中宫廷生活的不足。
明嘉靖帝之崇奉道教,在皇城之内宗教建筑的情况上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大高玄殿是其中一处较为重要的建筑,作为“习学道经内官之所居”[2],门前有二石碑“曰宫眷人等至此下马”[3],以示尊崇。大高玄殿为一路狭长的院落,规模并不大,见缝插针,有说其中牌楼上的题字为严嵩所书,此殿始建于嘉靖二十一年[4],以时人讥讽“青词宰相”相度[5],严嵩题字,大有可能。明代帝王崇奉道教由来已久,自明太祖朱元璋始,成祖继之,到世宗时,可谓登峰造极,毁佛寺,同时也大兴土木,其中大部分是为了道教活动所用。此处也经常召见大臣,明夏言有《雪夜召诣高玄殿》诗[6]:
迎和门外据雕鞍,
玉 桥西度石阑。
桥西度石阑。
琪树琼林春色静,
瑶台银阙夜光寒。
炉香飘渺高玄殿,
宫烛辉煌太乙坛。
白首岂期天上景,
朱衣仍得雪中看。
可以肯定深夜召见并非为了国事,道教的斋醮仪式都在半夜进行,仪式内容之一是拜表即上青词,明世宗的青词都是命大臣写的,此时召见必定就是奉召来写青词了。从这些情况来看,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此类建筑要建在禁城和内苑之外了,因为外臣往来比较方便。
大高玄殿的建筑颇有特色,殿前有二亭,与角楼相仿,称“九梁十八柱”。 内有象一宫,供奉象一帝君“范金为之,高尺许,乃世庙玄修之御容也”[7],此处也是明世宗率修的斋宫之一[8],以帝王之身而成教中偶像之事,由来已久,清亦有之,国外的宫廷礼拜堂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帝王此时具有了双重身份,统辖着身在其中的人们,不仅是世俗的权威,也是彼岸世界中的神圣一员。明时的情况只有《酌中志》中约略提及[9],有殿阁名称,详情不可考了,《旧都文物略》描述了清朝遗留下的建筑情况:入正门之后“左右各有钟鼓楼一,中为正殿,殿七间,东西配殿各五间,过大高玄殿为雷坛殿,五间,两旁配殿各五间。过雷坛殿,有殿三间,制上圆下方,二层,上题‘乾元阁’,下题‘坤贞宇’。此全殿为明时建造,清乾嘉间重加修饰,供奉玉皇,为祈雨之所。”基本格局同明时相同,只是名称改变了,殿内的内容也有所变化。
另一处重要的宗教场所就是大光明殿,《旧都文物略》称此即为明万寿宫,而在《北京历史地图集》中,大光明殿与万寿宫毗连并存。嘉靖时,万寿宫毁于火,而大光明殿的活动屡见之于文字,肯定不是同一处。明王世贞有《西苑宫词》,从中可以一窥当时的情景:
色色罗衫称体裁,
铺宫新例一齐开。
菱花小样黄金盒,
昨夜真人进药来。
两角鸦青双箸红,
灵犀一点未曾通。
自缘身作延年药,
憔悴春风雨露中。[10]

图4 大光明殿平面图
帝王迷恋道教,长生此其一,纵欲此其二,从上述宫词中可以感受到这点。这也是道教名声不好的一个原因,有明一代为劝谏皇帝远离此道而丢掉性命的大臣,不计其数,仅嘉靖一朝,就有数十人。至清代,此处作为拜斗殿,高士奇、汤金钊曾赐居于殿侧。使得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文字一窥其中堂奥,“在西安门内万寿宫遗址之西,地极敞豁。门曰登丰。前为圆殿,高数十尺,制如圜丘,题曰大光明殿。中为太极殿。后有香阁九间,题曰天玄阁。高深宏丽,半倍于圆殿。皆覆黄瓦,甃以青琉璃,下列文石花础作龙尾道,丹楹金饰,龙绕其上。四面琐窗藻井,以金绘之。白石陛三重,中设七宝云龙神牌位,以祀上帝。相传明世宗与陶真人讲内丹于此。”[11]建筑的装饰相当富丽,就内容而言也是将宗法性宗教的祭天同道教礼仪混合,颇能反映当时的宗教观念,儒道混合不仅仅是在嘉靖朝,只是嘉靖朝的崇道有些出格。明代皇城之中的这些道教建筑在具体的使用上各有不同的侧重,不惟是宗教功能,因为明世宗不再在宫中居住,这些宗教建筑承担了一定的朝会功能,“自西苑肇兴,寻营永寿宫于其地。未几而元极、高元等宝殿继起。以元极为拜天之所,当正朝之奉天殿。以大高元为内朝之所,当正朝之文华殿。又建清馥殿为行香之所,每建金箓大醮坛,则上必躬至焉。凡入直撰元诸侥臣,皆附丽其旁。即阁臣亦昼夜供事,不复至文渊阁。盖君臣上下,朝真醮斗几三十年”[12]。明世宗作为道教皇帝可谓名副其实,也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一位皇帝。这些东西一改朝换代马上就废止了,以明代普遍崇道的传统看,这些都是荒唐至极的事。
大光明殿之南有兔圜山,“相传世宗礼斗于此”[13]。此处总体上是一处园林,叠石为山,还有一些奇巧的喷泉、岩洞、曲水等景致,“明时重九或幸万岁山,或幸兔儿山清虚殿登高”,[14]兔儿山得名可能与此有关,于高处礼斗符合道教的教义。宗教同园林结合的例子比比皆是,园林之兴在帝王而言,游观是一方面,表达孝心也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借太后之名同样屡有兴筑,清馥殿即为其一。“度金鳌玉 桥,西转北,明世宗所建,常奉兴献太后来游”。严嵩有诗句“共传今圣孝,当日奉慈游”,说的也是此事。此处是属于宫苑性质,园林景致有亭台楼阁、仙宫洞壑,颇为可观[15]。
桥,西转北,明世宗所建,常奉兴献太后来游”。严嵩有诗句“共传今圣孝,当日奉慈游”,说的也是此事。此处是属于宫苑性质,园林景致有亭台楼阁、仙宫洞壑,颇为可观[15]。
玉芝宫是皇城中一处特殊的皇家家庙,“即睿宗献皇帝庙也。”[16]睿宗献皇帝就是明世宗的生父,明世宗为抬高其生父的地位可谓煞费苦心,不顾大臣的反对,甚至廷杖致死了数位大臣,终于为生父争得了皇考的地位。本来此宫名为献皇帝庙,在成功地将生父升祔太庙之后,差不多处于闲置的状态,后传出有祥瑞,改名玉芝宫,好是热闹了一阵[17]。这是一处独立的专门祭祀其生父的建筑。在整个争名分的过程中还有其他的建设活动,如紫禁城中的崇先殿等。在那个时代,祭祖建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二)西苑、景山之内的宗教建筑
西苑、景山在明代也是重要的宫廷生活场所,其使用的频率要高于清代的使用频率。明代帝王的生活多局限在皇城之内,没有像清代帝王那样在北京西郊建设了成片的园林群组,因此西苑就成了他们游观的主要场所。景山位于中轴线上,风水和空间总体构成上的意义要大于其作为园林的游赏价值。西苑、景山虽为清代沿用,但其中的建筑变动也较大,尤其是北海一区,现存明代的建筑几乎没有了。造成了我们现在想要深入了解其中明代宗教建筑的情况困难。只能根据文献记载,知其大概了。
1.景山
景山山北有寿皇殿,现在的寿皇殿是乾隆十五年时修建的,比明代的寿皇殿规模要小得多,即雍正时所建寿皇殿也只有三开间,又顺治时曾在寿皇殿为董后起建道场,十分热闹,则顺治时的寿皇殿当为明代旧物,不知与雍正时的寿皇殿有何不同。清代的寿皇殿是属于家庙形式的建筑,类似于奉先殿。明代时其功能如何,不能确知,《酌中志》只提及寿皇殿同御马监左右毗连,从其命名来看也像是用来供奉祖先神位的场所,但其位置又表明其等级不高,而且文献中也并未提及供奉神位的情况,始建年代也不清楚。景山为宫廷苑囿中禁卫最为森严的地方,别无宗教建筑了,因为登山可俯视宫中情形,又在中轴线上,风水所系,格外重要。
2.西苑
西苑属于大内宫苑,明代没有在西郊发展园林,此处就是皇家重要的避暑地,也是使用较为频繁的游观场所。明世宗由于宫婢之乱,不敢再住在宫中,之后就一直住在西苑,耽于道教修炼,不问朝事。明嘉靖年间,西苑出现了众多的道教建筑,或含有道教用途的建筑。同时由于政治中心的偏移,在西苑中也兴建了一些宗法内容的建筑,西苑的活动在嘉靖年间出现了一时之盛,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
明代礼制在嘉靖年间得到一次大的整理,起因是明世宗为了生父升祔太庙,显然以此发端之后,明世宗对此饶有兴致,不断有所发明,“嘉靖十年,上于西苑隙地,立帝社帝稷之坛。用仲春仲秋次戊日,上躬行祈报礼。盖以上戊为祖制社稷祭期,故抑为次戊。内设豳风亭、无逸殿,其后添设户部尚书或侍郎专督西苑农务,又立恒裕仓,收其所获以备内殿,及世庙荐新先蚕等祀。盖又天子私社稷也,此亘古史册所未有”[18]。无逸殿同时也有劝农之意,同先蚕坛一起,所谓农桑并举,正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耕织二门。无逸殿中也设有先皇神位[19]。上述这些建筑加上北海北岸的雩祷之用的雩殿和供奉祖宗列圣神御的太素殿[20],构成了西苑之中的一个儒教建筑的小系统,其内容已颇为完备,足不出园而诸礼遍行。问题是明世宗只顾到了自己方便,而没有搞清楚封建礼法所具有的国家意义,所谓私礼不可久也,大礼所应有的严肃性和庄重感不能被破坏。很快,帝社帝稷之坛就被罢废了[21],这一创新没有成功。明宪宗在宫中所创的玉皇之祠而用郊天之礼,也是很快被废(详见下节),宗法性宗教发展到明代已有了极为牢固的根基和规则,并不是轻易能改变的,即使帝王也难免失败。
亲蚕之礼始于明代嘉靖年间,亲蚕殿、蚕坛、土谷坛都在仁寿宫一区,位于中海西岸紫光阁北。礼议于嘉靖九年,坛殿建成于嘉靖十年三月[22]。蚕坛的议礼过程中,曾建坛于安定门外,同先农坛相对应,后考虑后宫出行不便,改在西苑内,这点同清朝建立先蚕礼的过程惊人的相似,颇可玩味。蚕坛之中“有斋宫、具服殿、蚕室、茧馆,皆如古制”。而行礼的人员构成不仅有皇家女眷,还有朝廷命妇,王侯大臣之妻,其礼载于祀典。有趣的是亲蚕礼也是只实行了很短的时间即废,“而农务则终世宗之世焉”[23]。由此可看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中,由女子担当主角的大型祭礼在实施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困难,并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其夭折也在情理之中。
芭蕉园就是明世宗设醮的地方,门口立下马碑,与大高玄殿前一样。在明代实录告成要在此焚草,七夕时也有活动,七月十五做法事、放河灯,有不少活动。[24]苑中规模较大的一处道教建筑为雷霆洪应殿,“雷霆洪应之殿有坛城、轰雷轩、啸凤室、嘘雪室、灵雨室、耀电室、清一斋、宝渊门、灵安堂、精灵堂、驭仙次、辅国室、演妙堂、八圣居,具嘉靖二十二年三月悬额”[25]。这个时间正是嘉靖刚开始定居西苑(宫婢之变是嘉靖二十一年),可能原也有建筑,额名改挂,从命名看应是祭雷电之神。
京城水系对皇家来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西苑水体占据了园林的主要面积,是景观中控制性的要素。对水的重视反映到建筑上,就是兴建祠宇,通过祭祀仪式和建筑这种直观的、形而下的手段来表达。“嘉靖十五年,建金海神祠于大内西苑涌泉亭,以祀宣灵宏济之神、水府之神、司舟之神。二十二年,改名宏济神祠。”[26]“宏济”之名也寄托了美好的祈愿。大西天经厂也始建于明代,具体年代暂无考,清乾隆年间扩建,留存至今。
3.其他
重华宫是一个功能特殊的建筑群,“前曰重华门,曰广定门、咸熙门、肃雍门、康和门,犹乾清宫之制。后有两井,东西有两长街。西长街则有曰兴善门、丽景门、长春门、清华门、宁福宫、延福宫、嘉福宫、明德宫、永春宫、永宁宫、延禧宫、延春宫,凡妃嫔、皇子女之丧,皆于此停灵,……东长街则有广顺门、中和门、景华门、宣明门、洪庆门、洪庆殿,供番佛之所也。”[27]由此可知,重华宫有三路建筑,中路规制较高,仿乾清宫的样子。东西两路,西为停灵之用,东为供佛之所,供佛和停灵显然是两个相互配合的功能,供佛是为了使死者的灵魂得到超度,这也是宗教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安抚死者及其眷属。重华宫可以看作是明代皇家的殡葬建筑,妃嫔、皇子女最终是用墓葬葬于西山等处坟林,但操办丧仪的过程需要专门的场所。专门的场所出现,说明庞大宫廷的生活制度化的程度较高。重华宫的使用对象是属于宫廷中第二等级的人物,最高等级的人物,如皇帝、皇后、太后等,他们的灵柩往往就在生前居住的地方停放,另有更高规制的丧仪。同时还有等级更低的宫眷,他们的殡葬制度又别有一套,据《宛署杂记》载:“宫人有故,非有名称者,不赐墓”,暂停于安乐堂,然后移送北安门外停尸房,“易以朱棺,礼送之静乐堂火葬塔井中”。火葬塔的形制是:“砖甃二井,屋以塔,南通方尺门,谨闭之,井前结石为洞,四方通风”。塔而有此等用途,有此等形式,可能也是一个孤例了,显然此塔并非宗教建筑,但确实具有一定的宗教意味,利用佛塔这一形式也是有所用意的:“非有名称者,不得赐墓,示有等也;非合铜符,不得出槥,重宫禁也。夫既礼送之出矣,而必付之烬掩,防奸欺也。以蔽帷蔽盖之义,施掩骼埋胔之仁,必建塔而焚之。若曰,佛之徒以王宫殊色,因缘示寂,非女子乎?瘗雁建塔,乃旌彼德,旃檀荼毗,何恤以神道设教,而不与民间蔂梩同也?”[28]宗教的社会功能,此为其一也。清代皇城之中也有类似的殡葬建筑,名为吉安所,并没有沿用明朝故旧,其址为司礼监廨,但具体情况已然不清了,其中可能或者说应该也有宗教内容的建筑或建筑形式,此为一个猜想,暂存一说。
二、明代宫城之内的宗教建筑
明代宫城之内的宗教建筑有相当一部分是被清朝的满族统治者所保留沿用的,对于这部分建筑在本节就不加详述而放在清代宫廷宗教建筑的介绍中做重点论述。皇城与宫城相比,其中的宗教建筑在明代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皇城之内几乎没有佛教建筑,基本上都是道教建筑,而宫城之中却不乏佛教建筑。这一现象可能要归结于明世宗入继大统之后,开始毁佛寺、逐僧人,虔奉道教这一点上。那么为何宫城之中的佛教建筑可以幸免呢?这可以解释为一种有限度的宗教信仰自由,就像重华宫供佛同停灵相配一样,宫中的女眷需要佛教,尤其是太后、太妃等年老之人。同时尽管道教在有的学者看来属于阴柔的宗教,同儒相对,但是道教从其所习的内容看却是男性本位的宗教,尤其房中术之类,女眷不会热衷此道,即帝王本身可能也不会希望女眷迷恋此道,何况太后、太妃等年老之女性呢。[29]
(一)宗法性宗教祭祀建筑
明一代对道教的尊崇在历史上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具体考察的话,不难发现不同的皇帝具有不同的宗教态度,采取了不同的宗教政策,本文限于主题对明代帝王的宗教态度不做展开论述,但建筑演变的过程似乎也在明白地告诉我们,即明初的帝王仍然是以宗法性宗教为重,道教建筑在宫廷生活中频频出现的事在明中后期为多,尤其是在嘉靖年间。
奉先殿是明代宫廷中最早的宗教建筑,太祖在南京建造皇宫的时候就建设了奉先殿[30],“以太庙时享,未足以展孝思,复建奉先殿于宫门内之东”[31]。自此,皇宫内建祭祀皇帝先祖的家庙这种形式就一直保留了下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皇宫建制悉仿南京,同样建有奉先殿,其位置也在东路。奉先殿在宫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既不与外朝相连,也不与内宫相通,紧邻景运门,仍是宫城之中较为重要的位置。据许以林《奉先殿》一文考证,明时奉先门外无建筑,现在的样子是清朝时改的。南京的奉先殿为“正殿五间,南向,深二丈五尺,前轩五间,深半之”[32],显然朱棣在营造宫室的时候并未拘泥于南京故宫的奉先殿形制,其规制一如太庙,要比先前的等级提高不少,这座家庙在礼法系统中的象征意义也随之上升,得到了强化。
明代在奉先殿的附近出现了几座具有家庙功能的祭祖建筑,西侧有奉慈殿,是明孝宗在弘治年间所建,供奉其生母的神主[33];还有弘孝殿、神霄殿,分别奉安孝烈皇后、孝恪皇太后的神位。弘孝殿原为景云殿,明穆宗隆德元年三月改名。孝烈皇后为明世宗之妻,孝恪皇太后为明穆宗生母[34],这种频繁的建庙活动源头在明世宗。明世宗即位后,嘉靖二年,“葺奉慈殿后为观德殿”,五年,“以观德殿窄隘,欲别建于奉先殿左”。“嘉靖六年三月,移建观德殿于奉先殿之左,改称崇先殿,奉安恭穆献皇帝神主。”[35]其具体形制已不可考。明代几位皇帝由于没有子嗣,造成了继位的皇帝其生身父母的地位按照礼法制度不能入享太庙,这对于皇帝来说无异于骨鲠在喉,因此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要为自己的生身父母争取名分,同时也是抬高自己的血统,家庙的建设可谓是一个相宜的变通举措。从中也可以感受到宗法性宗教在当时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其直接同政治生活相关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宗法性宗教的礼法系统其不近人情的一面,相当残酷。这些建筑的存在对封建礼法来说也是一个讽刺,帝王通过自己的蛮横突破了礼法的规定,因此改朝之后很快就以将神主迁祔奉先殿这一变通的办法而罢废其中的祭礼[36],建筑往往也就闲置了。明代的末代皇帝崇祯帝也在奉先殿一带有所兴建,供奉其生母孝纯刘太后及七后的神主[37]。
值得一提的是,嘉靖帝为了将其生父祔太庙展开的这场议礼斗争,使其对明代的礼制进行了全面的审核,由于欲尊崇其生母蒋太后,对东朝宫院的建筑也重新定制,其时原太后所居仁寿宫毁于火灾,也为其创立新制铺平了道路。为配合这些举动,嘉靖帝同时经营了天地日月诸坛和太庙,这些都是在一个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完成的。嘉靖一朝形成的建筑格局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明代宫廷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
同皇城中出现了一些儒道合用、与宗法性宗教有所“创新”的建筑一样,在正宫之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明宪宗曾“于宫北建祠奉祀玉皇,曲郊祀所用祭服祭品乐舞之具,依式制造,并新编乐章,命内臣习之,欲于道家所言降神之日举行祀礼”。成化十二年八月,有大臣上书进言,认为“天者至尊”,如此“未为合制”等,并建议“凡内廷一应斋醮悉宜停止”。好在明宪宗没有那么专横,居然“命拆其祠”[38]。具体在宫北何地无从稽考,可能还是在御花园中。宪宗在明代也是一位崇道的皇帝,前者已有皇坛之建,但比之明世宗几乎可称之为“从善如流”了,不一意孤行,善莫大矣。明世宗就坚决利用道教建筑行宗法性宗教之礼,“嘉靖十七年,大享上帝于元极宝殿,奉睿宗配。十八年二月,祈毂于元极宝殿”[39]。对这位道教皇帝来说,可能也不存在这种儒道之间的界限,但这种界限存在于与他对立的官僚系统之中,这个系统中的成员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宗法性宗教的制度的合理性和纯洁性,这对于考察三教关系来说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前朝的文华殿为东宫讲学所在,照例有圣人牌位,清代沿袭了这些牌位。原先的文华殿中是孔子塑像,这是继承了元代的传统,后许诰以其所著《道统书》上之,改为木主[40]。文华殿的后东室还作为皇帝斋居之所。而“孟夏祀灶,孟冬祀井”[41]都属于五祀的范畴。文华殿后在嘉靖十七年建了圣济殿,即清代文渊阁的位置,祭祀先医[42]。圣济殿的朝向为北向,“殿之东北,向后者曰圣济殿,供三皇历代名医,御服药饵之处”[43]。此处圣济殿殿名之“济”字,当是济世救民之意,其为何北向,尚待考证,不知何解。
(二)道教建筑
明代的崇道是其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但宫廷之中兴建道教建筑却并非一开始就有。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贫寒,在征战过程中与僧道均有接触,而任用道士刘伯温更是富有传奇色彩。太祖本人也精通道教斋醮科仪,但他的政策却是尊儒抑道,从治国方面考虑还是儒教为先。在南京故宫中并没有道教建筑的痕迹,可作为一个例证。
明成祖基本上继承了太祖的做法,但成祖为使夺取政权合法化,不得不依赖道教,在宗法性宗教的路子里他是毫无出路的。明代崇祀真武,根子就在于他。时为燕王的朱棣,居于北方,以玄武配,道理就在于此。元代蒙古统治者也奉真武为守护神,因为他们由北方而统一全国。朱棣以封燕地发迹,继而取建文而代之,兵事之中即“被发跣足,建皂纛玄旗”,天下大定之后,武当大兴[44],京城之中建真武庙,紫禁城中则有钦安殿——“供玄天上帝之所也”[45],玄天上帝者即真武。北京宫城仿南京故宫,但南京宫殿之中并无钦安殿,中轴线上也别无宗教建筑。由此可知,钦安殿的建设完全出于明成祖对真武的崇拜和信奉。其时的宫后苑的规模可能也不如后来。嘉靖时为钦安殿增加了缭垣和天一门,天一生水,水在五行中也是配北方,更绝的是殿后正中一块栏板为双龙戏水纹,这块栏板是北中之北,以水纹装饰,整座建筑是充分围绕着“北”这个概念来做文章。崇祯帝问政于危难之时,对道教有所抑制,曾撤出宫中许多神像,唯钦安殿内没有受到影响。其地位由此可见。《篷窗日录》载:“北京奉天殿两壁斗拱间绘真武神像。”[46]可见这真武崇拜不是空穴来风,影响所及也不仅仅是立祠崇祀那么简单了。

图5 钦安殿东西为七所的假想图
钦安殿的建筑形式颇有特点,为重檐盝顶,这是非常奇怪的一点,盝顶是等级极低的屋顶形式,作为一个位于中轴线的建筑来说不相匹配,又用重檐,似欲提高其等级。联系到杨文概曾提出的乾东西为七所的说法,窃以为如果两侧为七所的话,钦安殿周围的空间尺度同现状有较大不同,采用这一屋顶形式的目的应当是使建筑在整个空间组合中不至过于突出,减小其形象尺度[47]。钦安殿坐落在汉白玉石单层须弥座上,南向,面阔5间,进深3间,由于尺度不大,所以明间减金柱,以求得较大的室内空间,黄琉璃瓦顶。殿前出月台,四周围以穿花龙纹汉白玉石栏杆,龙凤望柱头。
御花园现有格局可能成于明嘉靖年间,钦安殿东西两侧南有千秋亭、万春亭,北有澄瑞亭、浮碧亭,西南方有四神祠,整个御花园的建筑格局方正,除有植物繁茂、叠石玲珑外,没有一般园林建筑布局所特有的自由变化和天然之趣,此中固有其位于中轴线的尽端,要延续整体布局的气势与法度,窃以为还有道教举行斋醮仪式的需要,这种方正的布局非常利于建道场。明世宗重玄教,嘉靖二年就开始建斋醮,改建御花园时考虑斋醮仪式的需要也是非常自然的事。当然目前这只是一种推测,没有充分的证据。从别的宗教建筑的特点看,建筑布局或形制附会教义的不乏其例,是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钦安殿举办道场、建斋设醮的频率相当高,如此则御花园的重要功能并非游观休憩,而是一套道教科仪。
隆德殿是又一处道教建筑,位于景福门内,“其两幡杆插云向南而建者,隆德殿也。旧名玄极宝殿,隆庆元年夏更曰隆德殿,供安玄教三清上帝诸尊神。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毁,天启七年三月初二日重修。崇祯五年九月,内将诸像移送朝天等宫安藏。六年四月十五日,更名中正殿。东配殿曰春仁,西配殿曰秋义。东顺山曰有容轩,西顺山曰无逸斋”[48]。毁而复修,可见此建筑有其必需的理由,不能马上复修肯定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宗教建筑的兴建背后能考察出不少经济状况。除了上述堂而皇之的宗教建筑之外,宫中还有一处炼丹场所,建在一个角落里,“养心殿之西南,曰祥宁宫。宫前向北者,曰无梁殿,系世庙烹炼丹药处。其制不用一木,皆砖石砌成者。月华门之西南岿然者,隆道阁也。原名皇极阁,后更道心阁,至隆庆四年春更此名”[49]。炼丹需用火,因此完全用砖石为之,是非常合理而周到的设计,也是形式追随功能的一个例子,宫中出现炼丹场所,这是唯一的一处,选址临近膳房,是否考虑到都需用火,放在一起比较方便呢?起码燃料的堆放、储存并于一处是较为方便的。这应当也是明世宗时始建的,紫禁城作为正宫,有些行为是不宜于在其中举行的,炼丹即为其一,只有那种沉溺于此道、罔然不顾其他的帝王才会如此行事,也只有明世宗了。并且这也应当是在宫闱之变以前兴建的,其后他久居西内,不事朝事,也用不着此处了。[50]
前朝之侧,还有一处佑国殿,“出会极门之东礓嚓下,曰佑国殿,供安玄帝圣像”[51],此殿的位置极其显要,与内阁并列,显示了道教在明代具有相当于国家宗教的地位,据杨文概文中认为此已是明代后期的状况[52],不知所据为何。该建筑也是供奉真武,名以佑国,颇合明时情形。
明代一直以关公为政权的保护神,洪武、永乐时期分别在南京、北京建关公庙。明万历二十二年道士张通元请进爵为帝,四十二年敕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53]。关公为武圣,明代尊崇关公同明代多内外忧患、频繁用兵有关。因此宫城内“至如宝善门、思善门、乾清门、仁德门、平台之西室及皇城各门皆供有关圣像也。”
(三)佛教建筑
明代宫城[54]之内的佛教用途的建筑主要有英华殿和慈宁宫大佛堂等处。英华殿位于隆德殿西北,“即降禧殿,供安西番佛像。殿前有菩提树二株,婆娑可爱,结子堪作念珠。又有古松翠柏,幽静如山林。”相传此二株菩提为万历帝生母慈圣李太后所植,殿内“有九莲菩萨御容,明神宗生母慈圣李太后也。”其始建年代不详,从所供西番佛像来看,也可能是武宗正德年间所建,因为武宗曾引番僧入宫,习房中术。从原名降禧看,似乎此处原来同道教有关系的可能性要大于同佛教有关系,改名英华是在隆庆元年的事,明穆宗对道教多有裁抑,迥异于明世宗,此番改名是否意味着此地原来曾是道教活动场所呢?而习番僧房中术本身倒不一定就以佛教之名行之,这只能暂且存疑了,以俟更多的证据。明代遇万寿、元旦等节于此处做佛事,有相当热闹的表演,原由番经厂的内官为之,天启辛酉后奉旨改由宫人为之。英华殿的建筑及其中的活动一直保留到了清代。
慈宁宫建于嘉靖朝。明代洪武、永乐两朝无太后,所以没有创立这方面的典制,自宣德朝开始太后居于仁寿宫。仁寿宫本是皇帝别宫,“统于乾清宫”,其位置相当于现在的慈宁宫本宫区。嘉靖年间,仁寿宫遭焚毁,适逢明世宗欲使其生母蒋太后和孝宗的太后分而居之,决定在外东路、外西路各建一宫,即慈庆宫和慈宁宫。从其谕旨“拟将清宁宫存储居之地后即半,作太皇太后宫一区;仁寿宫故址并除释殿之地,作皇太后宫一区”来看,此处原来也是有佛教建筑的。因此,慈宁宫后建大佛堂就是必然之举了,佛堂已成了太后生活的必需。尤其慈宁宫是明世宗生母所居,尽管世宗毁寺逐僧,但在此处为表孝心,照样建佛堂,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宗教文化。以慈宁宫判断,则慈庆宫也应该有佛堂之类的宗教建筑,但目前无线索可循。
慈宁宫花园从清代的情况看,其中也包含了相当多的宗教内容,但在明代的情况如何呢?不得而知。慈宁宫花园同慈宁宫应是同时建成,是为慈宁宫配套服务的。同样,慈庆宫也有慈庆花园。慈庆宫及其花园到清代已不复存在,慈宁宫花园至今尚存,但明清两代多有变化,明代的确切情形已不可知了,其中所供佛像等物究竟始于何时,只能暂且存疑了。
4.其他
宗教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是渗入各个方面的,中国的宗教特点是多神信仰,并且有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保留着许多比较原始或民俗化的内容,其宗教属性是很难界定的,本文专设“其他”一节来针对这些方面的建筑。这些宗教实践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行业神的崇拜,宫城之中起码有两处,一处是马神庙,一处是圣济殿。马神庙在东华门之北,同御马监毗连。文华殿东还有一处神祠,“殿之东,曰神祠,内有一井,每年祭司井之神于此。”宫城之中,类似行业神祭祀的场所就是这些,都是同宫廷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皇城之中散布于各个管理部门的行业神就更多了。
[1] 《明史》载彭程任御史,上奏见光禄寺造皇坛器,以为皇坛已废,徒费民脂,结果招罪。《明史》卷一百八十,《列传第六十八·彭程传》,中华书局,北京,1974年,第4793页。
[2] [明]刘若愚著,《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8页。
[3] [明]刘若愚著,《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2页。
[4] “二十一年夏四月庚申,大高玄殿成。”《明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世宗纪一》,此殿当是宫婢之乱后马上着手建设。中华书局,北京,1974年,第231页。
[5] 明世宗常命大臣献青词,夏言后期表示出了一定的抵触情绪,因而失势,严嵩善青词,以此得宠,权倾一时。后徐阶揣摩此道,暗习扶乩,串通太监,遂取而代之。此又宗教与政治之关系一例也。
[6] 汤用彬、彭一卣、陈声聪编著,《旧都文物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51页。
[7] [明] 刘若愚著,《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9页。
[8] 汤用彬、彭一卣、陈声聪编著,《旧都文物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51页。
[9] “北上西门之西,大高玄殿也。其前门曰始清道境。左右有牌坊二:曰先天明境,太极仙林;曰孔绥皇祚,宏佑天民。又有二阁,左曰阳明阁,右曰阴灵轩。内曰福静门,曰康生门,曰高元门,苍精门,黄华门。殿之东北曰无上阁,其下曰龙章凤篆,曰始阳斋,曰象一宫”。语焉不详,但有门名,而无殿名,二阁可能就是钟鼓楼,牌坊一直保留着,其上题字也没有改变。——引文引自《酌中志》,第139页。
[10] 汤用彬、彭一卣、陈声聪编著,《旧都文物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01页。词中少女即为世宗从民间征集,以其经血提炼丹药,红铅之类就是用此为原料,药的效力无非还是壮阳。
[11] [清]高士奇著,《金鳌退食笔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7页。
[12] [明]沈德符 撰,《万历野获编》上,卷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41页。
[13] [清]高士奇 著,《金鳌退食笔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7页。
[14] [清]高士奇 著,《金鳌退食笔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8页。
[15] [清]高士奇 著,《金鳌退食笔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3页。
[16] [明]刘若愚 著,《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8页。
[17] 玉芝宫之得名也颇为荒诞,明世宗好祥瑞,太监们投其所好,嘉靖四十四年六月,称献皇帝旧庙前殿的柱子上长出了一棵白色灵芝,世宗自然大喜,将灵芝奉献至太庙,群臣附和,纷纷上表祝贺,遂改其名,并定祀典。显然这是一场太监们人为造作的闹剧,明世宗之昏庸亦可见一斑。穆宗即位之后罢废了其中的某些仪式。详情参见[明]沈德符 撰,《万历野获编》上,卷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47页。
[18] [明] 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上,卷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41页。
[19] [清]高士奇著,《金鳌退食笔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24页。明世宗谕尚书李时等曰:“西苑宫室,是朕文祖所御,近修葺告成,欲于殿中设皇祖之位告祭之。”
[20] “嘉靖癸卯夏四月,新作雩殿成,其地汇以金海,带以琼山,规构宏伟,地位肃严。前为雩祷之殿,后为太素殿,以奉祖宗列圣神御。斋馆列峙,临海为亭……”语出《钤山堂集》,转引自《日下旧闻考》第一册,卷三十六,第571页。
[21] “帝社稷坛在西苑,坛址高六寸,方广二丈五尺,甃细砖,实以净土。坛北树二坊,曰社街。”《明史》卷四十七,《志第二十三·礼志一》,第1229页。“隆庆元年,礼部言:‘帝社稷之名,自古所无,嫌于烦数,宜罢。’从之。”《明史》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五·礼志三》,中华书局,北京,1974年,第1268页。
[22] 详情见[清]高士奇著,《金鳌退食笔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9页。并《明典礼志》,摘于《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六,第562-563页。
[23] [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上,卷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41页。
[24] 参见[清]高士奇著,《金鳌退食笔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27页。
[25] 语出《明宫殿额名》,转引自[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一册,卷三十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70页。
[26] 载于《明会典》,引自[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一册,卷三十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70页。
[27] [明]刘若愚著,《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7页。
[28] 本段多处引文均出自[明]沈榜编著的《宛署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5页。
[29] 道教之中也有女丹这一类的功法,由女道士所创,从其修炼内容看还是要走向纯阳,并且这也只为少数人所知晓,远不如男性所习功法所具有的普遍的影响力。
[30] 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建奉先殿”。《明史》卷二,《本纪第二·太祖纪二》,第25页。又奉先殿的设立其建议来自陶凯,见《明史》卷一百三十六,《列传第二十四·陶凯传》,中华书局,北京,1974年,第3934页。
[31] 关于奉先殿在《日下旧闻考》中引用《春明梦余录》的一段文字,称“永乐三十五年始作”。许以林一文已作辨析,永乐没有三十五年,奉先殿成于永乐朝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其建设应该同宫城主体同时进行。《明史·礼乐志》有载明太祖有关言论,此处引自[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一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01页。
[32] 转引自许以林 著,《奉先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1期,紫禁城出版社
[33] “孝苏纪皇后薨,礼不得祔庙,乃于奉先殿右特建奉慈殿别祀之。嘉靖十五年,并祭于奉先殿,罢奉慈享荐。”语出《春明梦余录》,转引自[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一册,卷三十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02页。
[34] 参见[清]于敏中等 编纂,《日下旧闻考》第一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28页。
[35] 前句见《明史》卷五十二,《志第二十八·礼志六》,第1337页,中华书局,北京,1974年。后句见《明世宗实录》,转引自[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一册,卷三十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03页。
[36] 万历三年俱“迁祔奉先殿,二殿(弘孝、神霄)俱罢”。见《明史》卷五十二,《志第二十八·礼志六·奉慈殿条》,中华书局,北京,1974年,第1336页。
[37] 见许以林《奉先殿》《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
[38] 见《明宪宗实录》,转引自[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一册,卷三十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47页。
[39]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一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30页。
[40]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一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35页。
[41] 载《光禄寺志》,同上书,第537页。
[42] 《明史》卷五十,《志第二十六·礼志四·三皇条》,第1295页,嘉靖年间建三皇庙于太医院,“复建圣济殿于内,祀先医,以太医官主之。”又《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职官之三·太医院条》,载“嘉靖十五年改御药房为圣济殿”。中华书局,北京,1974年,第1813页。
[43] [明]刘若愚 著,《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1页。
[44] 传说真武为净乐王太子,修炼武当山,功成飞升,奉上帝命,镇守北方。朱棣之事可参见《明史》卷五十,《志第二十六·礼志四·诸神祠条》,中华书局,北京,1974年,第1308页。
[45] [明]刘若愚 著,《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第147页。
[46] 转引自[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16页。
[47] 如果钦安殿东西有七所的话,整个这一区域的变化较大,本人目前尚无法提出可信的布局形式,但做了一个尝试,如果是保留现在五所的位置不变,向内增加两所,则钦安殿两侧几无空间余地,连交通都紧张。考虑到五所东西两尽头还有不明用途的余裕,则自顶头的位置向内建七所,空间尺度在钦安殿这一局部尚称合理,但配套的环境有极大变化,本人没有把握想象其格局,仅能提出一个草图,表达这个构想,以供方家参考。详情参见附图。
[48] [明]刘若愚著,《明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页。
[49] [明]刘若愚著,《明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页。
[50] 从养心殿周围建筑的命名情况看,在明代也像是一处道教修炼的场所,参见本文清代养心殿部分的论述,因此本文判断养心殿也当是同时期建设。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在介绍养心殿时称其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同本人观点正相吻合,但并未说明来源,仅此说明。其网址为www.dpm.org.cn。撰稿人为周苏琴。
[51] [明]刘若愚著,《酌中志》卷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0页。
[52] 参见杨文概著,《北京故宫乾清宫东西五所原为七所辨证》,单士元、于倬云主编,《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第137页。
[53]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09页。
[54] [明]刘若愚著,《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