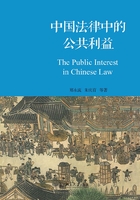
五、对设置众多公共利益条款的解释和评论
通过上面从用法到目的的多方描述,尽管在中国现行公法法律中找不到一个关于公共利益的“描述性定义”,且公共利益是一个含义随时空而变的概念,但人们大体能看出公共利益的轮廓,下述解释和评论,也许会有助于进一步形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
1.公共利益与公平、共和
公平是一种价值,共和是一种治理模式,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民共和国,这使得中国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尤为紧密。首先,公共利益关涉的是每个人的利益,在要求单个人或少数人、单位或集团牺牲其自身利益以满足公众利益需求时,就不免会发生权利冲突。公共利益本身不是价值,但关系着公平的价值,因为公共利益的实现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达致平衡,公平也就实现了。这从公平的含义便可看出:第一,公平是一个关系概念。它不是就单个人而言的,而是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在一个社会内部,是就其所有成员而言的。第二,公平具有分配性质。如果在公平上发生问题,总是由在人与人之间分配什么东西(如财富、权利、机会等)引起的,公平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适度调节分配。第三,公平所涉及的内容是社会资源,其中主要是社会角色及其权利和义务。第四,公平是一种价值要求,要求分配公平、合理,其一般尺度就是使相关人员得其应得,或者说大家各得其所,这是公平的根本要求。
社会主义国家在本性上是要克服自由竞争带来的社会不公,所以尤为强调公平的基本价值,这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为何在法律中设置众多公共利益条款的原因。目前在中国,社会不公的问题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风险,人们试图通过在收入、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发展起点和机会上的公共行动来对不平等进行干预,满足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公正。
其次,中国又是一个人民共和国,而公共利益与共和是联系在一起的。“共和”就其本意来讲,就在于把政治权力塑造成一种能为共同体中所有人共享的、保障各阶层利益的公共架构,共和的目的指向公共事务或公共利益。“共和国”就是一个促进公共利益、共同财富和共同事业的国家。古典共和主义核心原则之一是公共优先。所谓“公共优先”,是指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行使公权力的公民要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少数当权者的利益服务;一般公民也应当将公共利益或公共善(public good)置于私利之上。
2.公共利益条款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依共和主义,公共领域比私人领域更重要。设置公共利益条款的目的之一是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因而,中国在法律中设置了众多公共利益条款。由于公共利益是不同于个人利益的法益,当这两种不同法益发生冲突与抵触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就表现为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对基本权利加以限制。公共利益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就是从外部对基本权利的限制,这就是所谓“外在限制说”。与此相连的是“公益优位论”,中国《宪法》中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第51条也相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的、集体的利益……”,从这一表述来看,我们可以得出:(1)公共利益是外在于个人利益,(2)公共利益可以限制个人利益。
这当然是公共利益存在的理由,但也要警惕这样的理解:只要公权力“依法”而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如私有财产权在法律上被根本否定就是可以的。“外在限制说”及“公益优先论”可能导致的危险是:把公共利益条款作为国家权力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之利器。因此,在根本上,在重视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和相对优先性之时,要比较衡量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得失,尤不可任意限制个人利益,对限制个人利益也要加以限制,这就是限制之限制,使两者在协调中发展。
3.公共利益条款的抽象与具体化
公共利益条款容易抽象而难以具体化,但不可一概而论。法律中设置公共利益的目的有多个,对不同规范目的的公共利益,可予以不同程度的具体的明确规定。但是在立法层次和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有所不同。这取决于立法机关对公共利益的认知,对于法律规范目的的判断,以及现有的立法条件是否成熟。
对于作为立法宗旨的公共利益,法律文本的表达结构可以抽象一些,因为立法宗旨只是整个法律的纲领,其实现一般还需要依靠具体的法律规范。与作为立法宗旨的公共利益不同,对于作为公权力行使依据,行为的前提和合法性的标准,尤其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的标准的公共利益,应当使之具体化。不然,会导致公权力机关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会导致对基本权利的过度限制,甚至只剩下限制,而没有权利。之于前者,《行政许可法》是一例,它规定,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变更或撤回;同时又规定,依法应予撤销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又可以不予撤销。这就给了行政机关极大的空间,要求行政机关在适用法律的时候作出具体判断,从而使行政机关在公共利益的确定上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如何具体化,首先,是在宪法还是在法律、行政法规层面上具体化?对公共利益条款的具体规定主要不应由宪法来完成,这有可能造成一些基本权利自开始就被限制。尽管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制度的活动”,这是“公共利益”一定程度的具体化。[1]公共利益的具体化主要应由法律完成的,它是“法律保留”的事项,即必须是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并颁布的法律,否则缺少评价公共利益的形式条件,这样的安排还易于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因此,2011年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虽可被视作一个较好的具体化范例,但全国人大对“公共利益”没有作出规定,那么,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务院是否就有权作出规定呢?这是可质疑的,因为《立法法》第八条第六款明确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必须通过立法。对于暂时尚未立法的,则须经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才能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而该条例未经全国人大授权。
其次,具体化采用的立法模式应是示例加排除的方式:示例规定是先列出若干,以“等”为结尾,这是一种较为可取的表述方式。2011年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可被视作一个较好的范例。然后,再设立一个排除条款,明确排除那些不属于“公共利益”范围的事项,如企业从事商业性开发,政府兴建高尔夫球场等。再次,还应尽可能明确侵害示例规定的具体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构成要件。最后是通过宪法解释、法律解释,形成判例,尤其是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引发的行政征收和行政征用之判例,不断细化公共利益的内容。
4.公共利益条款的实体化与程序化
与具体化相连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大部分法律中,公共利益条款表现出概括性实体化倾向, 这体现在在前文所述的公共利益被具体地列举为六类20余种直接用途,但作为法律概念,即使公共利益的规定是概括性的,语义含糊的,政府仍要予以遵守和执行,这就需要通过行政程序来界定公共利益在具体个案中的含义。然而,公共利益条款程序化方面的中央法律只是少许,如《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但有的地方立法做得比较好,可资为中央立法借鉴,如目前上海的8部城市规划法律文件(包括3部地方性法规、4部地方政府规章和1部规范性文件)对一些程序性制度作了较为合理的规定,据有关资料梳理和归纳如下。[2]

[1] 另如德国《基本法》第11条第2款规定:迁徙自由在下列情况下予以限制:无充裕的生活基础和给社会增加特殊的负担;为保护青年不受遗弃;同流行性疾病作斗争和防止犯罪活动。
[2] 课题组:《行政规划理论与实践若干问题研究》,载《政府法制研究》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