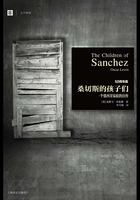
第3章 导言(1)
本书讲述了墨西哥城一个贫困家庭的故事。父亲赫苏斯·桑切斯五十岁,他的四个孩子分别是三十二岁的曼努埃尔、二十九岁的罗伯托、二十七岁的康素爱萝和二十五岁的玛塔。我的目的是向读者们呈现一个家庭内部的生活场景,在经历社会和经济巨变的拉美大城市中心区的贫民窟,住在一居室的出租屋里长大成人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
我在墨西哥的研究工作始于1943年,我曾经尝试过以多种方法开展家庭研究。在《五个家庭》一书中,我试图让读者窥见五个普通的墨西哥家庭在五个平凡日子里的日常生活。在本书中,我用新的方法让读者对其中的一个家庭进行更深层次的察看,每一个家庭成员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累加的、多面的、全景式的场景,每个个体是一个整体,整个家庭是一个整体,墨西哥下层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整体。同一件事会由不同的家庭成员描述成各自独立的版本,这提供了一种内在的查验机制,许多数据的可靠性和合法性得以确保,从而部分地剔除了个人自传中所存在的主观性。同时,每一个家庭成员回忆某些事情上的矛盾性也显露了出来。
这种多人自传体的方法也易于减少调查者的偏见,因为其中的描述没有经过我这个北美中产者的筛选,而是受访对象他们自己的描述。这样一来,我就避免了贫穷研究中两个最为常见的灾难:过于悲情、过于冷酷。所以,我希望这样的方法能同时带给读者们情感上的满足和理解。人类学家在直接和受访对象打交道时能够体会到这样的满足和理解,可在充斥了专业术语的人类学专著中却很少传达出来。
无论是针对欠发达国家的贫穷状态,还是我国[1]的贫穷状态,都很少有深度的心理方面的研究。本书中所描绘的底层穷人,尽管绝不是最底层的穷人,但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病学家都未对其进行过密切的观察研究。也没有哪个小说家对当代穷人的内心生活状态进行过足够的展现。从贫民区走出的大作家本就不多,等他们稍具名气时,常常会透过中产阶级人士的视野回顾自己的早年生活,并在传统文学的框架内进行创作,早年经历的即时性早已在这样的回顾性作品中荡然无存。
用来记录本书各日常生活往事的录音机使得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这种新的开端变成了现实。有了录音机这个帮手,不会说话的人、读书不多的人,甚至文盲都能够无拘无束地、自然而然地、不加做作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把自己的观察和经历串联起来。曼努埃尔、罗伯托、康素爱萝、玛塔等人的故事充满了朴素、真诚和直白,相较于书面文字,这都是口头叙述和口述文学的特征。尽管这些年轻人从没受过正式的训练,他们却能够出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尤其是康素爱萝有时候的讲述水平甚至达到了诗一般的高度。尽管身陷种种未决的烦恼和困惑,他们能够充分地言说出来,从而让我们瞥见他们的生活状态,也让我们意识到他们所具有的潜能和被埋没的才华。
诚然,穷人的生活一点都不乏味。本书的一个个故事所展现的世界充满了暴力和死亡、苦难与遗弃、夫妻不忠、家庭破裂、少年犯罪、贪污腐败、警察专横,甚至穷人对穷人的残忍相向。这些故事也展示了深深的感情和人性的温暖,强烈地表现了个性张扬、寻求欢欲,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充满着对于被理解和关爱的期待,乐于和他人分享他们本就不多的东西,以及在种种未决的烦恼面前敢于坚持的勇气。
这些故事的发生地卡萨—格兰德居民区,位于墨西哥城的中心地带,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一层楼贫民租户区。1951年,我前去考察阿兹特克村的农民们向墨西哥城迁移这一农民城市化问题,卡萨—格兰德居民区便是我所考察的几百个居民区之一。我关于阿兹特克的考察始于数年之前的1943年。其后,在村民们的帮助下,我在墨西哥城内找到了几处阿兹特克人的定居点,其中两家正好位于卡萨—格兰德。在做完村民迁徙的研究工作之后,我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设计,开始着手研究起整个居民区,其中涵盖了所有的居民,而不考虑他们来自什么地方。
1956年10月,在研究卡萨—格兰德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赫苏斯·桑切斯和他的孩子们。赫苏斯这个租户在那里已经居住了二十多年,期间,他的孩子们在这里进进出出,但位于卡萨—格兰德的这套一居室房子一直是他们生活中一个比较稳定的据点。赫苏斯的首任妻子和孩子们的母亲伦诺死于1936年,几年后,他们搬进了卡萨—格兰德。伦诺的大姐瓜达卢佩六十岁,所居住的帕纳德罗斯居民区位于几个街区之外的贝克大街。瓜达卢佩姨妈差不多成了孩子们的母亲,他们也会时常前去看望她,在需要的时候甚至把她的家当成避难所。因此,日常生活的发生就在卡萨—格兰德和帕纳德罗斯居民区之间来回交替。
这两个居民区都靠近城市的中心区,步行只需十分钟即可抵达主广场,以及矗立着大天主教堂和总统府的宪法广场。只需走上半小时,就可以到达供奉墨西哥的守护神圣女瓜达卢佩的国家神庙,各地的朝觐者络绎不绝地来此朝拜。卡萨—格兰德和帕纳德罗斯居民区所在的特皮托区是一个贫民区,区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小工厂、小货栈、公共浴室、破败不堪的三等电影院、人满为患的小学校、酒吧、龙舌兰小酒馆(专售当地特产龙舌兰酒),以及琳琅满目的小商店。墨西哥城有名的二手货市场特皮托——也被人叫做小偷市场,就隔着几个街区。其他的大型市场,如最近刚刚被改装得具有现代气息的默塞德和拉古尼拉市场也可轻松地步行到达。这一地区频频发生命案、酗酒和少年犯罪。其人口十分密集,无论白天或是深夜,大街上、门廊里、商场入口处总是挤满了熙来攘往的人群。妇女们在背街小巷支起厨具,售卖玉米面豆卷或是汤羹。大街小巷都很宽敞,也铺了地砖,但看不见几棵树木和小草,也看不见花园的影子。人们大都居住在封闭庭院里的一居室,隔着大街的要么是一排排商店,要么是一道长长的围墙。
卡萨—格兰德夹在理发店街和铁匠铺街之间,覆盖了整个四方形的街区,居住着七百多人。卡萨—格兰德自成一体,南北两边围绕着高高的水泥挡墙,东西两头是鳞次栉比的小商店。这其中有小食店、干洗店、玻璃店、木匠铺、美发厅,它们跟居民区的市场、公共浴室一起,为整个小区提供最基础的各种需求。因此,很多租户从未远离过自己的居民区,对墨西哥城的其他地方几乎一无所知。这一地区原来是黑社会的天下,即便到了今天,人们在深夜出门还有些害怕。不过,犯罪因素多已不复存在,居住的居民主要是贫穷的商贩、手艺人和苦力汉。
居民区东西两头那两个狭小的入口并不惹人注目,装着高高的大门,白天一直敞开着,夜间十点就有人上了锁。只要过了时间点,任何人进出都需要摁门铃招呼看门人,给了钱,他才会开门放行。这个居民区有自己的守护神:圣女瓜达卢佩和圣女扎婆潘,她们的塑像摆放在玻璃箱内,各镇守一个出入口。塑像四周满是供奉的花朵和蜡烛,裙边上拴着小小的亮牌,每一个亮牌都在昭示着她们在居民区内的某一个居民身上所发生的神迹。走过这两尊圣女塑像时,很少有哪个居民不关注一下,或是匆匆一瞥,或是边走边画个十字。
居民区里面有四个狭长的天井,或者说是庭院吧,铺着混凝土,大约十五英尺宽。朝向天井的是一百五十七间没有窗户的一居室房子,彼此间隔十二英尺,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漆成了黄色。大白天,在一扇扇大门边上,斜靠着一架架粗糙的木楼梯,直通厨房正对的屋顶。厨房正对的屋顶用处多多,密密麻麻地满是晾衣绳、鸡笼子或者鸽子窝、栽种着花草或药材的盆盆罐罐、用来煮饭的燃气罐,偶尔也能看见电视天线。
白天,天井里挤满了人、牲畜、狗、火鸡、小鸡、猪仔等。孩子们也会在这里玩耍,因为这里比大街上安全。妇女们排队等着取水,或是一边晾晒衣物一边高声交谈,街头小贩也会走进来不停地叫卖货物。每天清晨,总有一位清洁工推着一辆大大的推车穿行在天井里,收走每家每户的垃圾和废物。到了下午,一群群年龄稍大的孩子总会占据着某一个天井,疯狂地玩起足球来。星期天的晚上,一般会有露天舞会。靠近西边入口的地方有一个公共浴室,那里有一个小花园,稀稀拉拉的大树和草丛成了年轻人会面的地点,因为相对比较安静,老年人也会坐在这里,跟人说说话,或者看看报。这里还有一间独房子,上面标着“管理处”的字样,边上的告示牌列着一家家租金拖欠户的姓名。
卡萨—格兰德的租户来自全墨西哥三十二个州中的二十四个。有些来自南边的瓦哈卡州和尤卡坦州,有些来自北边的奇瓦瓦州和锡那罗亚州。大多数家庭在此居住了十五至二十年,有些已经长达三十多年。居民区内,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具有血缘关系,大约四分之一的家庭具有姻亲关系或者干亲关系(即父母、教父母关系、教子女关系等)。这样的关系纽带,跟固定而且低廉的租金和全城房屋供不应求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稳定状态。有的家庭收入较高,小房子里摆不下高档的家具和电器,会等着有机会搬到更好一点的地方居住,但绝大多数居民对于居住在卡萨—格兰德感到心满意足,甚至有些洋洋自得。
居民区内的社区意识极强,尤其是同属一伙的年轻人结成终身的友谊,一同上学,一同参加天井坝里的舞会,而且常常会在居民区内完成嫁娶。成年人也遍交朋友,一同出行,互借有无。挨邻的几家人会组织抽奖和轮流集资活动,一同参加宗教朝觐,一同庆祝居民区守护神的节日、圣诞节,以及其他活动。
不过,这样的集体活动只是偶尔为之,因为成年人大多数“只管自己的咸菜稀饭”,并竭力守护家庭隐私。多数大门总是关得严严实实,如需上门拜访,先要敲门,等着允许入内是基本的习惯。有的人只会拜访亲戚朋友,很少进别家的大门。除了正式的日子,如生日或者宗教节日,人们很少邀请亲戚或者邻居来家里吃饭。尽管有邻里互帮的现象,在遇到危难时尤其如此,但这样的情形少之又少。在卡萨—格兰德,家庭间因为孩子的顽皮而吵嘴、不同帮派间的街头争霸、男孩之间的世代结仇也并不罕见。
卡萨—格兰德的人们谋生的手段可算是大杂烩,有些人不出居民区也能养家糊口。妇女可以从事洗衣和缝纫,男人可以制帽、擦鞋,甚或摆个水果糖果摊。也有人出外去工厂做工,看守店铺、当司机,或者做小买卖。生活水平固然低,但绝不是全墨西哥城最低的,周围的人甚至高看卡萨—格兰德,觉得那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地方。
就贫穷文化而言,卡萨—格兰德和帕纳德罗斯两个居民区可以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帕纳德罗斯居民区很小,只有十二间未开窗户的一居室房屋连成一排,没有围墙,没有大门,只有一个脏兮兮的小园子,过路人一眼就能看个对穿。不像卡萨—格兰德,这里没有室内卫生间,也没有自来水。能够为八十六个居民所使用的,是只有几片破麻布遮挡的两个公共盥洗间和用破砖砌成的两个公共卫生间。
如果有人从帕纳德罗斯居民区搬进卡萨—格兰德居住,他会发现这里的人均床位数多,睡地板的人少,用燃气烹饪的家庭多过用煤油或木炭烹饪的家庭,一天吃三顿的人多;除了玉米饼和汤匙,用刀叉吃饭的人多;人们喝的是啤酒而不是龙舌兰酒;人们买的是新家具、新衣服,而不是二手货;人们为了庆祝万圣节是去教堂做弥撒,而不是像传统做法那样在家里摆上香烛、酒馔。总体的变化趋势是从土坯房到混凝土房、从陶罐到铝壶、从草药到抗生素、从本地求医到医院问诊。
1956年,卡萨—格兰德79%的租户用上了收音机,55%用上了燃气炉,54%用上了手表,49%用上了刀叉,46%用上了缝纫机,41%用上了铝壶,22%用上了电搅拌机,21%用上了电视机。在帕纳德罗斯居民区,这样的奢侈品还难觅踪影。只有一家人用上了电视机,两家人用上了手表。
卡萨—格兰德的人均月收入在二十三比索至五百比索之间(照目前的汇率,也就是三美元至四十美元之间)。人均月收入等于或低于两百比索(十六美元)的占68%,两百零一比索至三百比索(二十四美元)的占22%,在三百零一比索至五百比索的占10%。而在帕纳德罗斯居民区,超过85%的家庭月均收入不足二百比索或十六美元,超过二百比索的一家也没有,不足一百比索的占到了41%。
在卡萨—格兰德,一居室公寓房的月租金在三十至五十比索之间(二点四美元至四美元),在帕纳德罗斯是十五至三十比索(一点二至二点四美元)。许多家庭都由一对夫妻和四个小孩子构成,每一天的食物只能靠八至十比索(六十四至八十美分)勉强维持。他们的食谱上有清咖啡、玉米饼、豆子和辣椒。
卡萨—格兰德居民的教育水平各不相同,十二个成年人从未踏进过学堂大门,一位妇女读了十一年书。接受学校教育的平均年限是四点七年,文盲比例仅为8%,20%的婚姻通过自由恋爱结成。
在帕纳德罗斯居民区,人们的在学时间仅有二点一年,初中毕业生一个也没有,文盲比例为40%,46%的婚姻通过自由恋爱结成。在卡萨—格兰德,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庭具有血缘关系,四分之一的家庭具有姻亲或干亲关系。而在帕纳德罗斯,一半的家庭具有血缘关系,几乎所有家庭之间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干亲关系。
在选作卡萨—格兰德研究对象的七十一个家庭中,桑切斯的家庭只是随机选择的样本之一。在整个居民区,赫苏斯·桑切斯属于中等收入人群。作为餐馆的食品采购员,他的日工资水平约为十二点五比索,相当于一美元。如果仅靠这点钱,他连自己都养不活,因此他通过卖彩票、养猪、养鸽、养鸡、养鸟,甚至在各大市场获取所谓的“佣金”来贴补家用。对于这些额外的收入来源,赫苏斯守口如瓶。不过,他靠这些钱要勉力支撑分散在这个城市中的三个家庭,因此生活水平非常一般。我做调查期间,他和他年轻的宠妻德利拉一起住在丢孩大街上的一间房子里。他要供养这位妻子以及和这位妻子共同生养的两个孩子、她和前夫共同的儿子、她的母亲,以及他自己的儿子曼努埃尔的四个孩子。赫苏斯年龄稍大的妻子卢裴塔和他们的两个女儿、两个外孙居住在城郊埃尔多拉多居民点的一所小房子里,房子是他自建的,这一家人的开支也由他提供。赫苏斯在卡萨—格兰德的房子留给他的两个女儿康素爱萝、玛塔和她的孩子们,以及他的儿子罗伯托一起居住。
除了一台旧收音机,桑切斯位于卡萨—格兰德的家里就没有别的奢侈物件了。不过,这家人的吃喝没有问题,而且孩子们受教育的程度都比邻家要好。赫苏斯本人只上过一年学,但他的大儿子曼努埃尔一直读完了小学六年级。康素爱萝也小学毕业,甚至还读了两年商贸学校。罗伯托读到三年级就辍学了,玛塔也只读完了四年级。
跟众多的邻居不同,桑切斯家请了一个用人,白天来家里做做清洁、洗洗衣服,还负责一家人的饭菜。这是赫苏斯第一任妻子伦诺去世后的事情,因为留下的几个孩子都还太小。用人要么是邻居,要么是亲戚,有时也可能是一个寡妇或是被丈夫抛弃的女子,为了一小点收入便可以从事这样的活计。尽管请用人这事让一家人觉得脸上有光,但这算不上什么有钱的标志,在居民区也不是稀罕事。
介绍我认识桑切斯一家的是我在这个居民区早就认识的一个朋友。第一次登门拜访的时候,我发现他家的门半开着。就在等着有人开门的过程中,我发现屋子里十分阴沉破败。用作厨房和卫生间的门廊显得十分促狭,早就到了该好好粉刷一下的地步,全部的家什也只有一架两眼煤油炉、一张餐桌和两把未经粉刷的椅子。不只是厨房,还有里间稍大一点的卧室,都丝毫没有我在卡萨—格兰德的其他有钱人家里所看到的那种不太张扬的富足。
替我开门的是康素爱萝。她外形单薄,脸色苍白,一个劲地解释说她刚大病初愈。她的妹妹玛塔跟在她的身后,怀抱一个用披肩包住的婴儿,一句话也没说。我跟他们做了介绍,说我是来自美国的教授和人类学家,在墨西哥的小村子里做民俗研究已经好几个年头了。我正在对城市居民区的生活和村里人的生活进行比较研究,因此正在卡萨—格兰德寻找愿意协助我做研究的人。
为了打开话题,我问他们觉得乡下人和城里人谁更富裕一些。我在之前的采访工作中常常以此开启话题,因此,问了几个类似的问题之后,我就直奔调查问卷中的一些问题了。这些问题涉及他们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出生地、受教育情况、职业和就业史等。
就在我快要问完这些问题的时候,这家人的父亲赫苏斯·桑切斯肩挎一袋食物急匆匆地走了进来。赫苏斯个头不高,身板结实,一副印第安人的身材,穿着蓝布工装裤,头戴一顶草帽,既像农民,又像工人。他把袋子交给玛塔,跟玛塔和康素爱萝简单地寒暄了两句,然后疑惑地转头问我在干什么。他简要地回答了我的提问,说乡下人的生活比城里人的生活好得多,因为城里的年轻人很容易学坏,他们尤其不懂得该怎样利用城市里应有的各种东西。说完这些,他又急匆匆地出门走了,一如他急匆匆地夺门而入。
我到桑切斯家做第二次采访的时候遇到了这家人的二儿子罗伯托。他的个子稍高一些,皮肤也比其他人更黝黑一些,那架势颇像训练有素的运动员。他是个乐呵呵的人,说起话来轻言细语,给我的印象是谦逊有加,彬彬有礼。他一直对我以礼相待,哪怕喝得醉醺醺的时候也是如此。我遇到这家人的大儿子曼努埃尔是在几个月之后,因为那段时间他刚好出国了。
在其后的数个星期乃至数月时间里,我继续在这个居民区的其他样本家庭里做着研究工作。经过四次采访,我完成了针对桑切斯一家人的数据收集工作。不过,我还是经常造访桑切斯一家,跟康素爱萝、玛塔或者罗伯托闲聊一番,他们全都十分友善,为我了解居民区的生活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就在我对这个家庭每一个成员的了解有所加深的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单这一个家庭似乎就足以印证墨西哥下层社会中所存在的很多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至此,我决定进行一次深入的研究。先是康素爱萝,接着是罗伯托和玛塔都同意跟我讲述他们各自的成长经历。在他们知情和同意的前提下,讲述用录音机录了下来。曼努埃尔回来之后,他也很合作。在我对孩子们的研究持续了六个月之后,赫苏斯也同意了。要获得他的信任很不容易,可他一旦决定让我用录音机记录他的生活经历,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我和他的孩子之间的友谊。
在独立讲述各自生活经历的过程中,需要考虑隐私性,因此大多数讲述和录制都在我的办公室和家里完成。绝大部分都独立录制,但我在1957年、1958年和1959年回访墨西哥的时候,设法让二至三个家庭成员同时做了几次小组讨论。偶尔,我也在卡萨—格兰德他们的家里录过音,但他们在居民区以外的地方讲述起来更加游刃有余。我还发现,如果把录音机放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系在衣服上——也很有用,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当它不存在一般进行自己的讲述。
注释:
[1]此处指美国。——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