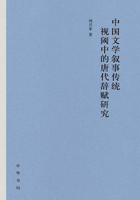
第一节 注重对事物的铺陈叙写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赋在体制上的突出特征就是铺陈,即对事物进行穷形尽相地铺张描绘和详细叙述,辞藻华丽绮靡,内容广博宏富。诸多文论家(包括赋论家)都申明过赋的铺陈叙写的特点,略举例如下:
《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曰:“教六诗: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郑玄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1]
刘熙《释名》卷六《释典艺》曰:“敷布其义,谓之赋。”[2]
挚虞《文章流别论》曰:“赋者,敷陈之称……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3]
陆机《文赋》曰:“赋体物而浏亮。”李善注曰:“赋以陈事,故曰体物。”[4]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5]
钟嵘《诗品》曰:“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6]
孔颖达疏《诗大序》曰:“赋者,直陈其事,无所避讳,故得失俱言……郑以赋之言铺也,铺陈善恶,则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7]
王昌龄《诗中密旨·诗有六义》曰:“赋者,布也。象事布文,错杂万物,以成其象,以写其情。”[8]
贾岛《二南密旨·论六义》曰:“赋者,敷也,布也。指事而陈,显善恶之殊态。外则敷本题之正体,内则布讽诵之玄情。”[9]
朱熹集注《诗集传》曰:“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10]
王芑孙《读赋卮言》云:“赋者,铺也,抑云富也。裘一腋其弗温,钟万石而可撞,盖以不歌而颂,中无隐约之思;敷奏以言,外接汪洋之思……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其旨不尚玄微,其体匪宜空衍。”[11]
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赋取穷物之变。如山川草木,虽各具本等意态,而随时异观,则存乎阴阳、晦明、风雨也。”[12]
上述诸家都注意到赋作为一种铺叙手段,具有指事而陈、象事布文、以形象或意象表达讽诵情感的特征,其实质属于叙事艺术范畴。从音韵学的角度看,赋与“敷”“铺”“布”等字声同而义近,它不假比兴、非常直白地对所述对象进行敷陈铺排,全方位地描摹其声貌,大大提高了叙事艺术的表现力。
虽然汉赋颇遭后人堆砌辞藻、泛滥铺张的诟病,但却大大推动了空间立体叙事艺术的发展。清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13]就注意到赋擅长对杂沓多端的情事进行绘形绘影、无所不包的铺写。他进一步阐述道:“赋兼叙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14]左右横列之法,是一种共时叙事法,赋家在空间上推而广之,动则东南西北、前后左右、远近高低、上下内外,有时甚至于进入一个杳渺无垠的世界,由此展现出一个个辽阔的空间格局,而天上人间的纷纭事物悉数摄入赋家的笔端,从而呈露出一个个壮丽宏伟的场景。先后竖叙之法,是一种历时叙事法,它按照时间序列,既具体展开情事发展的全过程,又详尽铺写过程中的每一个层面与环节,有时甚至虚拟场景,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终至一个无以复加的宏伟之境。刘熙载从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肯定了赋对杂沓多端的情事进行铺排叙述的贡献。后来,朱光潜先生在论述诗之所以流于赋的问题时,称引了刘氏上述话语,并进而指出:“赋大半描写事物,事物繁复多端,所以描写起来要铺张,才能曲尽情态。”[15]
据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曾对友人问作赋心得说过这样一段话:“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16]集中反映了赋取材广阔、铺陈有序、叙事有条不紊的典型特点。关于这一点,他人也多有所论及。皇甫谧《三都赋序》云:“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以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17]晋成公绥《天地赋序》说:“赋者,贵能分理赋物,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18]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曰:“作赋之法,已尽长卿数语,大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19]清刘熙载《艺概·赋概》云:“赋家之心,其小无内,其大无垠,故能随其所值,赋像班形。”[20]我们不难发觉赋家以驰骋上下古今的强大想象力、容纳宇宙历史的宏阔心胸、绚丽华艳的文辞及无所不施的笔触来叙写天地间一切事物,传达出赋家内心追求巨丽、大美的审美理想。万事万物都被刻意搜罗,形诸墨楮,由此赋作文本呈现出汪博宏富、夸饰赡丽之美:“《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 博富也。”[21]“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词夸;取风云山川之形态,使其词媚;取鸟兽草木之名物,使其词赡;取金壁彩缯之容色,使其词藻;取宫室城阙之制度,使其词庄”,恰如一种“冠冕佩玉之步骤”[22]。正是赋家以纵横之笔总览众物,才使汉大赋呈现出包罗宏富、气势雄健的特征。一方面,赋家以包罗之心、宏富之辞对外部广阔世界进行铺张叙述与渲染;另一方面,赋家也对世间渺小卑微事物乃至抽象事物,如人的心灵世界进行细腻摹写,从而造成赋体本身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兼具的双重特征,正如林联桂在《见星庐赋话》卷三中所说:“赋之有声有色,望之如火如荼,璀璨而万花齐开,叱咤则千人俱废,可谓力大于身,却复心细如发者。”[23]
博富也。”[21]“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词夸;取风云山川之形态,使其词媚;取鸟兽草木之名物,使其词赡;取金壁彩缯之容色,使其词藻;取宫室城阙之制度,使其词庄”,恰如一种“冠冕佩玉之步骤”[22]。正是赋家以纵横之笔总览众物,才使汉大赋呈现出包罗宏富、气势雄健的特征。一方面,赋家以包罗之心、宏富之辞对外部广阔世界进行铺张叙述与渲染;另一方面,赋家也对世间渺小卑微事物乃至抽象事物,如人的心灵世界进行细腻摹写,从而造成赋体本身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兼具的双重特征,正如林联桂在《见星庐赋话》卷三中所说:“赋之有声有色,望之如火如荼,璀璨而万花齐开,叱咤则千人俱废,可谓力大于身,却复心细如发者。”[23]
对于赋所具有的直陈铺叙的本质要素,当今学者也各有阐述,如刘朝谦曰:“铺,有展开和叙事的双重涵义:展开也是一种展示,而且在赋是一种夸耀式的展示;展开赋予大赋的是大赋文本空间化的特征,这种空间一般是在一个中心的基础上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铺开,或者是按一种植物学、矿物学的分类框架来展开;叙事则是指陈述性的写作,其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往往具有同一性,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张力,这样的叙事方式长于体物,且使大赋文体较之骚体赋主要具有的不是情灵之性,而是物性。”[24]万光治说:“故就实质而言,铺、敷、布、陈具有在时空两个方面把事物加以展开的意义。这些概念之被引入文学,指的即是不假比兴、直接表现事物的时空状态的艺术手法。赋既然可与敷相通假,又最早与语言表述方式发生关系,后人很自然地用它来概括文学中陈述性、叙事性和描绘性手法,并进一步用它来称谓以上述手法为主要特征的文体,这就是赋体命名的来源之一。”[25]两人都注重从时间叙事、空间展开两个层面来探讨赋之铺叙所含有之义,从而得出赋之陈述性、叙事性、描绘性等重要特征。程章灿在分析两晋赋的叙述结构的经营时说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话:“以横向的空间的顺序展开(结合时间的顺序)和以纵向的时间的顺序展开(结合空间的顺序),这两种极有凝聚力和涵括量的结构形式,在晋代赋家手里终于完善起来了。这是两晋赋史的一个贡献。赋凭借这两种结构形式,长期占据了长篇描写和长篇叙事的文学领域。这或许也是中国古代长篇描写诗和长篇叙事诗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认为赋就是长篇描写诗和长篇叙事诗也不无理由。”[26]从时、空展开铺陈的层面阐述赋何以为长篇描写诗与长篇叙事诗,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一书中,便将“赋”与“史书”标举为中国两大叙述性文学[27]。诚如祝尧所言:“赋有铺叙之义,则邻于文之叙事者。”[28]铺叙手法的运用,无疑大大增强了赋体的叙事功能。中国古代文人把汉字本身所具有的形美、音美、意美,非常娴熟地运用到赋的创作中,对外部客体世界作细腻描写与铺排式、罗列式叙述,这是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把握进一步提高的结果,标志着人们艺术思维与叙事能力的日趋成熟,同时这也正是辞赋在叙述描写方面对中国叙事文学做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