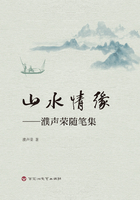
地质队里的那些事
我是1960年9月15日到达设计院报到。设计院没有房子,安排到东大街华西旅社,距设计院100来米,倒也不远。住的房间很小,一间房至少三四人,甚至五六人。
到院第三天,院人事科安排新分来的学生看戏。当时各地分来的学生有十多人。看戏的地点是端履门的五一剧院,演的是秦腔《三滴血》,下午一点半开场。我们十来人热热闹闹地进了场,但二三十分钟后,都陆续出来了。听不懂,但声音大,即所谓“秦腔不唱吼起来”。使劲吼,感觉无艺术性可言,大家都去逛了商店。对于秦腔还有一个糟蹋陕西人的段子,据说,周总理在此看完秦腔接见演出人员时,曾对他们说“要保护好嗓子”。应该说,秦腔的女旦唱得还是蛮好听的。
我们学地质的,很快就被分配到地质队。地质队当时在东仓门,住的是胡宗南公馆,它比张学良公馆小许多,只有十多间房。地质队在房前盖了几间平房,作为库房和灶房之用。外业人员回来就住华西旅社。
住华西旅社有时难以保证床位,你必须要早点去,把床位占住,去晚了没有床位则需自己想办法。1960年底,我与人干、盛金恰巧都从工地回队部汇报工作。吃了晚饭无事,决定去看个电影,看完后已11点多钟,待我们到达华西旅社留给地质队的大房间时,都住满了,已无空床可睡。与旅社交涉,已无其它空房,怎么办?电话打到队部办公室,答复自己解决。于是我们在东大街一带寻找旅社,奇怪的是,那天旅社几乎家家客满,没有空房了。这时人干提出,没有房就不住了,看电影去,我与盛金都同意。因为搞野外工作,与钻机住在一起,钻机出了事故,如卡钻、埋钻时,常同钻机工人一块去工地,打砣处理事故,晚上不睡觉是常事。
当我们去了解放路解放电影院和钟楼的钟楼电影院时,已是午夜已过,已不演电影了。这有点儿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原以为,西安是个大城市,娱乐活动应该通宵达旦,哪有过了12点就不演电影的道理。
走了一段时间,肚子也饿了,于是找东西吃去。来到一个小饭店,要了两笼包子,三碗馄饨,吃得很慢,吃完后,又坐了许久,聊天,聊工地情况和各自生活。饭馆已无人,不好意思再坐下去,就出得店来,往火车站方向走去。虽已是夜里两三点,但车站候车室的人还是不少,熙熙攘攘,喧闹异常。搭车人扶老携幼,托儿带女,背着大包,提着小包,寻找休息和落座的地方。有的坐在地上,有的靠在椅上,有的在地上铺几张报纸,拿行李当枕头,干脆躺在地上。这是一群平民百姓出行的状态,既坐不上卧铺,也住不起旅社,长途旅行只能这样煎熬,特别是老人小孩跟着受罪。
从候车室又转到售票处,人员还是不少。我们看了往南开的车次,计划回家的车次行程,今年春节不可能回家,只有在西安过了。
后来在西安过的第一个春节,也是蛮有意思的。过春节那几天,我们都回到了西安。大年初一,队部食堂给每人发了6两揉好的面,和一团掺有萝卜白菜的猪肉饺馅,自己包饺子,当然要交钱交粮票。到陕西后,在灶上吃过几顿饺子,但从未自己包过饺子。最后还是陕西同事帮忙,帮助包了,并帮助煮好,算过了一个年。南方人讲究是大年三十,一家围坐在一起“过年”,而陕西人讲究的是“大年初一吃饺子”,过年的气氛非常低落,队部食堂也没有专门炒几个菜,让异乡人在异乡温暖地过年。但队上给我们发了一张票,可以去街上饭馆买点好的吃。票有两种:一种是羊肉泡,一种是羊肉饺子。给我发的是白云章饺子馆的羊肉饺子票。
我与四川一位同事于初二中午去吃了羊肉饺子,排了很长时间队,半斤饺子,吃的时间很短,当然也没有吃饱。
那年过春节,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院里工会在市工会联系了一场篮球赛,地点在菊花园的青年俱乐部,在关中大旅社隔壁,有一个篮球场。春节期间,大部分人都不在,有的回家,有的探亲访友,队员凑不齐,院里只有宋大夫和祖志毅,队上有欧树元、高显一和我。我是半瓢水,高显一只会踢足球,不会打篮球,这样一个队伍,敢在西安的大场子出风头,的确是不简单的事,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火车站转完之后,我们沿解放路往回走,沿东大街往西走,一直走到西门,再往回走。到达鼓楼时,我们拐进了回民巷,这里还有灯火,卖吃食的不少。走了大半夜,人也困了,腿也乏了,走进一个小店坐下来,要了几样小吃,具体吃了什么,已记不起来,吃还能吃,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休息,店主没有催我们,我们坐了四五十分钟,天快亮了,我们起身往东走。
由此,我得到一个教训,照顾好自己,安排好自己的生活,离开家庭父母和学校同学师长,踏入社会后,没有人管你,关心你,只有靠自己,自生自灭。
我到队上报到两天后,即被安排去宝鸡太寅水库。这是离宝鸡约三十里秦岭山中的一个小型水库。但工作不到一星期,全体职工就被要求去乾县羊毛湾水库,全队集中学习,搞什么运动,要求自带行李铺盖。接通知后,即从宝鸡坐火车到武功车站。下车后,背上铺盖,步行70里,来到了羊毛湾水库,安排住在过去水库施工时民工住过的黄土窑洞里。我是第一次住窑洞,觉得很新鲜。地上铺的麦草,我没有垫的褥子,用队上发的一件棉大衣作垫,盖的是从老家带来的一床薄被,当时是十月中旬,天气还不怎么冷。
学习运动的内容是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搞运动的形式是组织学习文件,然后是讨论发言,揭发队上的三反内容。我被指定当会议记录。我们是刚来的学生,对单位情况一概不知,与队上同志是初次见面。因而,每天听念文件,听别人发言。我担任记录,却感到力不从心,主要是有些话听不懂,有些方言听懂了,却写不出来。例如,说某领导对工作不负责任,对事“怂管哇”,这“怂管哇”三个字写不出来,问旁边的人,也只会说,不会写。因而,一篇会议记录留下许多空白。为此,我也推辞过,但领导未应允。
运动搞了半月多就停下了。我背着铺盖回到了工地。
每年冬天,春节前夕,队上往往要搞运动。没运动就组织学习。开始都是学中央文件和上级文件,再后,也安排一点业务学习,主要给钻工讲课,有时也请人来队里做个业务报告。
1962年夏,地质队搬至黄雁村原陕西省水利厅工程局,地质队住东边一栋楼,工程局住西边一栋楼,后面几间平房作为钻探队的修配厂。文革前期,1966年夏,省水利厅安排设计院地质队去宝鸡,暂住原渭河工程局在宝鸡市五里庙盖的房子,计有一栋办公楼和十多排平房,近百间房子,地方宽敞多了。
但1969年宝鸡峡工程复工后,渭河工程局把房子要了回去,安排我们去暂住戴家湾一所工业技校的房子。
文革后,学校复办,宝鸡市政府要求我们迁出工业技校。经省水利厅安排,地质队被安排在咸阳市东郊一片河滩地,当时渭河河堤经省水电工程局已修整完善,工程局沿河堤占了300亩河滩地作为基地,而咸阳市在工程局对面划了50亩河滩作为地质队的基地。从此,地质队在此安营扎寨至今。
地质队于1952年在蓝田坝河成立,只有一台钻机,成为钻探队,只有钻工,而无地质人员。至1956年发展三台钻机,始称地质队,这时已有两三名地质人员。我们到来时,已有五六台钻机,上十名地质人员,院长当时称我们为“宝贝疙瘩”。
“不坐椅子蹲起来”,这是陕西十大怪之一。陕西农民特别是陕北关中农民,过去因为穷,生活清苦,一般家中家具很少,吃饭常蹲在窑洞门口,端一个老(大)碗吃糊汤或吃面条,很少像南方那样,即使再穷也是围桌而坐,一家人在一块吃饭。陕西人即使在单位机关食堂,也是爱蹲在食堂外面的地上吃饭。这倒不是单位狭小,而往往是习惯。1982年地质队由宝鸡搬至咸阳,院子有50亩面积,以后陆续盖了多座房屋,但管理不善。例如,盖的礼堂兼食堂却当做仓库,礼堂里,舞台上到处堆的是材料,而真正的材料库却没有好好放材料。好大的一个食堂,职工吃饭还是习惯蹲在地上吃。
我当队长后,首先叫供应科把放在礼堂、食堂里的材料搬出来,放到材料仓库去,又叫办公室把食堂、礼堂打扫干净,买了十几张桌子和几十张凳子与椅子,放在食堂里供大家吃饭用。
结果在下一次队务会议上,总队工会主席在会上发难,质问我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桌子和凳子。我说吃饭呀!我说盖的食堂就是吃饭的,不是放材料的。放材料有材料库,为什么不放到那里去?这位主席说,买桌子凳子是浪费,是大少爷作风、乱花钱。说陕西人蹲惯了,不愿坐椅子,你们南方人,时间长了就会习惯了。
当时,对这种落后习惯,我非常生气。我说:“陕西人过去穷,坐不起凳子,坐坐也就习惯了,不说了,就这样。”作为总队长,这点权力还是有的,所以我没有理他。
以后大家吃饭都围桌而坐,慢慢也习惯了。但过去的确可以看到,在一些县镇食堂,当地农民放着凳子不坐,却蹲在上面吃饭抽烟的现象。这种陋习随着民众生活的改善,文化素养的提高,如今很难见到了。
坐着比蹲着舒服,躺在沙发里比坐在凳子上舒服。这个道理不需要人去专门宣传,现今哪个农民家里没有几张沙发和桌椅板凳。然而,在八十年代的地质队,工会主席郑重其事给我提出来,还扣了帽子。如今陕西的这一怪,恐怕难以为继了。
在地质队说话要注意,千万不要背后议论人,为什么呢?因为你说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至少24人,24是16,地质队的工人往往是兄弟姊妹,是父子(女),是爷孙,是翁婿,是挑担,是姨表兄弟……最多的一家是爷、父、子(兄弟)三代四人,结婚组合后,是指数递增。评论一个人不是他的优秀与否,表现好坏,而是与他的亲缘关系,利益远近。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听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实的、可信的。没有十年八年的底层生活,不知道他祖宗三代的亲缘关系,我奉劝你对某人不要妄下评论,否则你何时出了问题,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地质队工人来队主要是两种形式:一是招来的,某段时间工人不够了,就招来一批。这招来的工人有两种情况,一是职工子弟,一是知青和转业军人(包括公安),另外一种是工人退休,子女顶替。招的工人几乎没有条件,特别是顶替子女,既没有文化标准,有的小学都未毕业,更没有身体条件的标准。所以,素质差较为普遍。
我刚来队时,钻机编制是一台300型钻机24人或21人,地质组是5~7人。大型水库工地往往还编有山地工作组,物探组,建材组,常常有三五十人,甚至七八十人。如开的钻机较多,常达一二百人。
从生产效率而言,一台300型钻机编制钻工用不了太多人。80年代改革开放后,国内外交流较多了,国内事业单位开始讲究生产效率和成本核算。说国外搞工民建钻探,就一两个人。既开汽车,也开钻机,打孔,取样,做试验,一两个人全干了。在这种形势下,队上开始讨论,一台300型钻机编制多少人比较合适,比较集中的意见,以12至15人较合适,如有高山送水,则人可以多一点,否则就少一点。当时我的观点,人要精干一点,一个人顶一个人用,不再编制女钻工。
地质队招工往往是一拨一拨的,而且某一年招工是在某一个地方。因此,招来的人往往是同乡,且年龄近似,父辈相互认识,故很快成为男女亲家。地质队往往是男多女少,且工人文化素质较低,女工的丈夫一般都不出队。由于过去女钻工很少,且又分散,在一起上班很容易产生恋情,而且还发生多起未婚先孕,以及与张三订婚,而怀上了李四的孩子,一时间有了许多反映。
我与书记商量,野外女工作用不大,但是非较多,且年龄慢慢大了,结婚后生儿育女,难以适应外业工作,干脆都安排到队部内业来算了。女的不去野外当钻工,有同意必也有反对的。认为男女就应同工同酬,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过去专门有女子钻机,今天为什么不能干呢?
当然,同意女的不干外业还是大多数。野外钻工干的都是力气活,女性身体单薄,力气小,能干的事就是当个记录。队上同志知道我有意不让女性出野外,但我没有马上做决定,我在队务会上说:“既然有不同意见,先放下,以后再说。”对于我这样的表态,许多人坐不住了,主要有两类人:一是女工的亲眷,父母兄弟;一类是准备把女工娶回家的人。这两股势力,力量非常雄厚,会后几天,全队都在议论此事,在会上发言不同意的人,这次成了众矢之的,被一些人骂得狗血淋头,日子很不好过。他们不敢来找我,担心我说他们,那样搞得更狼狈。我的党委书记倒找我来了,对我说,反对的只是个别人,现在都遭人骂,我看可以定下来。我说,不急,半个月后再说,你不要表态。本来是一件好事,也是人之常情,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但有些人总爱打横炮,让他尝尝被人骂的滋味。几天后开队务会议,研究了很多事情,我把女工安排之事放在最后,我说完安排意见,问大家是否同意,一致大声说:“同意!”我说:“好,就这样安排,劳人科发通知,散会。”
从安排女工的工作这件事上,我得到了一点启示。即使是好事,也不宜急,无必要去争取,更无必要去做解释工作,你不急,有人急。第二点,要示弱。在学校学习时,不要考前三名,只要你真正学懂了就行了。在一个单位你不要冒尖,这样,无论你在学校或在单位,你与群众的关系都比较好处理。
几十个女工从野外队退下来,工作岗位是个问题,不过我已有考虑,除了安排在后勤服务车间、试验室、仓库管理、出版室部门,还开办了幼儿园、缝纫部、商店,每人都有岗位,让其自食其力。总的看,此事处理还是不错的。
在地质队工作,你要像个地质队员,要适应这里的环境。身体要好,要能吃,能跑,能干体力活。但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困难,吃不饱是普遍现象。然而,跑野外,体力消耗严重。那时,干部要参加劳动,要去农村参加“双抢”,要去钻机参加搬家,帮钻机打砣处理事故,有时半夜三更爬到山上打砣。如果,你的积极性不高,就被扣上资产阶级作风,地主少爷作风。如果你爱看书而不愿同钻工们闲谝,则很可能给你扣上“只专不红”“白专道路”。如果你不爱看书,而爱与工人胡谝乱吹,则说你能与工人打成一片,能放下架子,是一个工人们喜欢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以不学无术,能与工人打成一片,则认为你是革命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别界线。如果你能同工人钻进一个被窝,更能说明你与工人站在同一战壕,能彻底脱胎换骨,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了。“文革”前夕队上分配来几个女大学生,几个后来调走了,几个则与工人结婚了。这就是典型的革命化了,白天同吃一锅饭,晚上同睡一个炕。就是那个时代的时髦。
再后,领导班子要掺沙子,要“三结合”,正儿八经的工人要当领导,领导革命,领导生产。黄河天桥电站踏勘是我院与山西省院一块合作的项目,代表我院的领导是钻探工人石师,他原是我分队的一名机长,小学没毕业,要他来领导和决策,真有点为难他了。不过他头脑还清醒,研究问题,决定工作,他还是一口一个濮队长,把我让在前面。当然,我给他出了主意,也给足了面子,踏勘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地质队不仅有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还有地缘关系,50年代初的蓝田人,五十年代末的周至户县人,60年代初的洵阳人,70年代的知识青年,80年代的职工子弟,以及老子的儿子,爷爷的孙子,亲家与亲家,翁婿与儿媳,……这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交织在地质队的工作和人事关系中,更增加了处理事情的复杂性。
陕西人的排外是明显的,地质队更为突出。我的几位男性朋友和同学,最后都调回了故乡工作。此地人缺乏气度和宽容。“如果他能把你踩在脚下,他会毫不留情。”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一位福建的朋友,在黑河工地与我告别时对我说的。他还说了一件事情,我们湖南的一位女老乡,她爱人是军人,70年代初为照顾他们家庭生活,把该女老乡调去东北。临离队时,她没有告诉外地同志,她雇了一部三轮车,拉的她一个箱子和一个铺盖,临出地质队大门时,被门房挡住了,说××组长说要对她进行检查,要她打开箱子,说着这位组长出来了。一个木箱子能装什么?况且是一位在地质队干了十五六年的女同志。检查完了,这位女同志流着眼泪出了大门。这位组长并不负责安全保卫任务,也不是队上领导,他有什么资格随便欺侮人?
这位福建同志说,我离开地质队时,要在大门口,指名道姓大骂这狗日的。我忙劝他,不必跟这样的人计较。他的为人,大家都心中有数。此人天分不高,在校学习并不好,仗着是当地人,同学、乡党、亲戚朋友一大堆,在队上当了一个中层干部,平常总是皮笑肉不笑,恃强凌弱,看人说话,因而在队威信并不高。院长曾建议将我调入队生产技术组,主管技术工作时,他从中作梗,企图阻止我调入队部。
但毕竟技术人员还是外省外地人多,干活还是靠这些人。“文革”后期,一批在外省工作的陕西技术人员,陆续调回了陕西。这批人经过在外地工作,其技术水平、文化修养、生活习俗都有很大改观。特别是在广东,长江委工作后回来的同志,对队上工作的正规化,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随着总队人员的增多,南北文化的交流,队部的闭关保守、固步自封有所改观。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把经济搞上去才是最大的成绩,因而,开始重视和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技术人员的话语权也逐渐增多。
为了提高队的生产力,必须要增加队上技术人员,提高技术人员素质。主管队上技术工作的老任提出了几项动议:一是把原武功水校毕业的工农兵中技生送大学进修;二是从钻工中选拔一些优秀工人,送中专和大专进修;三是送一批技术人员去学物探、遥感,增加工作方法手段。这些意见得到队上和院里的肯定与同意。而我当时由冯家山水库工地调回生产技术组,具体负责了这项工作的实施。
地质队的工人都是从农村招来的,有的小学未毕业。有的工人连钟表都不会看。别人给我说这故事时,我有点不太信,说是××,叫他去野外做土层渗水试验时,告知他开始是1、2、5分钟看一次渗水量,以后每10分钟计一次渗水量,渗水量误差在5%内时,再计3次即可结束试验。那天做试验天黑后,还不见回来。最后,打着手电筒找到他时,他还在做。看他的记录,早已达到稳定,就是不知道5%是多少,一直往下做。
对送去外地上学的干部、工人,还是采取考试的办法,择优选送。我出的题由最简单的小学数学,至高中的数学题,幅度拉得很大。考试结果出人意外,有个中技生得了0分。我出了10个题,由浅入深,一题10分。第一题是一个带小数点的数加一个分数,这位技干竟不知如何加。
根据考试分数,在前两名内送大学进修,再后分配至测量、物探专业。知识青年与职工子弟对等配送。技术干部主要看工作表现和专业知识掌握程度。对送去大学进修的干部今后要在地质队干一辈子,不得提出调走。
这样,前后送了四批去成都地质学院和其他大中专学校,送出学习的有几十人,这批人后来成了地质队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