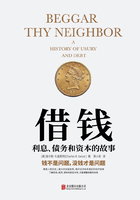
本章导读
收取利息一直被视为工业革命之前全球历史第二悠久的行业,但它损害大众福祉,违背人们应该互助、互爱的道德观念,和其他被社会排斥的行为根本就是一丘之貉。宗教准则认为它和卖淫嫖娼、纵火谋杀一样罪大恶极,不过,世俗社会对它倒是睁只眼闭只眼。中世纪时,放高利贷者常常挤在城镇贫民区,就像妓女总聚在红灯区一样。有关利息的理论和实践总是大相径庭,不过一般而论,社会宗教气氛越浓厚,对收取利息这一行为的打击就越严厉。
起初,重利和利息总被混为一谈,并未做系统的区分,宗教性文献只有“重利”一词,意思就是利息,后世才将两者区别开来。启蒙运动时期,这两者可以交替使用,只不过“重利”成了一个带有贬义的操作性术语。由于拉丁文在欧洲的使用频率江河日下,“利息”这个词渐渐被赋予了其他意思,但怎么也甩不掉中世纪时染上的色彩。近千年来,“利息”一直承受着无益于经济繁荣的解读。
“利息”的拉丁文词源是usury(即现在所说的“重利”)或usura;中世纪时演变为usuria,这是现代拼写的源头。这个词带有贬义,历朝历代皆是如此,因为中世纪的教会一方面严禁收取利息,一方面又允许合理范围内的“正常交易”。但是,不论在哪种商业模式下,鉴于古代社会四分五裂的状况,外加宗教传统的不同,人们对收取多少利息是“合理”的、收取多少利息是“剥削”,从未有过令人心悦诚服的定论。缺乏统一的信贷市场也意味着利息因地而异,甚至相差巨大。
与“利息”、“重利”这样明确的概念混在一起的还有“公平、公正”的概念,这便让借钱之举蒙上了厚重的政治色彩。在物物交换的经济体制下,利息是以实物支付的,所以计算起来很是棘手。假设,一位商人借给一位农夫一袋种子,怎么判断正常利息?偿还时该还多少、以哪种物品偿还?种子长大后成了庄稼,哪个价值更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因地而异的。以金钱作为交换媒介后,人们随即围绕着利息展开了“多少是正常、多少是过度”的唇枪舌战,但普通利息和现在并无二致。随着金钱使用范围的扩大,伦理道德也来插上一脚——只要还钱额度超出借钱额度,就被视为高利贷,因为放贷是好逸恶劳的产物,还要收取高利息,简直叫人忍无可忍!
再次回到那个老问题:到底多少才算“高利息”?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但凡为了必要消费而借贷并收取利息,这是有违公正的,理由就是借款人如果不借钱就无法生存。所以,这类借贷全都属于剥削,这种观点历史最长,《旧约》中就有提及。
绝大多数古代和中世纪评论家、作家一批判起高利贷来,就免不了要把《申命记》(Deuteronomy) 搬出来。书中提到:“万不可向兄弟姐妹放高利贷;不论是金钱、食物或任何东西,利滚利皆不可取。”“若为生人故,此举可取;若为手足者,万万不可。上苍圣主将庇佑其子民苍生,不论身处何方,紧握手中物。”不过,此处的“手足”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同一氏族的成员,也就是说,犹太人可以对非犹太人收利息,但不能对同族的犹太人收利息,后世称之为“申命记双重标准”。
搬出来。书中提到:“万不可向兄弟姐妹放高利贷;不论是金钱、食物或任何东西,利滚利皆不可取。”“若为生人故,此举可取;若为手足者,万万不可。上苍圣主将庇佑其子民苍生,不论身处何方,紧握手中物。”不过,此处的“手足”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同一氏族的成员,也就是说,犹太人可以对非犹太人收利息,但不能对同族的犹太人收利息,后世称之为“申命记双重标准”。
《诗篇》(Psalms) 里也有类似的警戒训示。“上帝之民,不可放贷收利,亦不可剥削无辜。若有此行径,将遭上帝遗弃。”这些教化,尤其是关于借钱给自己族人的训诫,成了古代和中世纪家庭手工业最普遍、最古老的基石。
里也有类似的警戒训示。“上帝之民,不可放贷收利,亦不可剥削无辜。若有此行径,将遭上帝遗弃。”这些教化,尤其是关于借钱给自己族人的训诫,成了古代和中世纪家庭手工业最普遍、最古老的基石。
约瑟夫斯(Josephus) 认为,贷方应该为碰上手头拮据的借方而知足感恩,而非图谋放贷吃利息。然而,尽管先哲好说歹说,但早期的借款合同显示,借款还息依旧我行我素。希伯来人将利率定为12%,尼希米(Nehemiah)在公元前444~公元前432年担任犹大山地(Judea)长官期间,曾颁令以12%的利率解决纷争,这一做法延续了近两千年。
认为,贷方应该为碰上手头拮据的借方而知足感恩,而非图谋放贷吃利息。然而,尽管先哲好说歹说,但早期的借款合同显示,借款还息依旧我行我素。希伯来人将利率定为12%,尼希米(Nehemiah)在公元前444~公元前432年担任犹大山地(Judea)长官期间,曾颁令以12%的利率解决纷争,这一做法延续了近两千年。
犹太人遵守《申命记》的教诲,只借钱给非犹太人,这一传统沿袭了数百年。但是,他们后来发现,欧洲的执政者先是纡尊降贵找他们借钱,等该还钱时,又义正言辞地说教会规矩禁止放贷收息。因此,自从和借钱扯上关系,犹太人既有所得,亦有所失。很显然,世俗法一般不会禁止借钱,但宗教却成了欠债不还的有力挡箭牌。
借钱给有迫切需求的族人,即使要收取利息,也必须少之又少,用今天的话说,仅仅是为了抵消借款成本。至于利息的最低额度是多少,谁也说不清。要是利息收高了,相当于贷方乘人之危,将借方逼入绝境,或者企图使其身败名裂,这无异于加害族人,将遭到全族上下的斥责,惩罚手段也因人而异,不过最常见的是驱逐流放。在古代和中世纪,借方欠钱不还,经证实有损贷方利益,也会被严厉惩处,不过贷方需要出示证据表明自己的确受到了损失,而且也没有收取高额的利息。在这里,利息和重利的区别显而易见。
在利息和借钱的讨论中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即如何准确地计算利息。如果从今到古地审视一下计算方法,便不难发现,对“利率”的概念定义和计算方法一直都在变化。部分遗存材料说明,利息计算是简单地以月为基础的,利息总额就是月度金额乘以贷款月数。利息高的贷款(拉丁文为mutuum)一般都是时间超过一年的中长期贷款。由于古代社会缺乏有组织的银行体系,因此也找不到严格的标准的偿还条款,一切都由贷方说了算。用现在的话来说,贷款人是私营性质的,即资金源头是富裕的个体和商人。
在罗马的法律体制中,声名赫赫的《十二铜表法》试图用法律来约束贵族和平民的借钱行为。一般是贵族借钱给平民,然后平民哭天喊地抗议缴利息。罗马历史中不乏禁止或控制利息的故事。公元前450年,在一次十人大公会议(Decemviri)上出台了一个法案,规定“任何人不得以超过1/12的比率收利息” 。按照公元前695年努马·庞皮留斯(Numa Pompilius)推行的《十二月历法》,即法定年利率为8.33%,而按照18世纪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计算,即月利率为1%。不过这或许有些夸大其词,因为绝大多数贷款都是一个月。1/12的利率主要源自农业,它是指一磅重的庄稼,利息为一盎司;偿还时间为每月首日;利息按年计算,不做叠加
。按照公元前695年努马·庞皮留斯(Numa Pompilius)推行的《十二月历法》,即法定年利率为8.33%,而按照18世纪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计算,即月利率为1%。不过这或许有些夸大其词,因为绝大多数贷款都是一个月。1/12的利率主要源自农业,它是指一磅重的庄稼,利息为一盎司;偿还时间为每月首日;利息按年计算,不做叠加 ,如果叠加就称为“年度叠加”,拉丁语为anatocismus anniversarius。在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更迭的那几年里,利率上涨到12%(usarae centesimae),之后百年维持不变,而后数次调整,但公元4世纪时,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再度采用了该利率。虽然利率相对较低,但对欠债不还的惩罚却依旧残酷严厉。依照当时的法案:“一旦债务成立,或法庭颁令,则必须在三十天的法定缓和期内偿还欠款。如有拖延,债务人将被逮捕,押入法庭。如果不服法院判决,或法庭上无人为其担保,债权人有权带走债务人,或将其捆绑在木桩或链条上,或令其背负不低于十五磅的重担,一切遵从债权人之便。”对该法案的其他解读显示,只要债权人高兴,甚至可以对债务人动用凌迟之刑,以及将其子女卖为奴隶。
,如果叠加就称为“年度叠加”,拉丁语为anatocismus anniversarius。在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更迭的那几年里,利率上涨到12%(usarae centesimae),之后百年维持不变,而后数次调整,但公元4世纪时,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再度采用了该利率。虽然利率相对较低,但对欠债不还的惩罚却依旧残酷严厉。依照当时的法案:“一旦债务成立,或法庭颁令,则必须在三十天的法定缓和期内偿还欠款。如有拖延,债务人将被逮捕,押入法庭。如果不服法院判决,或法庭上无人为其担保,债权人有权带走债务人,或将其捆绑在木桩或链条上,或令其背负不低于十五磅的重担,一切遵从债权人之便。”对该法案的其他解读显示,只要债权人高兴,甚至可以对债务人动用凌迟之刑,以及将其子女卖为奴隶。
尽管借贷利率和拖欠惩罚的规定就在眼前,但休想每个人都遵守。布鲁图在塞浦路斯从事数目可观的借钱生意时,利率高达48%,大大超过了官方规定的12%,并且,他还雇用中介、隐藏身份,以逃避罗马参议院的监管。历史学家阿庇安(Appian)也记载了公元前89年的一件案子——债务人和债权人各执一词,闹到了罗马地方法庭上。债务人拒绝还钱,理由是一道比《十二铜法表》更早的法令规定严禁任何形式的高利贷。双方无法达成和解,法官只好放任他们继续纠缠。债权人想到自己平白无故因为某项过时的法令而追不回钱,怒火中烧,在古罗马广场上了结了法官。参议院悬赏缉拿凶手,可惜无果而终 。
。
拉丁文的usura指代单利,usurae usurarum(利滚利)则是复利,罗马法中将后者称为anatocismus,这是大约公元前51年西塞罗从古希腊语的“利上加利”引入拉丁文的一个术语。该词早就进入罗马的立法、司法体系了,但几个世纪之后,却因查士丁尼的缘故,遭到了官方的严禁。诚然,被禁的原因并非利上加利这么简单——anatocismus是叠加在借款原数额之上的额外利息,这让借方深陷债务旋涡,情况之严峻远远超过复利出现之前,这种结局实在令人大为不快。
由anatocismus带来的严重后果被称为alterum tantum,即“翻倍”。在表示利率大大超出许可范围时(官方规定为12%),这是最精准的措词。将未支付的利息叠加在本金之上并非罗马特有的现象,古代印度也是如此。一般认为,3世纪时在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那个年代,“翻倍”和“复利”普遍遭禁,然而在《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的监管之下却死灰复燃。 这两个词体现出罗马人发展了早期的借贷利率的范围,这与数百年之后的情形大同小异。当时官方规定的利率是12%,这成了利率的下限,而利率的上限则是alterum tantum,即“让本金翻倍的利率”。尽管利率上限很高,但至少清楚地说明了借方将面临的灾难性后果,同时也反映了官方利率总遭漠视践踏的现实。照此思路,我们也顺便窥探了一下《72法则》(Rule of 72)的起源,这一经典数学法则可以快速计算出本金翻倍所需的年数——只需用72除以利率即可。
这两个词体现出罗马人发展了早期的借贷利率的范围,这与数百年之后的情形大同小异。当时官方规定的利率是12%,这成了利率的下限,而利率的上限则是alterum tantum,即“让本金翻倍的利率”。尽管利率上限很高,但至少清楚地说明了借方将面临的灾难性后果,同时也反映了官方利率总遭漠视践踏的现实。照此思路,我们也顺便窥探了一下《72法则》(Rule of 72)的起源,这一经典数学法则可以快速计算出本金翻倍所需的年数——只需用72除以利率即可。
如果短时间内就使金额翻倍,例如一两年,那绝对是违背借贷精神的。可是即便在复利情况下,贷方将借方交纳的利息再借给他人,也无甚不妥。收取复利是指,由于利息叠加、利率较高、偿还时间较长,使得借方所欠的利息居然高出了本金。这才是人们对复利忍无可忍、最终严禁的原因。但是,严禁复利并没有起到斩草除根的作用。复利,尤其是半年性复利,在13世纪早期就在斐波那契的数学作品中首次亮相了,不过具体运算方法模棱两可。
且不管利息应该如何计算,其长期存在于商贸交易之中的事实,似乎与宗教严打严禁的主张背道而驰。不过,必须明确金钱借贷和物品借贷在收取利息一事上的区别。人们常视利息为贷方好逸恶劳和借方走投无路的恶果,因而危害甚大。贷方借出一笔钱,不管借方是以金钱偿还还是以物品偿还,在绝大多数古代和中世纪学者看来,这都是一种奢侈的做法,因为贷方没有创造价值,没有收获有意义之物,但却占尽了好处。那时的农民和市民过一天是一天,几乎没有储蓄和经营资本,因此,这种观念在当时勉强糊口的经济形势下屡见不鲜,尽管后来的数百年间贸易腾飞,对商贸投资资本的要求渐渐增加,但这种想法早已根深蒂固。
除了《圣经》和罗马的一些文献,亚里士多德也被视为利息问题的哲学权威,尤其受古代和中世纪教会人员推崇。他的老师柏拉图没怎么提利息问题,不过也曾说过:“不应……借钱收利息。法律不会保护那些索要利息或本金的人。” 罗马衰落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欧洲消失,直到21世纪才被阿拉伯学者再次引入。经过再度引介,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13世纪的经院派哲人中盛行起来,集大成者当属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以独一无二的视角审视利息问题,被不少中世纪学者和经院派人士尊称为“先哲”。《旧约》、氏族派系或清规戒律对重利都持贬低的态度,而亚里士多德则是从哲学角度来看待该问题的。他认为,收取重利对借方不公平,是对借方的肆意剥削,因而是最有违自然的谋利手段,“毋庸置疑,卑鄙无耻的放高利贷者恶贯满盈,以钱生钱,敛财牟利,扭曲了金钱原本的用途”。
罗马衰落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欧洲消失,直到21世纪才被阿拉伯学者再次引入。经过再度引介,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13世纪的经院派哲人中盛行起来,集大成者当属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以独一无二的视角审视利息问题,被不少中世纪学者和经院派人士尊称为“先哲”。《旧约》、氏族派系或清规戒律对重利都持贬低的态度,而亚里士多德则是从哲学角度来看待该问题的。他认为,收取重利对借方不公平,是对借方的肆意剥削,因而是最有违自然的谋利手段,“毋庸置疑,卑鄙无耻的放高利贷者恶贯满盈,以钱生钱,敛财牟利,扭曲了金钱原本的用途”。 也就是说,金钱是死物,只可用作交换媒介,不该用作自我繁衍之物;其正当用途是促进货物或服务的交易;要是放贷收利有违公正,就算进行借贷,也不能收取重利。这倒不是说古代雅典人不允许借钱收利,而只是说那时的世风舆论掌舵人影响深远,长达数世纪,在他们眼中,此举损害了借方,满足了贷方,万万不可取。
也就是说,金钱是死物,只可用作交换媒介,不该用作自我繁衍之物;其正当用途是促进货物或服务的交易;要是放贷收利有违公正,就算进行借贷,也不能收取重利。这倒不是说古代雅典人不允许借钱收利,而只是说那时的世风舆论掌舵人影响深远,长达数世纪,在他们眼中,此举损害了借方,满足了贷方,万万不可取。
不少古代社会,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重利法》还受到道德、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这些社会出台了旨在控制意图跟风贵族或统治阶级的下层阶级大肆消费的《节约(消费)法》,法律规定了个人能够拥有的奢侈品数量。罗马的第一项节约法是《奥庇乌斯法》(Lex Oppia),于公元前215年出台生效。这项法律内容颇丰,其中一条规定了一位妇女可以持有的用于衣着打扮的饰品等物件数量。一般认为,《节约法》主要是用于扼杀非贵族阶层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只有贵族才有资格打扮得华丽奢侈,商人和平头百姓想都别想。不过购买奢侈品和借钱关系密切,因为那些向富裕公众人物看齐的人,多数要靠借钱欠债才能达到目的。很多时候,《节约法》和《重利法》有名无实,然而却反映出一种焦虑,很多人担心借钱居然是为了消费,而非生产性目的,这会浪费宝贵资源,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时期下。《奥庇乌斯法》的出台背景是与迦太基帝国(Carthage)进行第二次布匿战争(The Second Punic Wars)时期,罗马打了胜仗,该法律规定也松懈下来。和《重利法》的变迁一样,淡出舞台的《节约法》总会在后世再度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