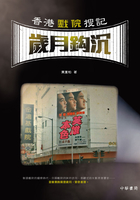
帶位和座號
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收藏、攝於1909年的一張太平戲院內觀照片,顯示院內座位屬可移動的靠背椅。究竟當時戲院是否普遍安排這種散置的座椅?有沒有編號?要不要帶位員引領?
1927年3月,薛覺先演出的新片《浪蝶》在九如坊新戲院公映。有作者寫下影評,記述他和同事梁先生結伴觀影的經歷,提及進入放映廳時的情景:
到了新戲院,影戲已開演了十分鐘許,入門黑漆漆一團,看不出座位,左邊滿了人,右邊又滿了座,且十之七八是女性,更令我們不便。我們在當中進出道上,徘徊了數次,覓不得座位,梁先生喚那個執電筒帶路的,找二個座位,他仍懶洋洋的坐着不動,只將電筒一射,謂:「座位隨處都是,你去找好了。」他不知執着電筒幹什麼,戲院裏大概請他執電筒閱電影,而未附帶着招領閱客的職務罷。[1]

(圖片提供: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
 第一代太平戲院的內觀。照片攝於1909年12月,該院當天舉行「香港大學堂籌款演戲」活動。
第一代太平戲院的內觀。照片攝於1909年12月,該院當天舉行「香港大學堂籌款演戲」活動。
上文活現當時戲院運作的概略,包括映廳內有手執電筒的職員,負責「招領閱客」。新戲院設包廂、散廂、超等、頭等及二等共5個座區,這段文字沒說明作者買了哪區的票,但看來不設畫位,座位毋須編號,他們要自行在漆黑中摸索。場內男女觀眾雖然同坐,但在暗黑中碰撞,仍須避忌。
文中雖用上「那個執電筒帶路的」,但「帶位」一詞當時已被採用。1928年一篇題為〈帶街與帶位〉的文章便指出:「帶位者何?茶樓中引人入座者也……帶位一職,本非茶樓所獨有,戲院及影畫戲院均有之。」惟該文作者指戲院帶位的工作性質並無特殊,沒有細論。[2]當時戲院寥寥可數,任「帶位」者數量有限,大概這是作者認為無甚可談的原因。
至於戲院帶位的職業操守,按上文描述,實不敢恭維,更可能是普遍的陋習。1927年啟業的利舞台,一開始便以嶄新的方式營運。戲院開業當天,報章一則「利舞台之演劇情況」報導指出:「入座後,不見舊式的帶位人,其招待員均優禮相待。」[3]言下之意,其他各院的帶位者多屬款客不周,有欠禮貌。
另外,利舞台亦把全部座位供顧客自由挑選。該院在1927年3月24日刊出的廣告便強調:「凡本臺演戲,必預將連日劇本佈告,同時以大堂公座圖則,交與票房,任從諸君採擇,先到先得,採公開主義,更無門外沽票。」把這則廣告的用詞反過來,正好反映其他戲院在選座上的諸多問題。
1925年初,有作者在報章撰文,力陳戲院的流弊,指放映西片的戲院如皇后、新比照,無論座椅及秩序,遠勝一般粵劇戲院。粵劇戲院雖設廂房、貴妃床、梳化床、對號位,原意是「以先後為序,憑票對號」,但戲院管理不善,上佳座位被惡霸操控,抬高價格在院外兜售。[4]所以,利舞台才強調「先到先得,採公開主義,更無門外沽票」。
該評論續指,戲院的座椅殊不舒適:「後座者踏足於前座椅後之橫木,稍一用力,則前椅移而推於前;或坐前椅者,稍一曲肱,或稍一靠後,則傾倒椅後所乘之茶果點心瓜子等物,淋漓狼藉。」帶位員更乏善可陳,既不懂招呼客人,加上不穿制服,衣衫襤褸,下等看客容易冒充帶位,搶奪戲票。「所設領票人,似乎專為最高等而設,其餘則可以自由覓位,不論等級,空則坐之。故中下之客,入場較早,多佔踞同上各高等之座。」總而言之,「各院秩序均極紊亂!」[5]
可見二十年代一般戲院,由管理人到惠顧者,普遍欠缺遵守秩序、對號入座的意識。翻看1934年報章報導油麻地戲院裝修後煥然一新,提到「雖前座位,亦復加編號碼,以利觀眾」。[6]似乎到三十年代,部分戲院仍未給最廉宜的座位制定編號,毋須對號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