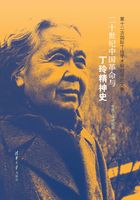
三
为丁玲作传,因此也是困难的。她的一生在荣辱毁誉之间的巨大落差,特别是她在后革命时代的“不合时宜”,使得要讲述她的故事,总是难免捉襟见肘、顾此而失彼。
同情和热爱她的人,容易把故事讲成“辩诬史”。丁玲是复杂的,因此围绕着她的种种误解和传说,常使熟悉和理解她的人不平。特别是,作为革命体制内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丁玲的后半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写文学作品,而是在写“申辩书”。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丁玲”,总是要与复杂的历史人事关系相关的各种谣言、传说、误解和歪曲做斗争,总是难掩难抑辩护之情。但是,如果将丁玲的一生,固执在说明她之“不是”,反而使人无法看清她之所“是”。更重要的是,辩护式写法其实也使写作者停留在丁玲置身的历史关系结构中,而无法超越出来尽量“客观”地描述这个“结构”本身,由此重新理解丁玲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20世纪已然远去,曾经与丁玲爱恨纠葛的当事人和利益格局,今天也大都已成历史。在这样的情境下,客观地描述丁玲的一生,不止具备可能,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知丁玲和20世纪革命的必要步骤。
讲一个完整的丁玲故事,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回到“丁玲的逻辑”。1941年在延安的时候,丁玲写了后来引起无数争议的著名小说《在医院中》。关于小说的主人公陆萍,丁玲说,这是一个“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这固然是在谈小说创作,其实也是丁玲的现身说法。
丁玲是一个个性和主体性极强的历史人物,对她喜者恶者大都因为此。喜欢者谓之“光彩照人”“个性十足”,不喜欢者谓之“艺术气质浓厚”“不成熟”“明星意识”,批判者谓之“自由主义和骄傲自满”“个人主义”……所谓“丁玲的逻辑”,就是她始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面对、认知外在世界,并在行动和实践过程中重新构造自他、主客关系,以形成新的自我。她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并不自恋;她有突出的主观诉求,但并不主观主义;她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但并不封闭;她人情练达,但并不世故;她的生命历程是开放的,但不失性格的统一性……尽管一生大起大落,经历极其复杂,晚年丁玲对自己的评价却是“依然故我”。
如何理解这种“丁玲的逻辑”,实则构成理解丁玲生命史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