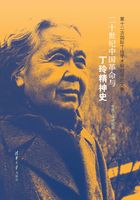
二、白色恐怖在美国的反响
美国的知识界对中国左翼政治和文化的关心可以追溯到20年代中期。例如,著名的杂志《劳工保卫者》(The Labor Defender)在1927年发表了三篇有关中国的文章,1928年又发表了九篇。与中国相关的文章与日俱增,1932和1933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九篇,达到了一个发表的高潮。 30年代初期,以中国为焦点的文章也出现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这样的主流期刊上。
30年代初期,以中国为焦点的文章也出现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这样的主流期刊上。
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上海以及中国南部的劳工问题和左翼抗争上。例如,1930年史沫特莱为《新共和》撰写的文章题为《中国的农民和地主》。该文仔细描述了长江沿岸出现的激进农民运动。史沫特莱认为,这一运动的出现预示着一种更广泛的反对国民统治的运动。 随着30年代的推进,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美国杂志对中国劳工政治问题日益增加的兴趣。中国开始“热”起来了。上海的劳工积极分子,例如30年代末被国民政府处决的黄平,成了美国迈克·高德(Mike Gold, 1894—1967)和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 1901—1982)等左翼知识分子的英雄偶像。或许,美国支持中国劳工激进分子最令人注目的例子便是,1931年的纽约,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sier, 1871—1945)等一大群美国工人和作家走上街头抗议国民党杀害六位中国作家。
随着30年代的推进,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美国杂志对中国劳工政治问题日益增加的兴趣。中国开始“热”起来了。上海的劳工积极分子,例如30年代末被国民政府处决的黄平,成了美国迈克·高德(Mike Gold, 1894—1967)和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 1901—1982)等左翼知识分子的英雄偶像。或许,美国支持中国劳工激进分子最令人注目的例子便是,1931年的纽约,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sier, 1871—1945)等一大群美国工人和作家走上街头抗议国民党杀害六位中国作家。

发表于1931年8月《新大众》上的《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之死》。

发表于1943年6月27日《新大众》上的茅盾短文的翻译。
美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为什么对中国如此感兴趣?作家们,例如迈克·高德,在中国似乎看到了美国政治和经济继续恶化后可能出现的样子。在美国,劳工运动和左翼的反对声音早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伊始就出现了。股票市场于1929年崩溃,并引发经济大萧条,这一切又在1931年的美国政治和文化中激发了大规模的左翼和社会主义力量。这场运动最有力的表率便是30年代的“文化战线”了。“文化战线”不分性别、不分种族地凝结了所有想要通过劳工平等和重新分配财富来改造美国社会的工人、职业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他们都坚信文化的力量,坚信文化运动可以帮助他们实现目标。尽管这一社会运动一部分是因为受到了苏联国际主义的启发,美国的学者认为文化战线运动主要是吸收了美国当地的思想资源。 美国历史将铭记30年代,因为它是第一次,可能也是仅有的一次,社会主义占据美国社会的主流。
美国历史将铭记30年代,因为它是第一次,可能也是仅有的一次,社会主义占据美国社会的主流。

史沫特莱1932年3月30日发表于《民族》上的《上海的恐怖》一文,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的“白色恐怖”。

史沫特莱1934年6月13日发表于《新共和》上的《上海插曲》,再次向美国读者介绍上海的“白色恐怖”。

(续上)
虽然美国的激进分子面临着严酷的政治打击和各种困难,但是中国的“白色恐怖”更为惨烈。美国左翼所担心的那可能在美国发生的一切,例如对激进思想和言论的暴力镇压,已经变成了上海活生生的现实。《新大众》的编辑每周都能读到有关中国作家被国民党杀害的报道。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写作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美国的情况虽然不好,但远不及上海恶劣。因此德莱赛和史沫特莱等美国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案例,可以借此探讨世界范围内的左翼和劳工运动。一方面,上海的政治迫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另一方面,对政治迫害的反抗也达到了顶点。美国的激进分子们为鲁迅、丁玲、茅盾以及其他众多挺身面对暴力政府的中国作家所打动。美国的左翼运动者们想在中国的左翼抵抗经验中吸取经验。
我们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寄给美国左翼领军杂志《新大众》的一系列的信件为例。1931年1月,左翼作家联盟寄出了一份“来自中国作家的通信”,该信作为社论刊登。在这份信中,中国作家告诉美国左翼知识分子中国正在经历的政治危机以及正在大行其道的“白色恐怖”。信里写道:“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正在使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革命文化运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希望揭露国民党的暴行能够激发美国左翼人士的同情,并在他们那儿寻得援助。信中说,“我们需要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支持。我们呼吁世界各地的同仁给予我们任何可能的帮助,公开中国的革命斗争,和我们一起反抗那些支持中国反动势力的帝国主义力量,迫使他们从中国撤走。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支持,面对革命工人和农民的抵抗,国民党连一个月也抗不住” 。1931年6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又寄去一封信,再次作为《新大众》的社论刊出。该信唤起了美国读者对发生在上海的“白色恐怖”的记忆。信里说“白色恐怖”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越演越烈。左翼作家联盟还仔细描述了国民政府如何处决了几位成员。信中写道:“白色恐怖已经影响了中国革命的文化领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已经失去了许多成员。许多作家被判三到七年的监禁,狱中的情况极差,他们往往在狱中囚禁几个月后就牺牲了。他们身受镣铐,在中国黑暗封建的监狱里等死,或是在外国租界的审讯房里倍受折磨。”
。1931年6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又寄去一封信,再次作为《新大众》的社论刊出。该信唤起了美国读者对发生在上海的“白色恐怖”的记忆。信里说“白色恐怖”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越演越烈。左翼作家联盟还仔细描述了国民政府如何处决了几位成员。信中写道:“白色恐怖已经影响了中国革命的文化领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已经失去了许多成员。许多作家被判三到七年的监禁,狱中的情况极差,他们往往在狱中囚禁几个月后就牺牲了。他们身受镣铐,在中国黑暗封建的监狱里等死,或是在外国租界的审讯房里倍受折磨。” 《新大众》的编辑们配合着照片刊出了被国民党杀害的“五烈士”的生平介绍。
《新大众》的编辑们配合着照片刊出了被国民党杀害的“五烈士”的生平介绍。

1931年1月《新大众》上的文章,题为《来自中国作家的通信》。

1931年6月《新大众》上刊登的《中国作家致全世界的呼吁书》。
到30年代中期,从中国左翼作家寄来的报道已经在《新大众》《新共和》和《工人日报》(The Daily Worker)等报纸期刊上司空见惯了。从谈论中国文学到中国政治和社会,许多文章在这些拥有广大读者且代表美国智识中心的杂志上定期刊登。美国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属于左翼的读者,非常了解中国以及中国的政治危机。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主要由伊罗生(Harold Isaacs, 1910—1986)、史沫特莱和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等20年代就移居中国,且对中国左翼运动抱以同情的美国国际主义者在其中穿针引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形式的中美文化交流和以前的诸种交流不同:以前的交流往往更多地在农业发展领域,或者是留学交换,而如今的交流却在和自由相关的言论空间中展开。比如说,20年代中期,许多美国的农业学家到南京,和当地的中国工人一起组队,意图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赛珍珠就是当时的随行团员之一)。又例如,许多中国留学生利用庚子赔款远赴哈佛和哥伦比亚求学,膜拜实用主义这样的美国政治和社会理想。 与此不同,我们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新大众》的交往中看到的是一种独特的中美左翼文学的交流与接触。
与此不同,我们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新大众》的交往中看到的是一种独特的中美左翼文学的交流与接触。
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会讨论这种中美交流或“跨太平洋文化战线”的主要思想和文本。我的主要论点是:这种交流非常特殊且重要,因为我们习惯性地以“苏联国际主义”来理解30年代美国和中国的激进主义,而它却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虽然在美国和中国,左翼运动的兴起是由于苏联的组织和动员,但是在中美激进分子接触以后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自主的国际主义左翼思想。我认为有许多思想并非仅仅来源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有着更丰富的形成历史。中国和美国在30年代都处于苏联和欧洲政治文化思想传统影响的边缘。因此,他们可以创造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概念的新谱系。也正因为如此,跨太平洋联系尤其吸引人。中美的左翼知识分子找到了共识,发现了一个既可行又具有创造性的综合思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