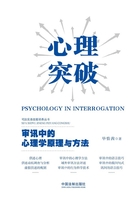
一、虚假供述的形成
1.身体与心理强制的审讯方法
美国错案报告中认为非法审讯方法与虚假供述关系密切,包括逼供、辩诉交易和青少年及精神有障碍群体。向嫌疑人呈现虚假证据在美国是被允许的,“如果审讯人员对嫌疑人说,我们已经在现场提取到你的指纹(实际上没有),你还是交代吧。这种欺骗就无不当”(何家弘,2008)。但心理学家的研究却发现,使用这一圈套会增加虚假供述发生的可能性。事实上,在许多被证实的虚假供述案件中都曾用到过这一圈套。
引发虚假供述的因素很复杂,包括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个人因素有:(1)服从。以古德琼森服从量表为研究工具的研究表明,被试出更高的服从特征;(2)受暗示性;(3)年龄。青少年在决策中显示出“不成熟的判断”的特点,缺乏对未来风险的感知能力。情境因素包括:(1)诱骗;(2)许以利益;(3)威胁、压力;(4)身体、精神折磨。
无论是个人因素还是情境因素不外乎为身体强制与心理强制的两大方法。身体强制主要着眼于对犯罪嫌疑人肉体施加痛苦的方式来迫使犯罪嫌疑人做出供述。在人类发展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践中的审讯方法主要是由身体强制所主导的。18世纪末期,启蒙思想家对于身体强制的审讯方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身体强制的合法性遭到了重创,并在后来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以及判例所禁止。如今,身体强制的审讯策略已经成为国际公约所明文禁止的行为,随着身体强制策略因其严重侵犯人权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心理强制策略便迎来了其发展期。在率先废除身体强制的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心理强制策略已经成功地取代了身体强制的地位,但不能忽视的是心理强制策略的潜在风险。
美国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与身体强制的审讯策略不同,心理强制的审讯策略不仅具有导致强迫顺从虚假供述的潜在危险,而且还可能诱发新的虚假供述类型——强迫内在化虚假供述。所谓强迫顺从虚假供述是指无辜者出于工具性的目的,例如,避免令人厌恶的处境、逃避各种明示或者暗示的威胁、获得或明或暗的各种好处,而对其根本未实施的犯罪做出自我归罪性陈述,尽管犯罪嫌疑人知道自己是无辜者。心理强制的审讯策略之所以容易导致强迫顺从性虚假供述是因为心理强制的审讯策略,常常使犯罪嫌疑人形成一种错觉,即警方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其有罪,只有做出有罪供述才能获得量刑上的优待,这种错觉经常导致部分无辜者陷入两难选择的境地。要么做出承认犯罪以获得从宽处理的理性选择,要么做出以丧失量刑上的优待为代价的感性选择——矢口否认。在这种两难的选择过程中,有些无辜者就会选择暂时做出虚假供述,以求得量刑上的好处,然后再想方设法寻求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与身体强制诱发的强迫顺从性虚假供述容易引起警方自身的警觉不同,由心理强制引发的强迫顺从性虚假供述很难引起警方的警惕,这是因为由心理强制诱发的强迫顺从性虚假供述的产生过程与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陈述的产生过程一样,二者都是在审讯人员的高度暗示性和诱导性审讯策略的猛烈攻击下,经过长时间的拉锯战后而获得的。因此,在心理强制的审讯时代,对于虚假供述的辨识更加艰难。[3]
强迫内在化虚假供述是指无辜且脆弱的犯罪嫌疑人由于受到高度暗示性和诱导性审讯策略的影响,在审讯的最后阶段真诚地相信自己实施了所指控的犯罪行为而做出的陈述。以美国为例,由于米兰达规则的确立,从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审讯实践便基本实现了身体强制的转变,并且在审讯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心理学审讯策略,这些审讯策略不仅成功诱使80%的犯罪嫌疑人放弃了米兰达权利,[4]而且还采取有效的审讯策略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顺利地拿到了口供。
我国当前的审讯方法也面临着转型问题。近年来,诉讼法学界的有些学者提出应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威胁、引诱、欺骗等审讯方法应给予一定的宽容度,与此同时,侦查理论界以及实务界也开始加强了对于审讯方法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审讯策略。在我国长期的审讯实践中,侦查人员根据自己的审讯实践经验总结了一些审讯方法,其基本的程式是以施加压力为主要方法,以增强犯罪嫌疑人的紧张与焦虑,利用犯罪嫌疑人求生、求轻的本能对压力产生服从或屈从,有的则以利益作为诱因,使犯罪嫌疑人利益屈从。其供述的模式主要有:(1)在侦查人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感召下供述;(2)在侦查人员告诉他如果不承认可能带来不利后果后供述;(3)在侦查人员做出某种承诺后供述;(4)身体和精神折磨之下供述。可以看出,上述几种供述模式都是由于情境性力量,即诱因、压力、诱导策略促使嫌疑人供述,而“逼”和“诱”的因素下增加了虚假供述的风险,而一旦这种情境因素消失或暂停,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翻供(见图11、12、13)。

图11:自白的几种情形

图12:自白的原因

图13:虚假供述的产生风险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是由于审讯压力或强制审讯导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自愿供述,但因为一些即时附带利益而开始屈服于审讯者的要求和压力。附带利益有:(1)供述后准许回家;(2)结束会见;(3)应付情境要求,包括感知压力的手段;(4)逃避警方的羁押。[5]犯罪嫌疑人可能不十分清楚供述后的后果,但他已经感知到现在所面对的利益的诱惑、强制审讯的重压、身体折磨等情境因素带给的压力,即时利益已经超过了不确定的后果使他选择做虚假供述;另外,短期的虚假供述比直接否认的惩罚后果更能接受,这更增加了犯罪嫌疑人选择做虚假供述的可能。Elliot Arronson等人认为:“相当大的奖赏或严厉的处罚,能够为行为提供强有力的外部理由。因此,如果你只要求一个人做一件事或者限制他做一件事并且仅此一次,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予相当多的奖励或严厉的处罚。但是,如果你要对方形成固定的态度或行为,那么导致服从的奖赏或处罚越少,最后的态度改变会越大,而且效果越持久。大量的奖赏及严厉的处罚都是强烈的外部理由,因此能够激发顺从行为但阻止了真实态度的改变。”[6]
2.嫌疑人的受暗示性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coerced-compliant false confession)和强迫—内化型虚假供述(coerced- internalized false confession)即是错供,强迫屈从型错供,包括完全无辜的屈从型错供和不完全无辜的屈从型错供两种类型,前者是指犯罪嫌疑人内心也不相信自己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行为,而是在外部压力下被迫做出的屈从表现;后者是指犯罪嫌疑人具备某些违法犯罪的事实,但在外部压力下被迫承认夸大的或不存在的犯罪事实,这种屈从型错供,往往会被既有的违法犯罪事实所迷惑。错供的形成原因出于非法审讯方法、嫌疑人个性的影响。其中暗示易感性是较为重要的特征。
受暗示性是指个体对外界的暗示性刺激以特定的方式做出反应的倾向。例如,在审讯情境中,办案人员在正式向团伙成员之一的某犯罪嫌疑人提问之前,花了较长的时间认真翻阅一本厚厚的案卷,侦查人员的这一行为,对犯罪嫌疑人就是一个暗示性的刺激,是用间接的方法向犯罪嫌疑人传递一种信息,即他的某个同伙已经做出了详细的供认,办案人员正在翻阅的就是对其同伙的审讯笔录。某犯罪嫌疑人是否能够受到这种信息的影响,并且按照办案人员的期待形成其同伙已经供认的认识并改变拒绝供述的态度,与其“受暗示性”的强弱有关。
英国学者古德琼森(Gudjonsson)教授提出了“审讯的暗示感受性”概念来解释不同的人对于警察审讯反应的差异性。他还发明了古德琼森暗示感受性量表(Gudjonsson Suggestibility Scale,简称GSS),以具体测定个人对审讯的暗示感受性。古德琼森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暗示易感性的强弱,与其个性特征有关,例如,易于相信他人、低智商、记忆力差、低自尊、缺乏自信以及焦虑等高度相关(Gudjonsson,1991)。[7]除了犯罪嫌疑人因个性特征而具有的受暗示性特点,审讯情境本身也会导致犯罪嫌疑人受暗示性增强,主要理由有如下三点:
(1)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易产生不确定性认识。一般来说,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的情形下,面临着法律追诉或刑罚惩罚的可能性,无论犯罪嫌疑人是否与案件事实有关联,对办案人员掌握证据的情况及审讯意图的认识都处于不确定状态。但这些情况对犯罪嫌疑人选择供述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迫切需要了解这些信息。其迫切性越强,则其对认识对象的注意程度越高。当个体全神贯注于注意对象时,会导致感觉阈限降低而感受性增高,从而较易受办案人员提供的暗示信息的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犯罪嫌疑人感受性不正常增高,一方面与犯罪嫌疑人对办案人员提供信息的高度关注有关,另一方面与犯罪嫌疑人自身对有关信息的记忆和认识的不确定性有关。“不确定性”在暗示现象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暗示性刺激能够引起被暗示者的关注并且导致被暗示者做出特定的行为反应,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被暗示者对暗示性刺激存在着“不确定”的认识。例如,犯罪嫌疑人非常清晰地记得自己在犯罪现场始终是戴手套作案,即使办案人员向其暗示已经提取到他留在现场的指纹,犯罪嫌疑人也不会受这种暗示刺激的影响而形成办案人员已经掌握其犯罪证据的认识。
在很多情形下,在外界信息的影响下,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对证据暴露情况的“确定性”认识是可以被改变的。一方面,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必然要在现场留下一些物质痕迹甚至是极少量的微量物证,或者有未被犯罪嫌疑人感知到的目击证人等。因此,即使是惯于伪造现场、反侦查手段高明的犯罪嫌疑人,也常常不能形成“确定性”的认识,即侦查人员不可能掌握有关他犯罪事实的证据;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在羁押中由于与外界联系中断,对侦查人员掌握证据情况也无从知晓。这种情况也说明,犯罪嫌疑人虽有侥幸心理,但其侥幸心理是盲目的,是建立在其主观“不确定”认识的基础上的。笔者的实证调查(1998)同样证实了这种推理的正确性。[8]被调查的1104名在押犯罪嫌疑人,侥幸心理相对较弱。犯罪嫌疑人侥幸心理的脆弱,使其容易受外界有关信息的影响而改变其关于侦查人员掌握证据情况的认识。
(2)办案人员权威性的地位及信息不对称都会使犯罪嫌疑人的受暗示性提高。审讯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互动,在这种互动情境中,互动的双方在占有信息与社会地位方面都极不平衡。
就与犯罪有关的信息来说,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的了解,是全部犯罪事实中他自己亲身经历的部分;办案人员对犯罪事实的了解,是全部犯罪事实中除了尚未调查清楚的部分之外的部分信息,其中尚未调查清楚的部分,主要是犯罪嫌疑人在封闭的犯罪环境中亲身经历的部分,而这部分内容,也是办案人员希望通过审讯行为加以确定的部分。由于办案人员有资源(现场勘查所得、调查访问以及各种情报信息的收集等)可以查清大部分与案件有关的信息,而这部分信息是犯罪嫌疑人并不掌握的,因此,就此类信息来说,办案人员具有相对较高的权威性,犯罪嫌疑人对办案人员传递的此类信息,可以不加批判地接受。
就双方的社会地位来说,在审讯情境中,办案人员处于支配与控制的地位,而犯罪嫌疑人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低地位者一般倾向于相信高地位者所传递的专业性信息。如果办案人员在审讯过程中始终能够以专业的精神与语言向犯罪嫌疑人提问以及对犯罪嫌疑人的提问做出专业性的反应,会提高在这种互动中的权威地位;此外,办案人员如果能够与犯罪嫌疑人建立良好的心理相容关系,也能够提高互动中的人际信任。审讯互动中办案人员权威地位的确立以及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信任,都可以使犯罪嫌疑人的受暗示性提高。
(3)审讯情境会使犯罪嫌疑人产生紧张焦虑情绪。在笔者的调查中,审讯中最为突出的心理与行为表现是“紧张恐惧”。无论是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还是无辜者,绝大多数都极为关心审讯及自己供述行为的后果,害怕在审讯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身体或精神的折磨。此外,在羁押与审讯环境中,犯罪嫌疑人对未来及可能遇到的危险的认识是不确定的,由此而易形成焦虑感。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的紧张情绪和焦虑感,使他们的认知水平下降,对自己的记忆能力与记忆的内容都有可能产生怀疑感。当侦查人员的提问中包含着某种需要犯罪嫌疑人搜索记忆的内容加以确定的信息时,犯罪嫌疑人就会产生困惑感,难以形成确定性的认识,从而可能产生接受侦查人员的信息的倾向。
此外,根据国外学者的理解,紧张或焦虑情绪本身往往是和有罪感有直接的联系。当受暗示性高的犯罪嫌疑人在羁押或审讯情境中体验到强烈的紧张、焦虑情绪时,可能会使他们产生错觉,认为这种情绪就是他们自身有罪的一种生理唤醒。也即是说,情绪本身可能就是内化型错供形成的一种原因(Schachter & Singer,19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