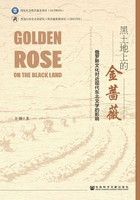
二 移民与殖民的影响
东北地区处于中国的边疆,自古以来地广人稀,生产力相对落后,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清政权龙兴于东北并统治中国之后,中原大量移民涌入东北,而移民的构成主要是流放的罪犯和垦荒的农民。清代自顺治初年,将内地的各种罪犯,发配到边远省份及烟瘴之地。这种遣犯,史称流人。据推测,清代东三省流人当在十万左右。”[14]流人中有农民、手工业者、士兵、商贩、太监、官吏和文人学士等,他们不仅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将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传入了东北地区。移入的垦荒农民数量更多,清初的招垦时期(1644~1667年),在招民垦荒和遣戍流人政策下,大批关内人口流入辽东。这一时期大量移民的移入不仅有利于当地的社会安定和农业发展,对医治明末清初战争遗留下的创伤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进入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不顾清政府的禁令,源源不断地流入东北,至1840年东北地区总人口已经突破300万人,比100年前猛增了七八倍。这时全国人口已经达到4亿,人口压力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为镇压关内农民起义,八旗士兵大批内调,东北边防空虚,又因为赔款、军费,清廷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希望以民垦增加收入。另外,关内汉人的大量流入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清政府于咸丰十年(1860)正式在东北局部地区弛禁放荒。咸丰以后,随着吉、黑两省开放,迁至这里的华北农民日增,至1897年更是全部开禁。这样既减轻了关内的人口压力,又充实了边防。此外,统治阶级还制定了垦民可以减免船价、宽限起科、“酌量给以工本”的政策,所有这些,更促使关内贫苦农民蜂拥北上,终于形成了一股“闯关东”的狂潮。
另外,自19世纪后期开始,经俄罗斯迁入东北的朝鲜人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迁移人群。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19世纪末期,随着延续200年的清朝封禁政策的解除,朝鲜人迁入东北变得容易。关于这一时期朝鲜人的迁入情况在中俄东部几个边境县的县志中有所记载。中东铁路东线铺轨时期(1898~1903年),沙皇俄国为铺设中东铁路,从西伯利亚和朝鲜雇佣了大量劳工,铁轨铺设完工以后,部分劳工留在绥芬河、磨力石、一面坡、阿城、哈尔滨等铁路沿线定居。1910年‘日朝合并’以后,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反日志士和朝鲜人纷纷逃离故土,其中很多人越过图们江和鸭绿江迁至东北境内,另外还有大批人口迁至俄罗斯,再迁到东北境内。这一时期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大量增加,1908年延边朝鲜族人口为9100人,到1911年猛增为127500人”[15]。沙俄一直对东北虎视眈眈,侵占了东北大片土地。日俄战争之后,日、俄两个侵略者划定了各自在东北的势力范围。沙俄占据北满,“哈尔滨曾是俄罗斯侨民在中国的最大聚居地,一度被视为在华俄侨的首都”[16],1922年是俄侨在哈人数最多的一年,据统计,高达155402人。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从日本本土发动了大量人口移民东北,分为初期移民、“武装移民”、“百万户移民”、“青少年义勇军”移民等。日本帝国主义希望通过这种移民的方式,实现对东北这块肥沃黑土的殖民统治,这种移民侵略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日本战败以后,仍有一批日本人滞留在东北地区,融入了这片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和百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又将全国各地的大量人口送入东北这块广阔天地。
综上可以看出,清代以来,东北地区成为典型的人口迁入地区,移民构成了东北地区人口的主体。而人口迁移的意愿、规模等与东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直接相关。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全部复杂关系表现形态的总和。大量的移民和殖民势必会对东北地区的文化特色产生深刻的影响。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移民为东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地区原有的渔猎、游牧为主的社会形态,农耕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靠渔猎和游牧生存的人群逐渐减少,到当代已渐趋绝迹。前文已述,中原移民主要由流人和垦荒农民组成,而流人的成分比较复杂,包含了一些掌握上层主流文化的官吏和文人学士等,他们的到来推动了东北地区文化的发展。但是这种高文化人群数量极少,占移民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处于乡村底层,在关内难以生存的垦荒农民,他们一般都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深厚的国学根底。通过他们移植过来的是几千年来沉积在中原农村的儒家文化,这样的儒家文化难免欠缺一点精英意识,不是士大夫的儒家文化,而是大众的儒家文化。这种相对弱势的儒家文化来到关外以后,虽然也给东北地区原始的雄健豪迈的渔猎、游牧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毕竟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发生了改变,一方面这种移入的儒家文化本身就存在弱点,另一方面是受关外苦寒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儒家文化在东北地区并不能轻易地同化东北原始的地域文化,并没有形成强势的文化冲击,而是与东北原始地域文化发生了碰撞和融合,并且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
这种碰撞和融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规范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文化格局,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因此,早期的大多数中原移民虽然来自底层,并不掌握和拥有中原的精英文化,但由于他们的故乡属于文化昌盛之地,是产生文化伟人的土地,所以他们来到东北后,心理上自有一份文化优越感和归属感,在浓浓的乡情中自然有对故乡文化的依恋和归属意识。骆宾基在其自传体长篇小说《混沌初开》中,通过对父亲形象的描绘,真切地展现出来自山东的“闯关东者”的文化寻根情结。这种自觉的向中原文化的回归和依附,是大多数来自中原的移民的普遍行为,他们的中原文化之根是难以割断的。对他们来说,背井离乡无疑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子曰:“父母在,不远游”。固守家园是中原人的一种人文精神。他们心中仍怀念着故土,怀念着“海南”。就像“乡亲——康天刚”一样,暂时离开故乡是要到关东发财致富,然后再重返故土,关东不过是暂时栖居的、获取重返故乡资本和生存资料的地方,真正的故乡则永远在心中,在中原。
然而,从近代以来的东北地域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影响的缺乏,特别是儒家的“礼教”传统的薄弱。例如阿成在他的散文《当代人的土穴与土炕》中提到章炳麟对北地火炕的批判:“北方文化,日就鄙野,原因非一,有一事最可厌恶者,则火坑(炕)是也。男女父兄子弟妻妾姊妹同宿而无别,及于集会,无所顾忌,则德育无可言”[17]。火炕是东北地区特殊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是祖辈为了抵御极北苦寒所发明出来的,直至今日在东北乡村仍然广泛存在。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地域环境对人们生存方式和文化风俗影响巨大,橘生淮南淮北有不同,一种文化进入另一不同的地域环境也会发生变化。文学所收摄的生活信息,总是与特定的时空中的具体认识相关联的,而这种具体而实在的生活往往是在特定地域中演绎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落到实处便往往要向“地域”的生活索求素材、提炼题材,并生成相应的地域审美观。考察一下现代的东北作家,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大多是移民的后裔,在他们的心中,一方面对中原主流文化是尊崇和亲近的,所以中原文化的变动很快就会影响到东北地区。五四运动前,受关内新文化的熏染,东北地区就已经有人用白话做起文章来,但还非常幼稚。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文学在当时的奉天、吉林、哈尔滨等地区迅速勃兴,新文学社团和新文学刊物陆续出现。另一方面,东北地域文化对他们的文化心理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固然当中原移民初到东北的时候,大多还怀有像“乡亲——康天刚”那样的回乡梦,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几代人已归尘土,现代的东北人虽然大多是移民的后裔,但是他们的成长环境是东北的大森林、大平原,他们的根系已经扎在了东北这块黑土地上,先辈的开拓者身份淡化为遥远的影像,成为偶尔被后代忆起的历史或传说。此时,移民的后裔们已经变成了东北的主人,他们的故乡就在这里,他们的性格中融会了先辈的开拓者精神和东北荒原林莽豪爽乐观、张扬外向的特殊气质。
日寇的殖民统治是影响近现代东北区域文化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可以说故土的沦丧,使现代的东北作家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支当时著名的歌中所记载的逃离故土流入关内的“东北人当年被迫离开家园的心情,呐喊着他们渴望收复失地,迫切回到自己故乡的悲愤情绪”[18]。迫于日伪政权的压力,舒群、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等东北作家相继逃离东北,流亡到关内。1935年以后,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端木蕻良《鴜鹭湖的忧郁》、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第七个坑》、白朗《伊瓦鲁河畔》、骆宾基《边陲线上》等一系列小说相继发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东北作家群引起了文坛的特殊关注。他们的创作给正在兴起的抗日文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增添了抗日救国的崭新内容,发出了强烈的时代呼声,因而也成为东北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1940年前后,在流亡作家群创作更为成熟,产生了《呼兰河传》、《大江》等重要作品的同时,“东北沦陷区文学也进入到繁荣阶段。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剧本)等各种文学体裁都有了较丰硕的成果,出现了热衷于长篇小说和叙事长诗创作的现象。山丁的《绿色的谷》、秋萤的《河流的底层》、田琅的《大地的波动》、石军的《沃土》、姜灵非的《新土地》、小松的《北归》、古丁的《平沙》等长篇小说都是在这一阶段开始酝酿、创作、发表的”[19]。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东北的沦陷刺激了,或者说激发了现代东北文学的发展。一方面,大批东北的仁人志士、文化精英流入关内,这满足了他们学习、吸收关内主流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背井离乡使他们与故乡产生了时空的审美距离,根须断裂和漂泊无依的痛感更加强烈,乡民生存状态和风土人情也更加清晰地萦绕在作家脑海,萧红的《呼兰河传》正是这一状态的最佳表述。而留守在沦陷区的作家的创作,也在日伪政权的压迫下和东北不断的战火的洗礼中,焕发出了动人的光彩。
但是,沦陷时期东北文学取得的成就并不能掩盖日寇入侵对东北地域文化发展进程的巨大破坏和打击。纷飞的战火使东北人民陷入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之中,物质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自然无从发展,移入的儒家文化本就没有扎稳根基,在这种环境下就更无法深入民心。近代以来的东北区域文化“有一个最重要的本质劣根性,就是其不完全不成熟的世俗化倾向”[20],日寇的殖民统治可说是造成这一缺陷的重要原因。日寇殖民统治造成了东北地区历史进程的间断性和精神文化发展的匆促性,同中国中心地带的文化相比,东北文化在过程内容、时间长度、变化方式等多方面有着历史性的缺失,具有杂糅、边缘、粗俗、蛮顽等特点。近代以来的东北区域文化是一种不成熟、不完全的文化,其主要表现如下:第一,没有形成根深蒂固的理性思维习惯,是一种“原始朴素的、以生存为中心,更多世俗化倾向的文化,其思维方式往往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其价值取向往往是实用的”[21]。第二,没有出现具有广泛影响的经典文本,日寇的殖民统治使东北地区的社会呈现出十分复杂而又极为惨烈的人生景观,然而现代东北文学对沦陷时期的东北社会民生却缺乏深刻的探讨和表达,个中原因,既可以归结为时间的接近,以及对反帝反封建实用性目的的集中表达,又与现代的东北地区文化积淀的薄弱密不可分,没有厚重的笔锋就无力描绘如此驳杂宏大的历史图画,这就造成了东北地区虽然有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却没有产生文学大师的尴尬局面。及至21世纪之初,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的出现,也只不过是作家用其擅长的纤细和敏感把繁复庞大的历史还原为平民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了对战争的残酷和非人性的激烈的批判、控诉和鞭挞,表达了对无助的个体被愚弄、被残害的命运的深深悲悯。第三,没有形成一个能够主导其文化前进方向的核心观念和基本原则。这就使东北文化的发展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之中,只重眼前实利,跟风跟潮,而无法建立独立的文化品格。
由此可见,近代以来的东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接受型文化,移民与殖民既给东北带来了丰富多元的文化因素,又是东北文化世俗化和不成熟的重要原因,但越是不成熟的文化也就越具有可塑性,因为越是成熟的文化传统就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越难以接受外来文化的入侵。东北文化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外部文化的接触,自身文化的浅薄使得东北人肯于接受和包容外来文化,表现在文学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的东北作家们身上集中了某些俄罗斯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影响,又带有儒家开明的精神个性,例如穆木天对日本现代文化思潮的吸取,萧军对俄苏文学的模仿,等等。但文化底蕴的不足,缺乏理性思维的能力和习惯,又决定了东北文化更容易接受那些表层的物质技术层面的文化,而对高层次的精神方面的文化则不敏感,缺乏理性的文化思考能力和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因而难以有持续的、原生的内在推动力,这也是东北一直文风不振的原因。应该说,东北文学可开拓的空间是广阔的,不过只靠学习和模仿别人显然是不够的,作家还需要真正深入到本土地域文化资源之中,真正体会那些在民族大融合过程中的苦痛的记忆,在善于向外看的同时又勇于向内看,东北文学的景观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