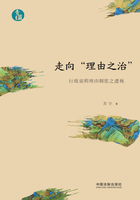
导言
行政法学需要一场思想变革。在“最为普遍的合法性形式即对合法律性的信仰”的时代,行政法治的内涵曾一度贫瘠得只剩下形式上的符合性,而合法性概念中隐藏的丰富内涵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合法律性非常重要,但远不是全部。在今天,当理由的形成、说明与审查成为行政过程中日益重要的构成部分时,它所展示的丰富内涵令人意识到,“理由”可能有着远超越单纯的形式合法性之上的深远意义。当我们渐次展开有关理由的思想史与制度历程的浩瀚图卷时,我们不仅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理由的内涵,也可以真正看清楚合法性的完整形象。真正的合法性并不建基于孤立的字面意义符合度之上,而是需要一系列的理由来支撑,直至总体上满足一定的充分性水平。在此,理由的角色举足轻重,无可替代。
在复杂社会中,行政法治远非单纯的形式合法性判断所能调节。在社会生活千变万化、行政法律规范更新让人目不暇接的今天,基于纯粹形式合法性的传统行政法教义学已经无法提供充足而有效的理论资源,而基于实质合法性的行政法学理论却又缺乏合适的中观概念架构。作为行政合法性的中间层结构,理由正是新的行政法学框架的理想支点。为了详尽而明确地展示理由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和意义,本书将沿着历史、法理、逻辑以及实践的线索,对行政过程中的理由作一次较为深入的检视。作为一项力图视野开阔的探索,本书的观察对象并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行为说明理由。这幅图卷上及于两千多年来理由在公法思想史中的漫长变迁、对合法性概念的深入分析,下及于行政过程[1]的各个主要环节,包括行政决策、行政立法、具体行政行为、其他行政活动与司法审查,甚至包括与此相关的社会互动。我相信,面对行政过程和行政法治实践中日显重要的理由层面,我们需要在历史中追寻法理,在现实中把握治道,在反思中探索未来。
(一)当前的研究基础
行政法上的说明理由制度是一个发源已久的学术主题,但只在最近一段时间才获得学界的强烈关注。近二十年来,西方国家对行政过程中的说明理由制度的关注与日俱增,最近几年这一主题更有成为行政法学一个焦点的趋势。1992年,当代世界行政法学名家马丁·夏皮罗教授以《说明理由之要求》一文引发了学界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夏皮罗在系统地介绍美国行政法上的说明理由要求及相关司法审查实践的发展历程以后,转而比较欧洲共同体法中的说明理由要求,指出欧洲共同体说明理由实践的不足,认为说明理由对于保障政府行为的透明性有着重要意义,欧洲需要积极的变革。[2]1995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著名法学教授绍尔(Frederick Schauer)的《说明理由》[3]一文揭开了对行政过程中的说明理由制度进行深入理论思考的序幕。绍尔教授此文展示了说明理由的深远意义,主要从普遍性(generality)的视角对说明理由的意义进行了阐发,认为与法规、标准、原则等相比,行政理由是最普遍但却最受忽视的普遍化机制。他指出,理由比之结论而言是更具普遍性的命题,它使得决定被放置进一个更普遍的原则中,并相当于为未来作出一种原则上的表面许诺(prima facie commitment)。由此,说明理由不仅改善了决定的质量,还增进了决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4]在夏皮罗和绍尔之后,英美法系学界开始从不同角度深入思考这一主题。例如,南非的乔治·巴里(George N.Barrie)教授对英国和美国行政法中的说明理由制度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引用庞德的名言说明这一制度的重要性——它可以使绝对的权力受到以理性为基础的法律的约束。[5]芝加哥大学的格伦·施达策维奇(Glen Staszewski)从说明理由制度与负责性(accountablity)的关系着手,指出传统政治负责性图式(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paradigm)已经变得不可靠,派性的、代理的和直接的负责性图式又各有弊端,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主张“协商的负责性图式”(deliberative accountability paradigm),并将说明理由要求作为这种负责性图式中的首要因素,它限制了行政裁量权,提升了政府活动的透明度,并提供了协商的重要基础。[6]周迪·肖特(Jodi L.Short)更是直言,说明理由在美国行政法当中已经居于中心位置,并提出超越理性化的模式而从政治功能上看待说明理由的作用,强调说明理由对于法律和政治互动结构的重塑力量。[7]著名公法学家马肖(Jerry L.Mashaw)更是直接以说明理由和理性行政为主题形成了专著《理性行政与民主合法性》(Reasoned Administr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由此,行政法学界对说明理由制度的研讨有日益深入、如火如荼之势。
在大陆法系国家,学者们对这一主题的关注也是自最近十年来才开始逐渐升温。例如,德国学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甚至比美国学界更早,早在1974年就已经开始有这方面的专著;[8] 1989年,德国《行政程序法》第39条关于说明理由的条款也被行政法学专家以专著的形式进行了详细阐释;[9]但是,从理论到实践各方面较为成熟的作品直至2003年乌维·基舍尔(Uwe Kischel)的《说明理由:为国家针对公民的决定提供阐释》一书[10]才真正出现。此书从说明理由的概念及历史背景写起,论及说明理由的制度框架、功能,阐明说明理由的宪法基础、说理义务的教义学结构,介绍了法治实践中国家权力所作决定的说明理由义务,特别是行政行为说明理由的情况,延展及说明理由制度的各个方面,可谓一部集大成的作品。至此,德国行政法上对说明理由的研究已经全面趋于成熟。而在同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大陆法系国家日本,行政过程中的说明理由也得到了全面的研究,除去制度层面的差异,德国对行政法上说明理由义务的认识与英美已经日趋接近,但也有所差异。德国学者从促进行政的实质正确性(materielle Richtigkeit)、加强行政机关的自我约束和外部控制、增强行政的透明性、强化公民的接受和认同、生成更充分的合意等几方面解读说明理由制度的功能与意义,将对说明理由制度的认识推进到一个相当丰满的水平。
在我国,自世纪之交以来,行政过程中的说明理由制度也日益得到重视。章剑生教授《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判解》[11]一书是早年对这一主题较为突出的专著,该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法院针对行政行为说明理由的数十个判决,在阐述了行政法上说明理由的意义和要求的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此后,李春燕、朱应平、宋华琳、郑春燕、秦静等学者也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这种探讨主要可以归结为四条进路:一是外国制度引介和比较研究,以宋华琳的《英国行政决定说明理由研究》[12]、朱应平的《澳大利亚行政说明理由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发》[13]、梁承武的《国外说明理由制度立法模式比较研究》[14]等为代表,其中较有深度的分析集中于英语国家;二是理论与比较相结合的研究,以郑春燕的《论行政行为补充说明理由》[15]、尹建国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说明理由》[16]等为代表,理论研究虽然精彩纷呈,但限于主流行政法学的常规架构之内,未能进一步深入其法理内核;三是实务研究,多为行政机关中的实务工作者所撰写,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如江苏省镇江市工商局的《推行说理式文书促进执法规范化》[17]《林业行政处罚说明理由浅谈》[18]、苟铭的《“干戈”如何化“玉帛”——三问江苏盐城质监实施的全程说理执法新模式》[19]等,但有的研究也停留在空泛的宣讲层面;四是系统性的全面研究,以一系列行政行为或行政决定说明理由方面的学位论文为代表,但基本上均限于硕士学位论文,多数研究存在浅尝辄止的情形。从时间上看,在2000年以前,这一主题仅有章剑生和李春燕的两篇论文;近十余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喷涌,直接相关的研究文献已超200篇,研究的精度和深度都在持续强化。可以认为,我国对行政过程中的说明理由制度的研究虽然方兴未艾,但前景非常广阔,未来的成果将相当可观。
(二)研究现状之简要评析
总体上看,对于行政过程中的说明理由制度,国内外学界已经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尤其在美国和德国学界,对这一制度的法理基础、法律依据及司法实践的研究已经得到全面推进,各个板块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已经有了切实的通盘掌握。不仅如此,他们对说明理由的研究成果,已经全面反映在行政法的教科书中。例如,在长达六大卷、数千页的美国著名教科书《行政法》中,作者以详尽的篇幅介绍了这一制度的主要规范与司法审查实践全景。[20]国内外学界的这些研究基础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
不过,虽然国内外学界在这个主题上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研究,但从整体上看,现有的研究在理论深度和实践广度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尤其是一些根本的理论问题往往被忽略。从理论深度上看,一些论者已经注意到了说明理由对于加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21]的作用,并将说明理由制度的许多意义和功能与合法性增强作用关联起来,但却没有指出这种关联的法理根源何在。这一点正是制约整个说明理由制度研究深入进行的关键。换言之,当前针对说明理由制度的理论研究均是从外部视角进行的探讨,缺乏一种有效的内部视角对说明理由的意义进行整合与深化。也因为这一点的缺失,有关可接受性(acceptablity)、负责性与促进沟通、加强控权等各个要点无法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说明理由制度始终无法获得一个完整的意义图景和制度定位。从实践广度上看,说明理由制度的比较分析并未获得有效的展开,尤其是跨越法系的比较研究较为欠缺,对于说明理由制度的主要推动力——司法审查也没有作深入的追寻。尤其是国内学界针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基本上多属法条罗列和简单的法律价值宣示,既没有深入的法理和历史探索,也没有详备的实践素材支持,使得研究呈现出一种悬空感。
因此,对行政过程中的说明理由进行研究,必须力避既有研究所陷入的窠臼,而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打通理由与合法性之间的法理联结,将说明理由制度的外在功能统一于内在的法理中,使得说明理由制度能够在行政法学的理论架构中有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在这方面,现有的理论思考已经为深入推进研究做好了准备。在西方,盖涅斯·波斯特(Gaines Post)、维若里(M. Viroli)等学者的法律思想史研究已经揭示了公法思想中的“理由”与公共权力正当性/合法性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卡尔·施米特、于尔根·哈贝马斯等著名当代学者则提供了切入的法理线索。在国内,沈岿、王锡锌、何海波等教授对于(行政)合法性的深入反思(详见后文)也已经为深入打通此项法理关联做好了理论铺垫。在这种情况下,以“理由—合法性”的关系为主线,沿着行政过程中理由的形成、说明、审查及围绕理由的社会互动,展开整个说明理由制度的完整图景,从而彻底打通法理各要点及理论与实践间的关系,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最佳路线。
(三)本书的基本架构
基于以上论述,全书的架构由六章和一个简要的余论组成。第一章“理由在当代行政法中的地位”展示理由在公法中的历史变迁和当今风貌,寻求追根溯源,以知其非一时兴起的发明,而实含深远的机理;同时探索合法性的内层构造,力求深入展开合法性概念的复杂结构,表明理由在合法性认知中的关键地位,从而为真正把握行政过程中说明理由制度的完整功能奠定基础。第二章“理由的内涵与构造”具体阐述行政过程中相关理由的逻辑模式及构成类型,为详细展开理由的说明与审查机制作理论铺垫。第三章“理由的形成与说明”对行政过程中相关理由的形成与说明机制进行了扼要的比较分析,显示出当前说明理由法制的日益发达。第四章“针对说明理由的司法审查”以美国和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司法实践为代表,对行政过程中所说明的理由的司法审查范围、标准及力度进行了阐述。第五章“围绕理由的社会互动:说明理由的深远影响”进一步拓展了行政说明理由活动的法治意义,检视相关理由所可能促进的社会互动效果及社会影响。第六章“中国行政过程中的说明理由制度”集中检视了我国行政说明理由法制实践中的现状及问题,在肯定说明理由法制建设成绩的同时也思考这一法制建设的不足之处及提升空间。余论“理由的位置:行政法学体系的拓展”则从审视行政法学体系根本变革的需要及进路,指出理由或许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新的学理体系基点,通过一定的理由结构来丰富和充实行政法体系的横向结构是有益的发展方向,需要我们为之努力。
[3]. Frederick Schauer,“Giving Reasons”,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47(April, 1995), pp.633-659.
[4]. Frederick Schauer,“Giving Reasons”,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47(April, 1995), p.654.
[9]. Siegfried Schwab, Die Begründungspflicht nach 39 VwVfG, Centaurus-Verlagsgesellschaft, 1989.
[11]. 章剑生:《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 宋华琳:《英国行政决定说明理由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
[13]. 朱应平:《澳大利亚行政说明理由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发》,载《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
[14]. 梁承武:《国外说明理由制度立法模式比较研究》,载《社科纵横》2007年第7期。
[15]. 郑春燕:《论行政行为补充说明理由》,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16]. 尹建国:《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说明理由》,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5期。
[17]. 江苏省镇江市工商局:《推行说理式文书促进执法规范化》,载《工商行政管理》2009年第3期。
[18]. 邹润学:《林业行政处罚说明理由浅谈》,载《森林公安》2012年第6期。
[19]. 苟铭:《“干戈”如何化“玉帛”——三问江苏盐城质监实施的全程说理执法新模式》,载《中国质量技术监督》2008年第5期。